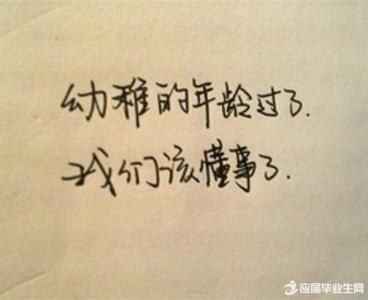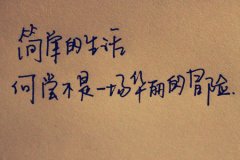父母养儿女,路样长;儿女养父母,扁担长。令人落泪……
生老病死
早春最冷的那几天,村里又一个老人走了。因我问起是什么病,母亲淡淡然说:“没什么病,老了呗。八十三了,确实可以死了,难道还能一直不死?”
她这些年对生老病死似看得越发淡了。都说崇明是长寿岛,但老人们只怕心里都清楚寿则多辱 。村里倒有三个老人年过九十,都已守了二三十年寡,有两个因为常年闭门独居,我甚至一度误以为她们早已离世了。
有次为了询问族里祖上的旧事,我去过其中一个老人家里,墙上的日历还是两年前的,暗沉沉的屋子里有几分阴寒,安静得像是坟墓。他们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已被遗忘,儿孙们不大喜欢来这些小屋里。
村里兰芬的婆婆也已九十四岁,自幼年当童养媳嫁入沈家,在这村子里已生活了八十多年;兰芬平素对婆婆还算不错,那天却也当面抢白:“你在大哥家里倒是精神焕发,看你贼都打得死,怎么偏在我们家里老是唉声叹气?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虐待老人。”她婆婆当即闭口不言。
说到这,母亲说:“我也老了。都没用了。可我不想自己将来这样。虽然活着,可你的自由都掌握在儿女手中 ——你走不动了,要上镇很难;想吃什么,都要经子女同意。我不想这样活着,我受不了这个。”
去年秋,五姑父的父母都走了。那时已有几分秋凉,老太太起夜去解手,老头叫她别去茅厕了,拉扯时推了她一把,失了轻重,倒在地上就此摔骨折。八十七岁的年纪了,再经不起这折腾,进医院后没几天就告不治。五十三天后,老头也走了。在此之前好几年,老头本已有些痴呆,到临死前更连老太婆走了都不懂得了。
五姑父平素有些咋咋呼呼,这几年更有几分脑满肠肥的志满意得,但父母面前倒是个孝子,这次老父最后就是死在他臂弯里,他在那泪如雨下。这几年知道老父亲有几分痴呆,老母颇为不易,不时会去南宅看望,唠会儿家常。最后那两三个月自尤其费心,一次听说老父亲情志不请,拿着剪刀对人,饭未吃罢便奔去,惹得五姑怒骂不止,到最后邻居听不过,在旁劝:“你不去照顾公婆也就是了,每次还骂他。”
这一点上,他女儿晓丽倒是和妈妈一样,也说:“老去干嘛?就生了你一个?没轮到你的这天也去,关你屁事?”我妈劝:“你爹是长子嘛。”“长子又怎样?落到点什么好处?”“别这么说,将来当大事,是要你爹来捧骨灰盒和牌位的。”“那难道是什么金盒子、金牌位?”
我以前其实还挺喜欢这个生性活泼的表妹,只是这十多年来相见甚少,印象中她仍停留在那个扎辫子的秀气小姑娘上,浑未料想她早已是一个干脆泼辣的少妇。她向来八面玲珑,这些年混得不错,不知怎么挤进了县城的事业单位,虽然不属公务员编制,好歹清闲工作也有两三千月薪,在县城也买了房,便于孩子在那读书。她只比我小两岁,出嫁已有十年,但仍常住在娘家;虽然在邻镇的夫家有房,却几乎从来不去。反正每天下班早,懒得买菜做饭,于是每晚父母等她七点半到了再开饭,老公倒等如是倒插门女婿一般。
她老公姓吴,是她职校毕业后在长征农场的珠宝厂里认识的,那时觉得他为人温和可靠,又曾去日本劳务输出过,算小有积蓄,二十一岁就结婚了。一次她婆婆来,我妈向她称许其子温厚,她婆婆笑笑说:“他傻咯。我这儿子,是帮别人家生的。”
吴本有兄长,但早夭,按单独政策也可生二胎,晓丽见他来劲,冷冷地说:“你喜欢是吧?那你自己生吧。出钱给我都不生。”更早前有次,吴心血来潮说起不如把两人的姓氏嵌入儿子的名字,叫“吴爱倪”算了,那时也不知何故逢彼之怒,她怒道:“操你妈逼,什么吾爱你?爱你个毛?”
她这泼辣个性,其实颇肖其父,弟弟的内向则像其母,所以五姑父向来喜欢女儿多过儿子,只是有时父女俩也互相看不惯。她耍泼起来没大没小全无顾忌,开骂也是家常便饭,当着面就对其父说“你只乌怂壳子”(等如说“你个傻逼”)、“也就我妈才会跟你”;对其母也并不客气,有次看不惯她老是忙忙碌碌,便说:“你就一直做吧,挣的这点钱将来还不够你买药吃。”
五姑父一次也怒:“妈的都嫁出去了还老赖着不去夫家,就知道啃我们,真个老话说的,‘强盗丫头贼外孙’。”我妈劝:“你别嘴硬,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总认得她。”姑父怒气未消:“死就死了,认得她什么?”
五姑原本重男轻女,小时开口便骂“贱人”,这些年却渐渐觉得还是女儿好——因为儿子脾气太好,全受老婆支配,连春节都不回家来。当初五姑原不肯嫁入同村的倪家,哭了好几天,但她畏惧奶奶,终于还是从了。那会她有手巧而勤快的名声,未来的婆婆逢人便说,娶到这媳妇是福气。事后证明,她确实很会持家,但手也极紧。
女儿晓丽出生时有点难产,也不知怎么回事,阵痛时胎心不好,不痛时胎心又好了,那会儿姑父泪水簌簌落。不得已转院到县中心医院,所幸遇到一个老医生,省了剖腹之痛便顺利接生。奶奶有些看不过去,说:“我生七个孩子都没你如此难,看这样别再生了。”我妈当时便说:“倪家重男轻女,不可能不要。”
果然,两年后儿子出世,姑父一时满面喜气,姑妈则因违反计划生育而被村办企业辞退。两人务农之余,几乎各种杂活都做过了:养猪养羊养鸡鸭、做豆腐、经营石灰场、轧米厂、接活做夹子(40元一天),最近两年则是开棋牌室。
倪家也确实有些重男轻女,至少晓丽一直觉得爷爷奶奶偏心,自己自小不是带弟弟就是带堂弟;对他们的离世,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据她说,七年前偶尔看到老头在银行转存两万元,怎么这么多年下来,身后仍然还是只剩两万?——可见这些年攒的钱都给了叔父。其实,乡下人种种地,又能有什么钱可偏心的?

即便是偏心,看来也有情可原。她婶婶侍奉公婆多年,喂他们进食,如今乡下没有哪个媳妇能做到这一点;连老头痴呆了打她,都还陪笑脸。老头垂危时吊盐水,很多日不见好转,五姑心疼医药费,不耐烦地说:“老挂不好,早晚都要死的还挂个没完。”这小的媳妇则说:“大哥,怎么办?难道看着爹死?再挂几日吧,总还有希望。”
至于医药费,“如今有小城镇保险,爹用的也不是我们的钱,就算是,又能有几个月?我们也都有子女。”听乡里赞誉婶婶,晓丽颇不以为然:“老说她好,好什么?她不过是替她男人的。”——她叔叔在上海开出租车,停一天要赔380元,所以病榻前到得少。
一次我妈说起这些事,叹息一声,她说,你们现在拉扯孩子,四年多下来能有1500天了吧?到哪天我和你爸不行了,你们做子女的能侍奉上150天? 舅公黄唯虎走之前,因肺部积水病危了十来天,四子女分上下半夜轮流照看,他身故后,儿子还说:“我爹要是再活下去,我们都要吃不消了。”古话说得没错:父母养儿女,路样长;儿女养父母,扁担长。
许多年前,村里的老人沈元郎垂危住院,女儿金兰扶他去上厕所,他那时已将油尽灯枯,在马桶上挪动一下也难,竟弄脏了裤子。女儿抱怨:“阿爹你怎么搞的,屁股再稍微朝前一点嘛。”他默不作声了一会,叹了口气说:“你到底是个傻闺女。你福气好,爹这是没几天了。”三天后,她跪在爹的灵前,想起这番话,一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