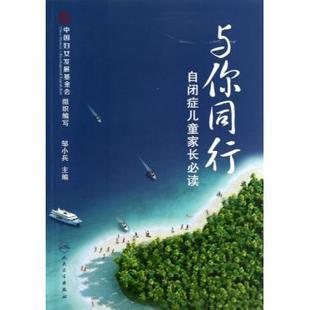深夜了,总想为自己写点什么,不为什么。
有时候,觉得孤独。但是因为深知孤独无药可医,所以也不想对谁说,孤独是海水,时间吸着吸着,就吸走了。

这个世界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些事情,像烟花在我们身边噼噼啪啪炸开,有些人被炸伤,有些人跑得快,而我是那个默默站在灰烬里,想要打扫一地落寞的人。
从小时就知自己和他人有点不一样,不是很喜欢站到一堆乱嚷嚷的人群里,为了多讨两口面包,而尽量挤出笑容。我不喜欢摆在脸上的,犹如工具的笑容,也不喜欢被一群人,像看屏风一样,观赏自己的眼泪。委屈也好,骄傲也好,都藏在心里,文字是我的衣兜,它把我的种种情绪装到里面,所以,我不会离开文字,因为若离开,也不知,还会有谁,能陪伴我那么久 。
一个人的夜晚,我喜欢无所事事的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大抵的路线也就不过是从卫生间、厨房、到卧室。会备上很多的零食,灌到胃里。我觉得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会比较童真,而童真的人,就爱做些理想主义者的梦:梦里有花园、有爱偷豆子的土拨鼠、有埋在海水里,像地壳层拱起一样探出头的海豚、还有可以把雨水串成珠子的亮闪闪的项链……我喜欢做梦,这是我最宝贵的爱好,在梦里,你可以无所压力的挺直身体,就像把所有的委屈,无助,都展开一样,安眠睡去。现实生活里的我,睡觉的时候,总是紧攒着拳头,有一次,EX掰开我的手心,把我的五根指头一一捋平,他说你睡觉,总是那么紧张,睡觉是个很轻松的事儿。来,学学我。他在我面前,就像把翅膀展开的海鸥一样展直了身体,你会以为,有一个可以升到天堂的竹藤,从他的语言里长出来,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长出来,好像睡着后,就会有弹着竖琴的天使,拥你入怀。
可事实是,事实这个词太过残忍,可我又不能不直视事实,人在活着的路上,要跟一个个事实相撞,有些事实会割伤你的脸颊。我们分开了,分开的很凄凉,凄凉的就像一枝还没长大就开败了的植物。
(爱华阅读配图)
人若是,能像个植物人,躺在床上,光能听见这个世界发生的斗转星移的变化,但不做任何反应,也是件颇幸福的事情。人要有反应,就会痛苦,因为要抉择,要想朝左走,朝右走。最哀伤的不是你走错了方向,而是你走着,走着,一回头,原本跟着你的那些说要一辈子守候你的人,已经不在了。
这些年,我无疑吃过很多次大亏,因为直言,或者因为忤逆,吃了一次次哑巴亏,我又不喜欢狡辩,受伤了也最多当一句玩笑话左耳进右耳出,可有时候,积郁的悲伤,就会像关在抽屉里的风,露出一个角,然后漫天的,在你的心里哭号起来。我不喜欢咀嚼苦痛,也不喜欢绝对乐观,哪里有绝对的乐观啊,人活在世上,必然要受伤,而这伤,不论谁发了多少誓言,都得要自己一根一线,才能缝补好。
好在还有黑夜,黑夜是最好的保护色,内心黑暗的人,也可以短时间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在黑夜哭,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在黑夜里,常常蜷缩了身子,就像被逼到死角的流浪儿童,表情却是僵死般的凝滞,带着兽的机警,和秃鹫的蛮狠,好像要和把自己抓走的怪东西对峙一样,可手指,不过是寂寞的在黑夜里扑了空……
人孤独的时候,哪怕周围充满了笑容,呆在热闹的红艳艳的KTV房里,也觉的孤独,孤独就像倒灌的海水,把眼泪倒灌进你的瞳孔里,很多人不想哭,只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倚靠的肩膀,在她哭出第一声时,就决绝的把她的眼泪抹去,我的很多眼泪,都是在风里风干的,或者就由空气的温度,一节节的冷下去,把眼泪冻成冰渍。
那种眼泪冻成的冰花,就跟一个无人住的屋子,残败的窗户上,被风掀起一角的窗花一样,看起来有人情味,却不过是一个留恋时空的摆设。不过哭泣,特别是在人前哭泣是小孩子的权利,我那么大了,也不需要用眼泪来证明是坚强或软弱。哭也不过就是生理功能上,解释的——一次对多余水分的宣泄而已。
人长大就是好事,比如,你可以证明,一段爱情的完结,是因为彼此荷尔蒙的耗尽,一个人的死去,也依旧有热波在空气中凝固成这个人的形象,那么,分手的人,就会原谅爱情的遗憾,健在的人,也就意以为已故者无时无刻的不弥散在周围。
黑夜里赶路的人,总是看起来有些说不出的冷漠,但是又充满了温暖,很容易向一个陌生的人靠近。人有时候真的很怪,即想人接近,又小心翼翼的要推开,怕一旦心里的窗户打开了,就会有人偷了你的心,绞碎你的肠。所以很多赶路的人,会眼神绵柔姿势抗拒,我有听过一个闺蜜,在很黑的夜晚,声音很软的讲她和一个不够爱的男人做爱,就像被浇了过凉或过热的水,内心虽知不是自己想要的温度,但因为太过干涸,太过干涸,才需要有什么感情,兜头的泼下来,把自己浇醒,或灌醉。
深夜里,紧紧扣紧一个人,把他的臀贴近自己的臀,就像彼此敲进对方身体里一样,虽然深知白天就要分别,可还是喜欢这一刻,有人大汗淋淋需要你的感觉,需要有个人,摘掉你白天防备的层层面具,然后坦露伤疾,袒露寂寞,坦露需要,袒露动摇,坦露你对一个人,一副身体,一颗心的渴求。
听广播,电台广播里的女孩,声音甜美的激励着听众,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在拔掉听筒的夜晚,在一个人赶路的街道拐角,忽然慌张的想哭泣,路边做生意的小贩,看起来满面红光的数着钞票,谁知道他会不会忽然动摇了用青春赚这些钱的意义?还有那些背着包,在火车站,一个,又一个,来到这冰凉而热闹的大城市的漂泊族,他们又会不会忽然就在出租屋里,蜷起了身子,脊背顶着墙角,想倒回到出发的前夕?
谁也无法预料我们这一刻的抉择是对,是错,只有时间,荒谬而理智的,砍掉一茬茬情感,冻住一滴滴软弱,送走一批批人,然后把你双手奉送到霓虹灯照耀的明天去……明天,又是个灯火闪烁的夜晚了,可有谁知道,在这样的夜晚,道晚安的人,是否真的睡去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