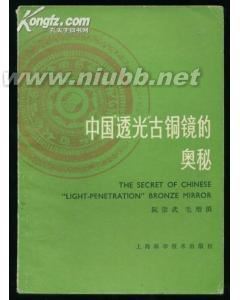渠枫来见我的时候,披头散发,衣帽邋遢。对一个容颜娟秀的女孩子来说,糟蹋自己到了这种地步,可见她遇到了重大的困厄,心灰意懒,已经抛弃自爱,不再珍重。
她一屁股坐下来,从内兜深处掏出一件东西,握在手心,对我说,都是它把我毁了!

我以为那会是一枚珠宝首饰或是一个信物,要么干脆是一封绝交信,没想到在渠枫苍白
的缓缓展开的手掌心里,是一只普通的塑料的小眼药瓶。到街上的药店,一块钱可以买回三只。
我细细地观察着这只药瓶。奇怪它有何魔力,竟能把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折磨得如此憔悴萎靡?
药瓶基本上是空的,它的底部,有一些暗红色的渣滓沉淀着,好像是油漆的碎片。瓶颈部的封堵已被剪开。之所以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它被剪开的位置,反常地偏下。一般人怕药水大量滴出,瓶尖部的口通常开得很细小。但这只眼药瓶,几乎是从瓶肩部被断开了,瓶颈缩得短短,仅够套上瓶帽。
我看着渠枫。渠枫也看着我。很久很久,沉默如同黑色的幕布,遮挡着我们。终于,渠枫说,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说,我在等你。
渠枫说,等我什么?
我说,你来找我,就是信任我。我等着你把你想要对我说的话,说出来。
渠枫又继续沉默。当我几乎不寄希望的时候,她突然说,好吧,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爱上了申拜,一个并不高大但是很有内涵的男生。有同学说,依你的条件,可以找一个比申拜外形更酷的男孩,申拜矮了些,要知道,身高就是男人的性感喔!我说,我看重的是申拜的内在。注重男子的身高,是农耕社会和游牧民族的习气了,机械欠发达的时候,男人的力气就是他的资本,比如扛麻包挑担子什么的,当然是大个子占便宜。如今到了电子时代,经营决策,敲击电脑,都和身高无关。一个男人能不能给女人幸福,不在身高,在乎内里的质量。
朋友被我驳得两眼如同死鱼,干张着嘴,无话可说。申拜知道了我的观点,对我更是呵护有加体贴入微。他说,我是他交的第一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是我的……。我们的感情很快进展到如胶似漆。一天,我约他到我家玩,父母正好同到外地出差。夜深了,他抱着我说,他忍不住了,想彻底全面地得到我。我急忙推开他的手,说,不……不能……
我看他退开,情绪很伤感,觉得我对他不信任。就急忙安慰他说,不是我不愿意,是我还没做好这个准备。下次吧,好吗?
他很尊重我,就让自己渐渐地平息下去,那一天,我们好说好散了。
没想到他期待中的下次,竟那么快,就是第二天。也许是怕我父母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就不容易找到如此安全无干扰的地方了。又是我的小屋,又是子夜时分,我们聊着,却都有些心不在焉,在期待着什么,畏惧着什么,迎接着,又想躲避……
他突然拥着我说,今天,你准备好了吗?
我战战兢兢地回答,准备好了。
我把灯熄灭了。在黑暗中,我们脱掉所有衣服,把彼此还原成伊甸园中的模样。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看着窗外,觉得自己的床如此陌生,我就要在这张床上,变成申拜的新娘。我看到申拜被月光镀成青铜色的躯体,知道一个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申拜的激情越来越蓬勃,我在昏眩中等待。就在箭即将离弦的时候,他突然抬起身体,说,渠枫,你说得对,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既然我们要爱到地老天荒,为什么不能再等几个朝朝暮暮?我保存和尊重你的领土完整,直到婚礼之夜……
我拼命搂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离开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申拜,你不能这样!不能!我要你!
但是,没用。申拜是一个自制力非常顽强的人,他一旦决定了,谁也无法更改。我于是绝望地看着他起身,拧亮电灯……于是,在明亮如昼的灯光之下,他看到了–在我的雪白的床单之上,有一片鲜红的血迹……
这是什么?他大吃一惊。
刚才,床单上还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我干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干啊……
申拜惊愕地捶着自己的胸膛,我知道,在他的胸膛里,一颗纯洁的心正在粉碎。
他疯了似的抓住我,歇斯底里地喊道,这是你干的,是你!是不是?
我泪水凄迷地点了点头。这屋子里没有别人,不是我干的,又是谁干的?!
这就是你所说的要做的准备,对不对?你想伪装成一个处女,你作案的工具在哪里?在哪里?!申拜的目光喷吐着蔑视的火焰,嘴唇哆嗦。
我不说。我什么也不说。默默地穿上我的衣服。我看着申拜,如同路人。刚才,我们还在肌肤相亲啊。
申拜在我的房屋里疯狂地寻找,很快,他就在我的床下,找到了这只眼药瓶,里面还有几滴残存的血液。
申拜说,你是处女吗?
我说,我不是处女了。
申拜说,那个人是谁?
我说,是我以前谈过的一个男朋友。我不知道男人为什么要用性这种东西,让女人来证明自己的爱。我那时还小,我不知道说”NO”。当我发现他不可信任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