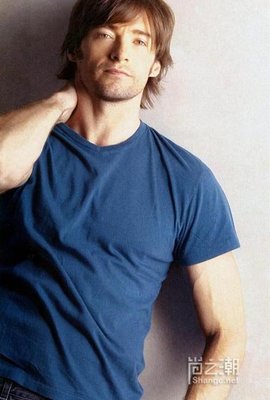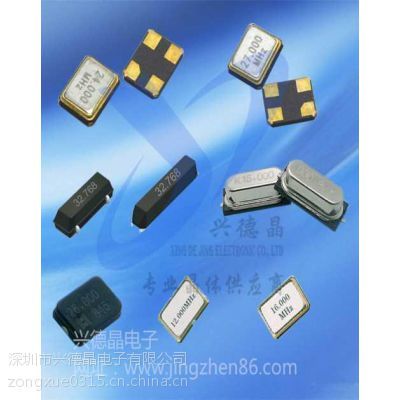一夜长大
(马良:当代艺术家、观念摄影师、导演)
我小时候是个弱小的孩子,身体不好,各种体育活动无一精通,智力也让人着急,功课大部分是不及格的。每次恬不知耻拿着亮满红灯的成绩报告单让家长签名,我妈总是先长叹一口气,再签字,然后摸着我的头用一种无比悲悯的眼神望着我。
习惯了各种垫底,我倒也培养出某种超脱于“俗世”的洒脱,别人都在认真读书,我上课下课都在画画儿。小学毕业,校长推荐我跨区去考上海当时唯一一所美术专业教育的初中,可校长把报名表给我的时候,话锋一转,这个学校文化课最低分数线是240分,也就是三门功课每门平均80分。试试看吧,“神笔”马良!
我本来觉得人生之路在我眼前“砰”地一下就铺开了,像是老式闪光灯烟熏火燎地亮了一下,前方我的理想国,一瞬间都可以看见了,但事实也摆在这儿,我这糟糕的学习成绩就像瘸了的腿,根本就走不了路。
果然,模拟考总分190。晚饭后我把卷子掏出来放在父母面前。爹沉默了许久,轻声缓语地问我还有多久正式会考,这一问我是彻底绷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也就两三个星期了,来不及了,我不可能考进美校了,我已经尽力了,你们不要怪我!”那天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对我这个从小散漫不知痛痒的孩子,这实在算是个前所未有的重击。
第二天早上,我睡眼惺忪里突然看见墙上贴了一幅很大的毛笔字,是父亲遒劲的书法: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从小爱看闲书,这对子里的两个故事我都是明白的,也许是诗歌的魅力吧,突然这几个字抑扬顿挫地连起来,居然有连天号角军马催动的壮阔。
后来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学习,最后如愿考进美校,然后读美院,一学就是十多年,算是扎扎实实地和美术结了缘。直到今天,还是会常常回忆起那个早晨,这可以算是一夜长大吧,从一个糊涂小孩子只一夜间就变成了怀有某种英雄主义理想的预备役男子汉。我后来甚至有种错觉,这满脸的络腮胡子也是一夜间生长出来的,从路人张三一夜间就变成了猛张飞。
艰难的抉择
(袁凌:作家、媒体人)
30岁那年,面临选择,作出决定的瞬间,我觉得真正成人了。
我不记得在哪个瞬间自己成为一个男人的,可以肯定的是,30岁那年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当时,我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新京报》做全职记者,那一年《新京报》刚刚创刊。做调查记者需要付出很多精力,时间长了,学业完全顾不过来。到了最后事情变得严重起来,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我还想拿到学位就必须放弃调查记者的工作。

那是在2003年的冬天,最纠结最犹豫的时间持续了近一个月。这个选择对我十分重要,同时艰难无比。读完博士后,生活可能会相对安定,而《新京报》刚刚创刊,前途未卜,调查记者的工作又比较辛苦,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我想要的是和现实相关的东西,我也渴望成为一个写作者。
当时我的头发掉了很多。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我没有告诉家里人,也没有告诉同事,因为当时隐瞒了在读的身份。最后我选择放弃学业,专心去做记者。那时候,我的导师对我说了一句话:“与其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后果,档案和户口将会变得非常麻烦。
第二年4月份,我正式办理了退学。作出决定的这个瞬间是我真正成人的瞬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不安中度过,我记得我经常会微微颤抖。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篇一篇的稿子让我内心慢慢感到踏实。时至今日我都不后悔,我知道了自己真正在乎和热爱的东西。
鼻涕虫
(欧逸文:记者、2008年度普利策奖获得者)
10岁时,在美国的东北角缅因州,我在一个湖边度过了整个夏天。在我到那儿的第一个早晨,其他孩子都向一个树木茂密的小岛进发,它离海岸大约有一公里。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知道如何游泳,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过只是知道如何水而已。我能够用“狗刨式”在水中游来游去,能平稳地划水,但需要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时,我失败了。我试图跟上其他孩子,但200米后,我开始下沉。我看着他们向前冲刺。一个成年人把我捞到一条小船里。
一年过去了,这次“小岛游”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无论何时,每当我想起它,我总能想起在心中留下烙印的虚弱、脆弱和不堪一击。对于这基本的人类技能——漂浮在水面上——我是个失败者。
下一个夏天到来了,我拒绝前往那片水域。一个早晨,在人们醒来之前,一个少年唤醒了我,他力劝我去湖边。我们悄悄地跳进湖里,开始游泳。200米后,我的胳膊感到疲劳,没有力气,我翻过身来休息,用侧泳的方式推着自己前行,然后再翻回来,挣扎着踢水,像鼻涕虫一样缓慢地前行。我不停地被水往后推,以致偏离了方向,又不得不涉水回去,回到航道上。那是最难看的游泳姿势,但好歹也是在游泳。一个小时之后,我感到脚下黏糊糊的岩石表面。我到小岛了。并不是想象中平稳、直接、优雅的冲刺,但我漂起来了,一直在向前。后来我发现,那正是我花了很多年时间成为一个男人的方式。
父亲不在了
(沈博阳:糯米网创始人、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父亲是个极其聪明和勤奋的人。他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渴求。我们从未有过亲密的交流,也从未直白地表露感情,甚至没有过一个拥抱。在美国时,每个周末我都会给家里打电话,父亲接起电话,交谈不过三句,电话便被转交到了母亲手中。1996年到2004年的8年里,我只在1999年回过一次国。
2004年,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者说不愿意去回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接电话的人不再是父亲,母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去填补我的疑问,父亲出差了,父亲最近工作很忙……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实在记不清当时我在电话中是如何知道这个消息的,我所想的最坏的结果不过是父亲生重病住院。挂了电话后,我大哭了一场,那应该是我生平第一次痛哭。悲痛、无助、遗憾、悔恨各种感情席卷而来。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父亲不在了,就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无论以后我多么优秀他也看不到了。更大的遗憾是,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在他身边。
那次痛哭之后,我知道我已经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男人,应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更知道活着的幸福。2006年回国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父亲选了一块环境清幽的墓地。墓地周围种上花草,墓碑上有两只栩栩如生的鸽子。父亲生前很喜欢养信鸽。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父亲具体是什么时候走的,因为什么走的。我没问母亲,我没有勇气再去碰这个话题。
1999年回国,父亲和我在家门口那次平常的道别竟是永别。我只记得那一年回家,母亲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清晰地记载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间和通话的长度,某年某月某日,几分几秒。纸上全是父亲的笔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