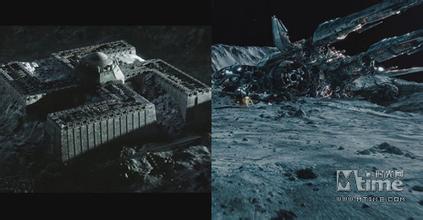唐人张打油先生有首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虽明白如话,且杂以村言俚语,却因视角独特,幽默传神,机巧有趣,而被人们推崇,这类诗体遂被后人称为“打油诗”。这首别有情趣的咏雪诗,可谓开了打油诗的先河。 打油诗拙中见巧,俗中藏雅,那亦庄亦谐的语言,机趣横生的意蕴,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往往令人过目难忘。一次,苏东坡遇到两个“不通”的秀才辨认文庙上的字,一个说是“文朝”,一个说是“丈庙”,争执不休。这时又来了两个“不通”的秀才,一个建议:“还是查查字曲(典)吧。”另一个更“不通”的秀才则说: “何不问问苏东皮(坡)先生?”苏东坡闻此,戏为打油道:“文朝丈庙两相疑,当路争论众更奇;白字先生查字曲,最后问我苏东皮。”讽刺了不学无术而又好为人师的腐儒,屡读错字丢人现眼的情形。
北宋理学家、名臣赵佧,进士出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称“铁面御史”。他对功名利禄淡泊如水,毫无恋栈之态,这从他退隐后的-首“打油诗”中可见一斑:“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诗里说,我已挂印退隐而去,这事稀松平常,官衔名位早成过眼烟云,想找当年的某某老已不可得,有的只是乡下赵家老四了。由达官显贵而布衣平民,角色转换反差如此强烈,但赵佧却能坦然处之,可谓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大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旷达。这首诗透露出的“个中消息”,表现了赵佧先生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洒脱,是历经宦海沉浮,生命航船终于泊靠故家锚地后的宽慰,是大象无形的超拔。相信他不会患什么“退休综合症”的,大概也不会千方百计发挥“余威”吧?

有一首咏石塔的“打油诗”,读来令人发笑:“远看石塔黑乎乎,上面细来下面粗;有朝一日翻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初看文句粗俗,其实粗中见巧,蕴有“置换法”的哲理在焉。被审视的事物,一旦主客体易位,那就另是一番气象了。咏石塔的作者倘是陈胜、吴广,就不仅不觉可笑,反倒深感暗藏机锋、奥妙无穷。因为这石塔的形象,正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那“有朝一日翻过来”,表达了何等的慷慨悲歌之情、腾挪乾坤之志啊!岂不是作者藐视王权、改朝换代的宣言?这时再看那浅近平实的文字,反倒具有了为惊世骇俗的真意作铺陈的妙趣,读之越发兴味盎然了。
由于打油诗不受格律限制,可以直抒胸臆,生动活泼,在民间广泛流传,脍炙人口。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率部驻防徐州时写过一首植树诗:“老冯住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读后不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更对冯先生关心民生、发展农林生产的良苦用心,顿生敬仰之情。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先生的诗,被时人称作“丘八体”,这首植树打油诗也保持了其“丘八体”的惯有风格,令人莞尔。
当今社会还流传着一些民间即兴创作的打油诗,讽刺社会弊端,描摹光怪世象。如“舌头不打弯,眼睛不打圈,抽烟不冒烟,说话不沾边。”“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