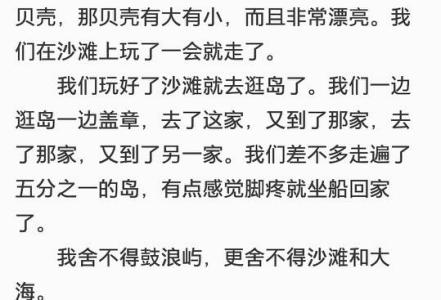鼓浪屿,单听这个名字就足以勾起你对它的美好想像。她仿佛是一名身着波希米亚长裙,波浪长发披肩,裸足浣纱的妇人。是西施,也是三毛。根基是有的,内韵是有的,美貌也是有的。只是今日,四下顾盼,难免失了骄矜。但又饱蘸世俗烟火,生命力顽强,是美人不肯迟暮么?
爱华阅读配图
鼓浪屿之好,舒婷说得很是美妙
舒婷可以说是真正的鼓浪屿人。对于鼓浪屿的情结,用她的话说,便是——“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
能在鼓浪屿成长、生活,对于你我行客而言,实在是好奢侈的一件事。对于鼓浪屿的认知,我一个行客自然不如舒婷看得真切,体悟得深刻,也定无法描述得如她妥帖。
她在文章《小岛也疯狂》里写鼓浪屿:“最不短缺的是阳光。冬天是蜜,夏天是火,秋天则是灿金灿金的铜笛。春天不好说。春天的阳光懂得迂回转折,工笔勾勒出梅雨、薄云和软风,是琵琶半掩的美人脸。”
文章《在家门口迷路》中,舒婷写道:“小岛色彩浓烈,由于它的玉兰树、夜来香、圣诞花、三角梅;小岛香飘四季,由于它的龙眼、番石榴、杨桃,甚至还有波罗蜜。这些大自然的宠儿被慷慨的阳光和湿润的海风所撩拨,骚动不息,或者轰轰烈烈,或者潜移默化,在小岛上恣意东加一笔,西修一角,增增减减,让一个拳头大的地方,坠住了千万游客的脚,使他们总也走不出去。”
鼓浪屿之好,苏婷说得很是美妙。
据说,鼓浪屿得名,是因鼓浪屿的老别墅前有一块中空的礁石,叫做鼓浪石。旧时,潮水上涨之时,波浪起伏拍击礁石发出声响,犹似鼓音。故因此得名。而今,礁石还在。而今,波涛还在。只是,鼓浪之声早已不曾耳闻。
那些斑驳又琳琅的旧物
很是喜欢王臣写的那本《一个人流浪,不必去远方》,书中谈的多是鼓浪屿的旧人、旧事、旧时风物。鼓浪屿迷人的除了海光水色,大约就是那些斑驳又琳琅的旧物了。
■ 鲁迅,来过这里。
鲁迅日记里有一则内容如下:“一月八日,昙。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它社员三四人,少倾语堂、矛尘、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夜大风,乘舟归。雨。”
当时,一如林语堂,鲁迅亦是应邀前往厦门大学任教,时间跨度为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后因校内学派争斗请辞。校内胡适一派与鲁迅一派意见相左,争斗激烈。鲁迅与林语堂等人请辞。在厦门大学的短暂经历对鲁迅日后生涯有重要影响。不入体制,只拿一支自由笔。
据说,这一则日记当中所记那日,鲁迅和林语堂一行人曾在鼓浪屿洞天酒楼设宴。甚至,有好事者自称记录下当时的菜单,包括:五香鸡卷、蚵仔煎、八宝鸳鸯蟹、白炒香螺、土豆仁汤等等。不知其真伪。
■ 巴金,来过这里。
1930年,初秋,巴金第一次来到鼓浪屿,与之初见钟情。在《南国的梦里》,巴金写:“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色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得年轻的空气”。

■ 施蛰存,来过这里。
施蛰存看到的鼓浪屿是抗战时期的鼓浪屿。他从黄家渡码头上岸,初眼便见难民。但沿着曲折马路行径,虽是乱世,但鼓浪屿上的生活程度依然要比其他地方高。
那一回,他还登上了日光岩。他写道:“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