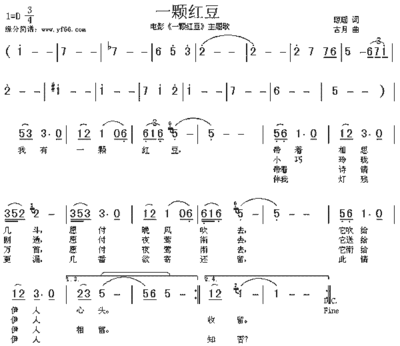01.
我一直不大喜欢吃馄饨,因为它的格调不够清。
一碗下肚,怎么回味都充满了白面的沉味和猪肉的腥味,和在一起,就是浊。与黄米清粥比起来,实在就像走卒之与隐士,差一个层次。
开始尝试馄饨是在看了一则广告之后。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年前的公益广告了。一个漂亮女孩下夜班回家,骑着自行车要经过一条漆黑的胡同。胡同口馄饨摊的老师傅看见了,每次都把悬挂着的电灯拿住,改变一个方向,照亮那条胡同。
我当时被这则广告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决定试一试馄饨。
后来工作之后,才发现这则广告就是对我的生活的真实写照,除了我不是一个漂亮女孩以外。
每次下了小夜班,打车回家,我总会让师傅停在十字路口,然后去那个早点摊吃一碗馄饨,再慢慢走回家。那个早点摊总是营业很早,半夜两点半就开门迎客,你都不知道这该算深夜还是凌晨。漆黑的夜中,独有那扇门透出光亮。进了门,老板在忙着打豆浆做豆腐脑,老板娘在揉一团很大的面团准备蒸包子。在这种忙乱的时候,下一碗馄饨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馄饨是温暖晚归者的最好食物,热热地吃了一碗下肚,所有的寒气都驱赶得一干二净,一并被驱赶走的还有工作中的烦恼,正好回家钻进温暖的被窝。
02.
十里河附近有好多残余的工地,满地碎砖乱瓦。但就算是这样的地方,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开在工棚里的小商店。
我楼下就有这么一处,从来没有进去过,也不知道它到底买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的指头上扎了一根刺,到处寻针,想把它挑出来,最后也没找到。下楼跑了好几家商店,都说没有卖的,最后路过这一家,我抱着试一试的样子去问了问,老板很好心地把他们家缝衣服的针拿出来了。那天的阳光很煦烈,我在门口,用那根针,把刺挑出来了。
借了一次针之后,才发现,这原来是家小吃店。墙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小菜、煎饼、混沌、小米粥。没错,写的就是混沌。
刚挑出刺的我突然笑了,一碗馄饨是一碗混沌,里面是不是还有测不准原理、薛定谔的猫之类的东西?
是不是吃一颗混沌,就是咬开一个宇宙?
我笑着笑着突然就笑不出来了,我想起了某天在小饭馆里吃馄饨,那个漂亮的服务员不知道为什么,红着眼眶从后厨出来,把围裙往桌上一堆,不声不响地出门去了。
一个老头从后厨追出来,无力地喊着,幺妹,幺妹!
我不知道她是受了什么委屈,只知道一贯开朗的她,原来也是会伤心的,也是会有脾气的。
其实后来想想,馄饨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食物。
所有的馄饨摊都是边卖边包,它们都是在车水马龙中诞生的。经营者的艰辛、早起赶路人的匆忙,都化作滚烫的一碗汤,就着寒风,落了无数路人的肚皮。中国这么大,南北饮食差异得几乎就要打起来了,可是只有馄饨都是一个味道,清汤、淡菜。一口吃下去,温温暖暖的。
吃一颗馄饨,就是咬开一个宇宙。世事的艰辛、谋生的不易,都在氤氲的水汽中,模糊了眼睛。
03.
说起包馄饨,我想起一个女生。那时候我刚写完年节碗菜,她跑过来问我还会什么。我说我会包饺子,山西样子的饺子,需要两只手捏好了再挤一下,出来就玲珑秀气,不是扁食那种呆头鹅嘴巴。她就想了很久,然后问我会不会包馄饨,我说不会啊。她高兴地拍着手,说,那我教你好了!然后活灵活现地表演起来,你看啊,左手要拿着擀好的馄饨皮,右手拿筷头蘸着馅儿在皮上舔一下,千万不要多,只舔一下就行!左一折右一折,最后再一折。然后就包好啦!
说实话,我压根儿没记住怎么包馄饨,只记得她那天的眼睛很亮。
不不过现在的她,已远在千里之外。

唉。
又一次下了夜班,我又一次坐在那个店里。
“来一碗馄饨。”
“好嘞!”
老板娘的动作麻利,虾皮、紫菜、芫荽都在碗里搁好了,再倒半碗汁水。把煮熟的馄饨盛进去,热汤一冲,香气四溢,十个馄饨像十朵百合,挤挤挨挨地,浮起了碗面。
我慢慢吃着馄饨,看着操劳的店主,和窗外漆黑的夜色。心想,要不然,来生做一颗馄饨也不错。洁白行世,怀着一颗肉心。在热水中洗一个澡,闻着最紫菜与虾皮带来的遥远的海的味道,去温暖每一个夜色中匆忙的行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