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只有主动向它走去。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地,但可以决定事业版图在哪里。只有不断扩大我们的工作半径,才能在市场中找到新机会。
早年,台湾以出产中小企业家出名。他们或者文化不高,或者其貌不扬,或者英语不通,但是提了一个007手提箱,里头装着公司的产品样本和目录,就敢飞到全世界去找客户。甚至,台北的松山机场30年前还飞国际航班的时候,经常有中小企业主拿着写着“我的公司卖××产品”的英文牌子,站在山口,吸引那些刚下飞机的国外客户注意。
商人无祖国,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战场,也是市场。这一点,台湾创业家和浙江、广东的商人很像。100年前,广东商人是最早跑到海外做生意的,檀香山、旧金山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近20年,浙江商人则进一步把足迹扩大到世界各地。对创业家和待在创业型组织的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半径不是由地理条件来定义,而是由商机条件来定义。台湾近几年来的创业风气越来越不如前,与其说是创业家失去动力,不如说是当外在环境改变后,整个社会还没有找到对应的方法。
举例来说,13年前,我刚投入新闻业,那是台湾财经媒体的黄金年代,比尔.盖茨、安迪.葛鲁夫、迈克尔.戴尔、约翰.钱伯斯和杨致远等人,都会到台北来,我有80%的工作可以在台北完成,世界会自动走过来,新闻资源丰富。如今,这些人和继任者很少到台湾,但是媒体同业却仍然留在台北,希望完成80%的工作。他们的工具更好,有录音笔和数码相机,电视台记者则配备了SNG车,可以随时直播新闻,却面临新闻资源少很多的窘况,只能靠整点新闻一再回放同样的材料。
企业也面临类似现实。台北工作者愿意被外派的比例,低于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以经常移动方式工作的比例,也低于这四个城市。越来越多高管的名片上印着两个或三个城市的联络电话和地址,台北的高管大多只印着一个。其他四地的高管把频繁移动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台北的高管却将之视为出差,心态上有很大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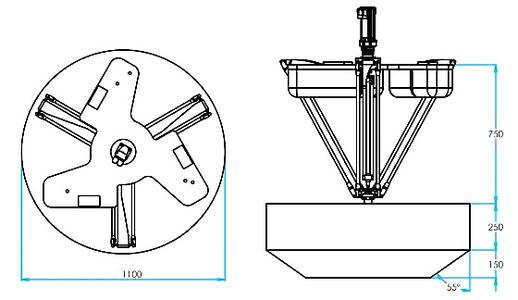
经理人的价值,如果仅在一个地方兑现,那上升空间就有限;工作半径越大,代表价值被需要的范围越大,上升空间就越大。你的工作半径有多大?10公里、100公里、1000公里还是10000公里?你的移动频率是多久?一年、一季、一月还是一周?与其他四地相比,台湾经理人在工作半径和移动频率上都落后,他们的薪水比不上香港和新加坡,领先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也在急速缩小。他们就像“植物”,顶着头上一小片天,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矿物”,能够被搬动,却非出于自愿,很少有主动到处觅食的“动物”。
(爱华阅读配图)
最近我到深圳大学EMBA讲课,班上都是三四十岁的经理人,其中有两位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来自鞋厂,公司在西班牙设厂,她经常要到当地帮忙,但一到夏天西班牙每天工作时间不到5小时,节假日又多,订单满载却出不了货,不知如何解决。另一位来自石化厂,他的公司在印度和韩国都有设厂,但印度当地的卫生条件差,韩国则是生活成本太高,他不知该如何说服同事过去。以我在北京和上海的见闻,我相信深圳这一班学生不是特例。
另一次,我受邀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主题是“全球化下的传媒行业演进”,我举了不少台湾的例子。问答时间,一位学生举手问我,台湾的媒体是否有“反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绝大多数的电视台和报纸,报的都是地方新闻,国际新闻的比例很低。这个题目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曾经一度以世界为家的台湾工作者,如今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而传媒反映了这件事。
台湾有很好的创业传统,从中产生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在培养专业经理人这一方面却没有跟上。台湾很少有能管理50亿美金以上规模的经理人,因为超过这个规模的企业极少只在一地运作,必然是跨国企业,需要大的工作半径。当世界距离我们更远,我们只有跨出去走向它,别无他法。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地,却可以决定自己的事业版图发展到哪里。创业就像革命,是要改变现状,而不是接受现状,如果连自己的心态和工作半径都无法改变,要改变现有市场的结构找到新机会,那是缘木求鱼。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