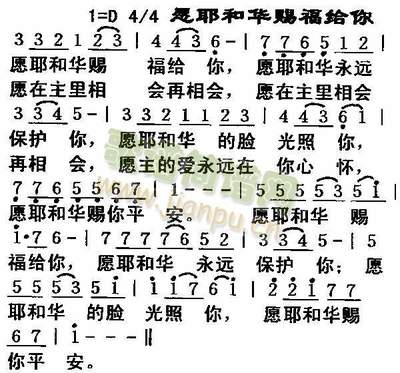《晋书·本传》开列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奇人、异士和疯子。“贤”怎么解释?当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吧。显然,把这乖张、怪异的七位哥们儿称为“贤”,是对汉语的一大嘲讽。说白了,所谓“竹林七贤”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虽说他们都有一点文化功底,也有造福黎庶的雄心壮志;可惜,当局不买帐。于是,这哥儿七个立刻暴露出三大致命弱点:一,脆弱。二,自恋。三,放荡。这种无功于当代的“废人”,居然被捧到了“圣贤”的交椅上——凭什么?显然,又是历代成群结队的失意文人,涂脂抹粉。倘若历史真的掌握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家伙手里,那么,华夏文明将熬成一锅 “烂炝汤”。
且看所谓“七贤”,曾怎样在魏晋的“竹林”里“耍活宝”:
嵇康爱骂街,公开和司马政权唱对台戏,还当面奚落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最终被推上法场,身首异处。据说,嵇康擅长弹琴,临刑前,还当着三千太学生的面演奏了最拿手的《广陵散》。死,如何慷慨悲壮已不重要,关键是他以言罪人,白白拼上了性*命着实可惜。斗争与借口无碍,但与方式有关。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没有任何自卫的武器,只图一时痛快而引颈就戮,世人就有理由怀疑他无畏背后的真实性*。即使逃过司马氏这一劫,也还有更糟糕的结局等待他。嵇康与那个时代实在是格格不入。他根本不能替老百姓做点什么,只有添乱子、找麻烦、徒增谈资的份儿。
阮籍稍微温和一些,他“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整日纵酒谈玄,却从未泯灭那颗高傲的心。“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他所谓的英雄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做英雄的机会,你拒绝;当一介草民又不甘心,对别人的声望和成就一脸的瞧不起。那么,当时势造英雄的关口,你在哪里呢?喝酒,清谈,说风凉话……《论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与司马政权不共戴天,干脆不为政治浪费唾沫,何必还吃一个、看一个呢?对常人来说,“哀大莫过于心死。”而阮籍这样的人,则“哀大莫过于心不死”啊。
刘伶是彻头彻尾的醉鬼,这几分深沉的醉意增加了他隐士的风度。据说,他常乘鹿车出游,随手携带一把酒壶,身后,跟着一名荷锸的仆人,刘伶吩咐过:“死便埋我。”《道德经》有这样的语录:“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患?”刘伶不眷恋这副臭皮囊,死了更清爽,索性*躲藏到对头与时间都找不到的地方。
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竹林七贤”空有满腹才学、一腔报国之志,可惜,生不逢时,寻求不到政治上的合作者。退一步,即使能达成两相情愿的合作,以 “竹林七贤”的性*格,久居人下恐也难以长久。说时势造就了他们的隐士身份,还不如说性*格左右了他们的命运走向。嵇康鼓吹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根本就不是巍巍庙堂上的主旋律。明知报国无门,还念念不忘“封侯印”,加倍的痛苦使这七个人选择了比原来更夸张、更慢世的生活方式:纵情山水,酗酒吟啸,抨击时政,臧否人物。aIhUaU.com
隐遁,反倒招来世人注目,或可认为他们夸张的表演纯系一种“行为艺术”,一旦找不到识货的买主,就枉费心机。姜尚、孔明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幸运者;而大多数更有才能的隐士,只能像“竹林七贤”一样,“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人才,也从来不在乎埋没人才。你生、你死、你做五花八门的夸张表演和 “行为艺术”,没有权门来捧场,最终也是无谓的挣扎。阮籍的《咏怀》诗可见这种没有观众的凄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再牛的人物,也是肉做的。没有观众的时候,就不需要表演了。卸妆之后赤裸裸,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