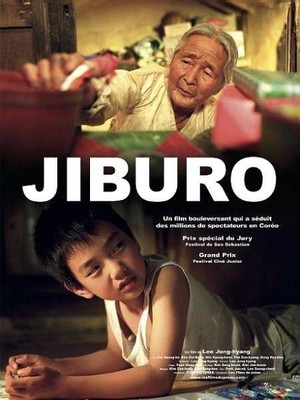外婆在我的印象里只残存零零星星的记忆,只记得我和娘站在窑垴畔呼喊她,她会踮着小脚笑盈盈地说一句:“是你们来了,我说早上喜鹊怪叫呢。”
外婆长得不如我母亲漂亮,但她的言语里透出一股阳刚气,这一点与现在的我说话为人如出一辙。小时候,母亲一回娘家就会带上我,那些个小姨姨小舅舅整天缠着让我给他们表演跳舞唱歌朗诵诗文,还出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考我。只要我答对能让他们满意,就赏我一个拥抱一个亲吻。每遇这时,外婆就照着母亲平日里的口气捧我一番,我在极害羞的心情下只好为外婆圆场,更卖力地做一些折腰劈腿翻筋斗的绝活赢得众人的称赞。于是,在小舅舅小姨姨们的簇拥下,外婆会不避讳表兄弟艳羡的眼光塞给我几粒糖果,或是平时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点心。那时的我真是幸福极了。当然在母亲的眼神指使下,我也会分给表兄弟们一点。
因为能深得外婆的疼爱,我非常喜欢去外婆家。有一段日子,因为农活忙,母亲将我寄居外婆家十几日。在那漫长的十几个日日夜夜,我都能感受到外婆给我超乎寻常的爱。白天,她一日三餐都能按时让我就餐;晚上,先安顿我早早睡了。在漆黑的夜里,外婆能活动手指头用麦秸筒掐编一种用来编织草帽草洞等精致的麦秸条,那时称“掐麦秸”。在麦秸筒上蘸了水,使麦秸筒变软,然后操作七根粗细相当的麦秸筒,织成宽宽的约摸一厘米宽的麦秸条,以“框”作单位,从手臂到脚跟缠上十五回为一框。我悄悄用被子蒙住我因想母亲而哭湿的脸。“嘣!”外婆狠劲地甩出刚捞出水盆的麦秸筒,一大片水珠停留在我的额头上。我顺势赶紧一并擦去泪水。
“你哭了?”
外婆那洪钟般的声音把我吓傻了。
“没有。”

尽管我的声音微弱至极,但还是逃不过坐在漆黑夜里正做活上劲外婆的第六感觉。她放下麦框,点亮了油灯,揭开我的被子,将我抱在怀里。我再也抑制不住:
“外婆,我想妈妈,我要回家!”
“不哭不哭,可怜的孩子。”外婆一边为我擦泪一边说:
“还不是你那老子不成人,离家不管你们死活,害得你妈既当男又当女,把娃娃也受的。”
听到外婆骂起了父亲,我很生气,强硬挣脱外婆的怀抱。外婆长叹一声,为我掖好被子,开始了长时间的啜泣。
幼时的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外婆是在哭什么。我在想我的妈妈!她呢,也一定是想女儿了?时隔多年,自己身为人母,也有了不痛快的家事,特别是在十几岁失去母亲,没有人会为我哭泣。这种被爱遗弃的失落疼痛犹如一把刀剜在我的心坎上,让我常常一个人暗自哀怜。因母亲生前在家境困顿时会时时提念起外婆五月四日的祭日,故,思念起母亲就不自禁想念已下世三十载的外婆。虽然外婆在我的记忆里只保留着模糊的极少的片段,可是在母亲为她戴孝奔丧走的那个晚上,我的一碗米钱钱饭因为眼泪的参与由甜甜的清香变为咸咸的苦涩永不消失。对于这一代一代生命延续的亲情激发我去追忆思索想念。
去年夏天,我因表兄有病前去探望,在给外婆上坟后回家,两位妗子亲热地送我出门,而我却把脚步挪到了另一个方向。那宽敞的大院里不再是我和表兄弟们嬉戏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老黄牛哞哞的高叫。我很迟疑地对两位妗子说:
“我想下去看看我外婆住过的那孔窑洞。”
两位妗子显然有些发愣,我已是含着泪向她们解释说:
“我每次来总要去看看的。”
透过门缝,窑洞里尽是横七竖八的柴火,我极力搜寻着外婆坐过的土炕。地上那一只红红的木柜在柴火的挡架下,为一只无家的蜘蛛成全了一个安乐窝。就是那一只落满灰尘的木柜,外婆不只一次打开它,取出我在自己家里吃不到的好东西。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滴落在门框上。我用心在高叫“外婆,外婆!”
我知道,外婆早在三十年前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可是,我的记忆里总是遗存着我母亲常常为她没有做好女儿的歉疚。现在,母亲也走了,她们可以在一起了。可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的,没有人会为我流泪。所以在呼唤外婆的同时,我正是在呼喊着已是离去整整二十周年的妈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