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意义在于,性欲和暴力得到了统一整合。从个性发展的角度来一看:当年金庸小说的热门预告了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心理治疗的热门。
金庸的小说意义在于,性欲和暴力终于在其中,胜利会师,得到了统一整合。
而在既往的中国小说,男性形象中一般都是半拉子男人——会做爱的男人必然不会做事,如许仙和宝玉;会做事的男人必然不喜做爱,如关公和李奎。偶尔有个把男人既会做爱又会做事,此人必是流氓不得好死,如西门庆。
故有文学评论家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是流氓的颂歌,宣扬流氓的道义,其实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正如1980年代,一众中学老师,宣称金庸的小说是毒草,毒性甚至胜过琼瑶,虽然这主要是说明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失败,教师们完全不知道如何帮助青少年整合性欲与暴力,从而面对性欲陷入了一种偏执状态。
但是那偏执的嗅觉,的确也是准确嗅到了金庸小说中性欲的芬芳和暴力的馥郁,正如性压抑者能够从“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唱哪”,从“海风你轻轻吹海浪你轻轻摇,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中听到暗流汹涌的性冲动一样。
金庸小说有三大特点:
1、所有主人公都是男的。 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小说。女性基本上都是这些男性英雄的陪衬。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些男人之所以那么需要出人头地,万众瞩目,是不是因为他们从未感觉到,自己的真实自我,被人看到过,欣赏过呢?
换句话说,他们正如《天龙八部》中的白夫人,不管有多少高富帅乞丐盯着她看,充满艳羡,但是只要乔峰,这个乞丐中的CEO,忽略了她,就立即引发其自恋暴怒,为了保护那脆弱的自恋,她必须摧毁整个丐帮(在她幻想中是夺取其客体关注者,是其嫉妒和攻击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狠狠折磨忽略者乔峰。
2、绝大部分男主人公都没有父亲,大部分人都是孤儿。
这大概部分解释了第一个特点,正是有弃儿情结者,才最需要无边的功名利禄,来填补自己那永远填补不了的自恋创伤空洞。
不管多少钱、多少名气,也无法让这个痛苦释怀,为什么当年我的父母忽略我、不要我、离开我?
但是金庸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都是那么创伤性的,这一点和陈青云、古龙的小说显然不同。后两者的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受困于弃儿情结和空虚感。而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感动一大批人,就在于其主人公的精神结构,具有较高的时代象征性——他们象征着写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父性权威的弱势,而不是父亲的死亡或彻底消失。正对等于1990年前的时代文化无意识结构,父亲的权力虽然被阉割、被贬低、被攻击,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切看起来可笑、过时的理想主义精神。
而金庸小说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其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有理想的,郭靖是典型象征。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按照时代顺序,一个比一个理想丧失更严重。
陈家洛是典型的君子,郭靖是大侠,都认同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到了杨过,令狐冲就成为隐者了,但是仍然具有一些个人主义的理想——如爱情,这一批人类似于1980年代以前的青少年。然后以张无忌、石破天为代表的是,充满身份认同危机感,这类似于当代的青少年。最后登场的就是韦小宝,一个纯粹不知理想为何物的人,他让金庸笔下的男性,再次回到了西门庆的水平。
其实近几十年来,中国男人的理想,一般来说,最高的也不过就是家国梦,民族振兴而已,类似郭靖。退一步的就是找个红颜知己过个好日子,就是杨过,令狐冲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有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也无非是买大车买大房,买个公众承认的大名气,和韦小宝无二无别。故有评论者惊呼。韦小宝可以和阿Q媲美,为中国国民性代表。
3、也是最重要的,金庸笔下的英雄全部都是个性化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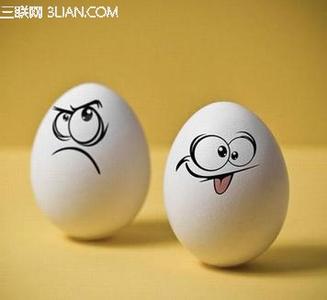
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一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像《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都是在一个英雄群体中,稍稍有点自己的个性,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忠诚侠义的代言人。
金庸小说的结构,其实更类似欧美小说,一部小说从头到尾,围绕着一个主人公来写。个人,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心态变化,成为了小说的主题。当然,《金瓶梅》也有这样的影子。
但是金庸小说之主人公,个体性都比西门庆要强烈很多倍。
西门庆的悲剧中,最悲催的就是西门庆从来不反思,其生命何以如此空虚,如此毫无意义。
而金庸的主人公,即便是郭靖,也会反思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自己理想的正当性,更不用说在爱情选择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这一点不知要让贾宝玉羡慕多少。
从个性发展的角度来一看:当年金庸小说的热门预告了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心理治疗的热门
荣格区分了两类心理治疗,针对集体人的心理治疗 和针对个体人的心理治疗 。
集体人就类似于金庸之前的侠义英雄,他们没有隐私,心胸向集体敞开如雷锋,晚上睡觉不需要关门,可以供集体参观。他们出心理问题,往往是因为脱离了和集体的联系。所以适合他们的治疗模式,也就是集体化的,如培训班、工作坊、个性成长小组、团体心理治疗等等,即便他们做个别治疗,也最好是提供一套集体承认的、标准化操作给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每一步都由治疗师扮演一个好老师,教给对方。
集体人只要找到集体归属感,心理疾病就好了一大半,所以他们去信个宗教,去上个课程,学个乐器,开个微博,也可以打发走好多空虚和无意义感的,不一定要做心理治疗。
个体人则不同,他们做治疗,是因为他们有隐私、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和情感,如他想和他姑姑结婚,这些内容需要一个治疗师承诺为之保密,而且这个治疗师承诺,不管这些内容多么惊世骇俗,不为世俗道德不接受,治疗师都和来访者一起尽力去理解它们。
集体人看到的都是集体标签,如灭绝师太一般,看人先看他出身标签,是名门正派,还是邪魔外道,而个体人注重的是,我和这个具体的人的关系。如张无忌对赵敏。
正是因为一个人成为了个体人,他才要整合自己的性欲和暴力,他要反思自己暴力的正当性,考虑自己性欲的实现途径。而不是把这些事情,留给周围的哥们,留给师傅师兄来安排。
但是,从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的象征意义来看,中国男人个性化历程大概是后果不妙的。
《鹿鼎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具有了强烈的个性意识后,最终他成为了一个纵欲者,如西门庆一般,因为他的文化中并没有任何体系可以吸收这个个性化能量。
《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要比《鹿鼎记》乐观很多,它描写的贾宝玉个性化的结局是——入道修行。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是允许个性化因素得与伸展的体系。
到了金庸写作的年代,这种寄托自由和个性的体系,在知识分子心中已经降格为江湖格斗了。
接下来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刘心武续写的《红楼梦》,贾宝玉的个性化历程居然是通过自己自创一门残缺不全的宗教来解决。
知识分子们在书里面幻想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心理治疗室里面实践的东西,不少人把治疗师当做人生导师,也把治疗关系当做灵性伴侣的关系。
这正说明了,治疗空间,正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如金庸小说中的“江湖”,如当代网络小说中的“修真”和“穿越”,如周杰伦式的rap和崔健式的摇滚乐,是一个寄托自由、孵化个性的空间,但是在一个缺乏支撑自由和个性的文化体系下,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最可能结局,却是成为一个流氓。
这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不少艺术家,最终成为了流氓的文化无意识原因。当然,也是不少老牌心理治疗师最终成了实习期流氓的原因。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