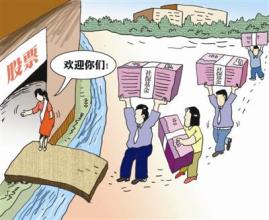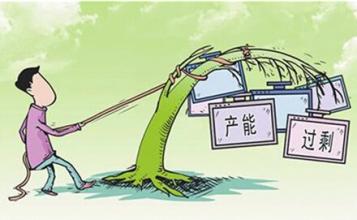一箪食一瓢饮,即可维持日常,几间房几亩田,足以糊口养家。说来简单,实则不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且是当务之急。人皆欲望动物,屈于物,折于势,爱生恶死,本性矣;人皆社会一员,扰于事,苟于进,驱名逐利,随流也。通过收藏满足贪欲,积累功名,聚集财富,耳目声色,游玩嗜好。其实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对欲望的控制。

既处群体之中,难免攀比。上半辈子比学历、职位、薪金之高,挣的钱都押给了房产;下半辈子比血压、血脂、血糖之低,挣的钱都捐给了医院。关注飞得多高,漠视飞得多累,攀比者实际只见他人,不见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莎士比亚则以文艺语言喻之:“当我们还买不起幸福时,不应走得离橱窗太近,盯着幸福出神。”圣贤有诲而弱弱,却是意味深长。财富占有,一时满足而已,时过境迁,便又陷入更深比较,手里有粮,心里也慌。收藏欲望如吸食鸦片,越多越上瘾。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盖戒贪之语也。
爱华阅读配图
无忧莫愁,至乐之域,一心无累,四季良辰,此等境界,惟幼年世界方得有。一天一成长,一日一世界,为过去赶着走,被未来牵着活,米兰?昆德拉无奈道:“生活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欲望中。”生活赐予梳子时,头发早已脱落,纯真就此无影无踪。何为纯真?好好吃饭,天天睡觉。
流光容易把人抛,樱桃芭蕉,终难找回。纯真之类但被抛却,便已摔得七零八碎,没法拼凑,但被搅合,瞬间杂成五颜六色,无以提纯。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日常生活几乎都在斗室打发,其他区域的存在几乎与之无关。有多少困乏,由于行李拖累,有多少疲惫,源自无谓竞争。
自叹不如梁上燕,一年一度也归巢,一生都为找回纯真写作的安徒生,临终道:“别问我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他的趣味能够影响孩子,却无法涉及成人。荣格说:“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从四十岁开始。”守贫似病医无益,习静如禅悟却难,除非失忆,否则没有第二次生命。太在意别人看法,无疑便是活给别人,结局要么累死,要么被整死。
世间哪有永恒的圆满,“诗囚”孟郊、清雅词派开山之祖姜夔、“金陵八家”之首龚贤等文人,死后无钱下葬,或情有可原,一些官员靠友人资助入殓,便为稀奇。雍正帝师顾八代官至礼部尚书,死后竟无钱下葬,只得由皇四子出资举丧。道光年间的河官黎世序,忧心劳瘁于江浙治水工地,其为官清廉,死后也无钱下葬,百姓联名上书,朝廷赐之太子太保,竖功德碑。门开杜径,室距桃源,虚堂留烛,日有三思,其在物质欲之外,皆找到了精神欲。在自己的生活里活得足够专注,便不会再留意他人的目光。
靠自己博人生,不谋求能力以外的收获,此为成年人的守真。梭罗说:“如果你富有,就像枣树一样慷慨;如果你无物慷慨,就去一株柏树那样:简单、安适、自由。”铺路架桥建学堂之外,排难解纷,济人利物,方为日行之善。仗义疏财,有时是对良心的拷问;施舍周济,或许是对贪婪的纠偏。福至祸至,祸生福生,务名者害其身,多财者祸其后,世人皆知此理,临场不由自主,依旧故我。
居尘而不染尘,不欲何贪;处俗而超脱俗,无贪无求。畏能止欲,足能止贪,人之制性,如堤防之治水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