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镜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指的是摄影家或摄影者爱好者拍出的有悖于常理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应不同社会、不同层次的行为,他们拍下来,以警示世人的作用。这就是所说的黑镜头了。
黑镜头-时间中国
幸福路・永定门
摄影/文/孙京涛 1994-1996年
事隔十载,幸福路的这种景象在首都建设和治理的炽热浪潮中已经淡出成为晦涩的过去,在今日的整洁和秩序中,我们应该有一种关于他们的清晰记忆。
在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西面,有一条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长,街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倚着被烟火熏得一团漆黑的砖墙,满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砖头搭起的窝棚。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衣衫褴褛。
小街口上只有一个门牌号:幸福路18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门东滨河路,那栋六层的红砖楼,是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门接济站”。从这里往东不远,先农坛体育馆西邻,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幸福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国各地来首都上访告状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这条小街,于是,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条小街以及小街周边地区的上访者。
从古到今,海内海外,信访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单单是哪个国家的事。在我国古代,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便逐渐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诉的制度。我国周代就有了关于“路鼓”和“肺石”的记载。目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部门,到80年代初,全国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就达到了约三十万人,其中法院系统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访部门有62个,这足见党和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大凡在幸福路落脚的上访者,虽然来这儿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刚走进幸福路的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个上访的人是杨建峰,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进京上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刮旋风呢!”他开玩笑说。他的冤情是“被无理劳教”,“简直冤枉死了”。
从山东沂源来的段连玉称,1989年6月2日,与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为理由,将他14岁的儿子开枪打死。他的诉状上写道,当时王离他的儿子只有十几米远,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上衣,王的行为纯属蓄意谋杀。案发后,当地法院以误伤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后,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结核而保外就医。“这个人就仗着他的亲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为俺不服上访,他还打伤了俺6岁的女儿,法院判他支付给俺的四千块赔偿费,他一分也不给。还说什么‘你就是告到江泽民那儿,我也不怕’……”
东北人吴永财自称是名转业军人,二十年前,他所在县的县长非要他娶其患有软骨症且痴呆的女儿为妻,吴不肯,便遭到报复。他说他因上访已被强制劳教了3次。
穿着体面的罗洪山是辽宁省瓦房店三台乡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笔“陈年老账”:1977年,他被原复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后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狱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离子散。他说,前不久法院判决给他2.1万元的赔偿费,但他的公职却无法恢复,他不服,继续上访,“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
从山东新泰来的吴文江称,1986年他在辽宁省阜新花了2.4万元钱买了一辆“黄河”牌卡车,没成想原车主以次充好―这本是辆已经报废了的车。在对方往山东送车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亡两人,同车的吴文江也受了重伤。吴想追回已付的钱款,未果。而由于吴买车欠了五六万元的债,妻子与他离了婚。我问他:“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说:“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官司打不下来,我也没法回去,什么事也干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只能在这里死磕……”
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诉状中诉说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诬告“持刀强奸”一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妇女,从此,曹的一家便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缢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长子和三子均系牢狱。曹可玉历尽千辛万苦,上访十年,上访的单位包括国务院、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铁道部等十几个接待部门,终获昭雪。但是,“就给我那么一张平反判决书就拉倒了?”老人继续上访,要求赔偿。在诉状中他写道:“这是我最后向国家呼喊,请求政府能安抚我一颗受伤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家三代能从此安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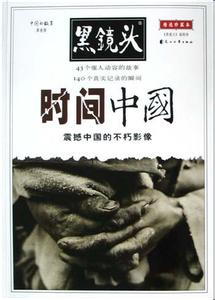
从河南新郑来的程兴珂是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她的诉状中陈述的是一桩催人泪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仅6岁的女儿被恶徒高健民强奸,然后,高犯又残忍地将孩子掐死,最后又用石块砸碎了孩子的头颅,这个案子发生在高健民因强奸一8岁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医期间。在犯罪事实确凿、高犯亦供认不讳的情况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重判处高犯“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二审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认了一审法院审定的犯罪事实后,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改判为“死缓”。个中原因,无法言说,女儿的死使程兴珂一家痛不欲生。因为程兴珂已经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孩子的父亲觉得生活无望,程兴珂哭瞎了双眼,他们不服终审判决,拄着棍子先后60次到省里上防。1991年,他们变卖了家产(6000元),进京上访,发誓要求中央能依法处以强奸和杀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极刑。
“寻找青天”,也许是这些进京上访的人的共同愿望,至少也是他们能在北京逗留的借口,而北京也是他们的问题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许多人都在诉状中写道: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我坚信共产党富有实事求是,救死扶伤,永放革命人道主义光辉”(原文如此);
“只有党中央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我就什么时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根据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基层法院,信访重复率平均为30%,中、高级法院要超过40%,甚至达到70%~80%。据于振安同志说,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庭长纪敏估计,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问题的,大约在10%左右。这些抽象的数字所带来的具体的结果是:许多人来来去去,反复上访,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过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上访老户,而他们的问题也越拖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但即使在这凄楚的上访路上,仍然会发生些令人感动的人间之情。从河南来的姓刘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从辽宁来的张姓上访者,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在自觉上访无望后,两人买了辆板车,靠收废品度日。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刘大嫂说,她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负?”
74岁的刘增老人因脚踝被车撞伤,躺在幸福路上没法动弹,其他上访者便把他们弄来的食物分给他一些吃。老人在这里支撑了111天后,死了。
这样的生活使很多上访者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了这身心的双重折磨,寻了短见(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访者从接济站的五楼跳下,自杀了),还有一些上访者在问题解决后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惯了,便依然在北京游荡……
不管怎样,在目前,信访制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它毕竟是老百姓与上级政府和法制机关通气的一条途径,信访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证这条途径的畅通。
这群人最前面是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拄着拐杖,在本应上学的年龄里,他们都随着家人踏上了上访之路。可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透露出和同龄人一样的好奇和天真。在靠后的位置有一个举着材料的僧人,本应该无欲无求的出家人看来也有好多话要讲。左面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可从他脸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扭曲的表情。在后面的墙上的几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字“上访之家”,明确地解释了这群人的身份。
1995年炎热的夏季,74岁的刘增因脚踝被撞坏,在幸福路上呆了111天后去世。
幸福路上到处都是这些露宿街头的上访者,这种情景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上访者的表情非常执着,从他衣服上不一样的扣子可以看出他生活虽然艰难,可并没有使其失去尊严。
一位老者正在一笔一画地写诉状。据说,在上访前他并不识字。从这双手可以看出他上访时间已经不短了。
这是两位上访者的家,在上访路上他们同病相怜产生了感情,靠捡垃圾养活两个孩子,并发誓要供他们考上大学。
希望工程
摄影/解海龙 文字整理/张 杰 1991-1993年
如果说有一个人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撼天动地的运动的话,那就是解海龙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解海龙在农村采风时注意到很多孩子想上学而上不了学,促使他产生了要设法拍下这些贫困孩子是如何渴望读书的想法。当时青基会正在准备开展“希望工程”的活动,意在倡导大家“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用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解海龙得知后,便跑到团中央请缨,要为“希望工程”拍片子,如实反映中国农村失学孩子渴望读书的现状。他认为城里人看了他拍的片子不会无动于衷的,只要他们帮一个孩子上学了,他的片子就没白拍。
1991年初,为了用照相机把那些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而不能入学受教育的情况记录下来,解海龙买了地图,东拼西凑,找了一些经费,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采访。
解海龙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大别山老区,拍摄了一批感人至深的照片,诸如“大眼睛”小姑娘,“小光头”,流着鼻涕喊“我要上学”的贫困失学孩子的照片,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上学,妹妹哭了的照片,甚至于还有为攒学费而背砖的小女孩的照片等等。那一年,解海龙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马不停蹄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他就往南跑,天冷他就往北跑,专门去体会孩子们的辛苦。费用紧张时,他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就这样一路艰辛地拍下去,到1992年4月份他返回北京,终于拿出了整套的东西交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以此办个展览,于是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五十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很快,几乎天天都有解海龙的摄影作品在各种书刊里出现,随之在当时还产生了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 开始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10月,解海龙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湾两地展出。当时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国内外名家荟萃。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解海龙的照片却引发了强烈反响,10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着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希望工程”真诚的道义支持,解海龙第一次感受到了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十天之后,影展结束。华北油田将解海龙的影展搬到油田继续举行,随后那里又掀起了结对救助失学儿童的高潮。武汉一家婚纱影楼搞店庆,老板取消了原计划好的宴请活动,用这笔钱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这之后,影展又接着在广州、珠海、青岛、上海、合肥、香港、澳门等地巡展,所到之处,即起轰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的巡回展出共展出八十多天,在台湾轰动一时。
在老师的帮助下过河的学生。 1991年
展览过后,人们纷纷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八个月时间收到善款上亿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捐款数万元。捐款源源不断,日益剧增,每年数以亿计,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悬挂了解海龙的照片,北京地铁火车每节车厢贴满了解海龙拍摄的宣传画。看到此情此景,解海龙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本想这些照片不会顺利发表,没想到却能及时发表并引发了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这些捐款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别人比他们更难。这些都让解海龙深深感动,于是他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参与进来。
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孩子们读书却很认真。
1991年 4月
回顾以往,解海龙曾感慨地说,拍摄条件艰苦并不是他最大的困难,困难的是他所拍摄这一专题,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提倡主旋律,要求摄影家多拍、多表现明亮的一面。可这个专题记录表现的全是土老破旧、老少边穷的教育现状,照片非但不能发表,而且还会惹来麻烦。在这样的压力下,解海龙仍坚定地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不能眼见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解海龙被完全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他也要坚持做下去,惟有把这件事做好,他也就算不枉拿十几年相机了。
甘肃省渭源县聂家山小学,一场暴雨摧毁了教室。
孩子们眼睁睁地盼着能有一间再让他们上课的教室。1992年
云南省红河县虾喱村垤玛小学,校舍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危险,学生们只好露天上课。
1993年10月
湖北省宏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一场春雨过后,
教室一片泥泞,可孩子们仍然在这“湖心”小学上课。
1991年4月
贵州省水城县花噶乡中心学校,这些孩子离家四五十里,
他们寄宿在学校,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做饭。1993年10月
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贫困地区的教师为贫困土地上的下一代
不再失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戴红英老师的丈夫在中学教书,为了工作,
她只好背着孩子上课。1987年4月
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大店子村的孩子们,烤烤冻僵的小手准备继续上课。1991年12月
在农村拍片时,解海龙经常遇到麻烦,备受冷落,地方领导不愿意解海龙给他们“曝光”,也不认为这些图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这样一来,进度很慢,车子找不到,解海龙走路便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解海龙在一所刚下过雨的破旧学校拍照片,但没曾想他被一位年轻教师误解,扭打之中,弄得满身泥水,让他心里很难过。教师们的生活很清苦,每月工资不足几十元(还要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垫付),可一旦他们见解海龙拍照,心情总是不悦,生怕给社会丢脸,于是便百般阻挠。尽管这样,解海龙仍不改初衷,依旧爬山涉水,风来雨去地四处为失学孩子们奔走拍照,每到一处他就被那些穷苦孩子祈盼上学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个心酸的故事没有溶化,又一个心酸的故事便哽在他的心头,开始,解海龙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钱给他们,但他很快发现,那样做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必须通过真实的照片来唤醒更多的人来捐资助学,于是他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让他们尽快得到失学救助。
贫困母亲
摄影/文/于全兴2001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所记录的,不仅有那些困厄中凄苦的面容和眼泪,更有中国妇女那种坚忍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2001年1月2日,我在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及家庭报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就中国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情况和生存现状进行采访。
历经一年,从白雪皑皑的高原到奔腾咆哮的江河,从荆棘密布的丛林到荒凉无际的大川,足迹遍布中国西部9个省市,走访了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以一个摄影记者的亲历,见证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我看到,在不发达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她们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她们在抚育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堪忧―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改善中国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而努力。几年来,在海内外各种组织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业绩。部分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已经摆脱了贫困和正在摆脱贫困,那一张张欢喜洋溢的笑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执著。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
措吉,67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全家9口人,1995年年底雪灾发生后,政府救济牛羊,现有40头(只)牛羊,吃粮少量靠政府救济。
顾彩莲,26岁,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人。全家4口人2亩山坡地,今年收了不到500公斤的苞谷,家无牲畜。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100块钱。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把,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嘎松卓玛,24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家里的 href="http://www.baike.com/wiki/%E5%9B%BD%E9%99%85%E6%85%88%E5%96%84%E6%9C%BA%E6%9E%84" class=innerlink>国际慈善机构先后救济其全家5头牛。现家里已有10头牛,但吃粮还是靠政府救济。
王小盆,27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4口人2.3亩山坡地,全年收苞谷350公斤、红薯100公斤,无牲畜。家里已经7年没有杀过年猪,她说,农闲时她每天上山挖药材,今年卖了40块钱,过年的时候用这些钱买肉给孩子们吃。
王五女,30岁,宁夏西吉县兴平乡王堡村人。全家4口人10亩山旱地,去年收成150公斤荞麦,政府每年救济籽种,无牲畜。丈夫得病卧床在家,不能外出打工。
刘引引,31岁,甘肃陇西县福星乡鹿鹤村人。全家6口人8亩地。去年大旱颗粒无收,丈夫外出打工贴补家用。陇西县地处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吃水靠雨水,家穷建不起水窖,她每天要到2里地以外的大山沟中挑水吃,挑一担水需要一个小时。
覃纯菊,38岁,全家4口人。九年前丈夫耐不住大山里的贫苦生活,抛下一双儿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覃纯菊背着一百多斤的沙子,一趟趟往返于山上山下,硬是自己背出了一栋屋。
股潮
摄影/文/张新民 1992年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的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百分之十,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股。
在这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暗中开始身份证搜集大战。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大塞车,占线的都是内陆长途,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多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已经开始有人占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寻梦者急奔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就买不到了,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大小巴士,票价比平时涨了好几倍,也丝毫未能阻止蜂拥而至的人潮。
公告预告的8月10日上午开始发售抽签表。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虽然蚊虫肆虐,但熬夜排队的人们却斗志昂扬。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潮,人们手里揣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经过整日暴晒,人潮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傍晚雷雨临头,湿气蒸腾,阵地依然固若金汤。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潮超过了100万。
深圳警方倾巢出动,在人山人海中维持秩序。因警力不足,边防部队,武警部队出动增援,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少数执法人员和工商,证券从业人员利欲熏心,在一些发售点公然徇私舞弊,刚开始发售不到半个小时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难日夜排队的民众美梦成空,导致了8月10日傍晚在深南大道,一些人上街游行请愿要求见市长,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多用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销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1992年深圳特区新股认购,抢购股民证的长队秩序极度混乱,众男女只好前胸贴后背,一个紧抱一个,在利益面前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尊严。
专程从江西赣来的小伙子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挤出列,他手上揣着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喊道:“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
列车边兜售食物的温州人
摄影/萧云集温州 2000年
一群温州人在细雨里箪食壶浆,戴着凉帽打着雨伞,正举着精心制作的长竹竿挑着橘子、面包、花生之类的小袋食品卖给列车上来往的旅客,这样的交易场面不仅需要手疾眼快,也需要类似钓鱼一类的稳度、耐心与投食技巧。
可以说,在国内商界一枝独秀的温州人的经商头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
在金温铁路沿线上小贩利用停车的机会用竹竿挑起食品和乘客交易,这种买卖方式对交易双方的诚信都是一种考验。在利益的驱使下小贩们只能承担这种风险。温州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靠着这种渴望温州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山区集市买镜的女子
摄影/ 徐晋燕 云南会泽 2000年
画面里的集市,也就是“街子”,可能位于极贫困深远山区的缘故,来赶集的人并不太多,两个裹着花格头巾的女孩正在逛集,其中一个买小镜子的女孩正欣喜地从镜里打量着自己,镜子里她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容颜,她既开心又满足,心情也一如远处山梁尽头那一片蓝天白云,那一刻就连她右边不远处那个照看摊位的小孩,也忘了招徕顾客,自顾羡慕地看着她。
云南人把集市叫做“街子”,大到如“三月街”上万人来赶,慢慢演变成民族节,小到连间房子都没有的几十人的草皮街。但无论大小,老百姓总能从街子上得到自己的满足和需要。会泽大海梁子虽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但买镜子女孩的爱美之心,竟是连这样的穷山也不能埋没的。
云南会泽大海梁子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在它的集市上一个女孩对着镜子满脸微笑,贫穷并不能掩盖她对美的渴望。
制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
摄影/谢海涛河南平舆县2001年
2001年2月9日,在河南平舆县什字路乡王关庙村一民宅内,犯罪分子正在进行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从一个小瓶里倒出点透明的液体,均匀地抹在假币上,然后用电熨斗把假币熨得平平的,咔咔作响。 这些假币大多是从台湾偷运到东南沿海(主要是广东),再偷运到河南的。有些假钞的制作甚至到了连验钞机也无法分辨真伪的地步。
照片上便是民宅内乌烟瘴气的假币制作现场,左边的造假者左右开弓,正在用电熨斗把桌子上的四张假币熨平,因为他“工作”太繁忙,以至于连点颗烟的时间都没有,旁边一个人于是为他匆忙点上。右边的造假者表情平静,嘴里叼着涂抹透明液体的小棍子,右手忙着往一张假币上涂抹透明液体,整体来看,两个造假者配合默契,对假币制作相当娴熟,“假币”,此时如同一根魔棒,把他们对钱的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间窄小的房子里几个人正从容地制作假币,金钱的欲望使他们忘乎所以铤而走险。
乡村苗人渴望的天籁
摄影/ 徐晋燕 云南昆明 1994年
画面里尽管我们看不到唱诗班全体,但却能看到七八部大小双喇叭录音机被一群苗人虔诚地举抱着,正把唱诗班优美的歌声录下来,左下角几个裹着头巾的孩子显然也受了这种虔诚歌声的感染,神情肃穆而恬然。
云南昆明富民有一个叫小水井的苗族乡,离省城并不远,驱车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却风俗迥异,村民们信奉基督教已有不短的历史。尽管时代变迁,很多事已发生变化,但信教的人始终存在着。村中有一个基督教堂,是周围几个村中最大的。教堂里的唱诗班唱出的赞美诗,共分几个声部,悠扬动听,听者无不为之感动。每到礼拜,周边的苗人便会带着自己简陋的录音机蜂拥而来,把唱诗班唱的赞美诗录下来,回去欣赏和学习。遇上圣诞节,这个唱诗班更常被昆明城里最大的教堂请去唱赞美诗。
在教堂的一角,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仔细地录下唱诗班优美的歌声。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睛里可以看出虔诚和渴望。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