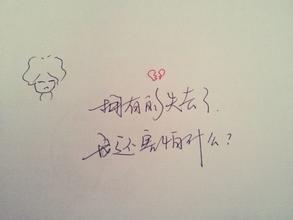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人生中第一支曲子的,或许是呱呱坠地后在母亲的怀中,但据我观察,内敛含蓄的母亲却不像是会哼催眠的小曲儿给我听的;倒是平日里爱说会笑的祖母时不时用带着浓厚乡音的调儿给我吟唱着:“杨柳叶子青啊奈,七打七拿蹦啊奈。”也是听祖母后来才说起,每次她唱起这两句词儿的时候我总是会嗤嗤地笑出声来,我笑了,全家人便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大抵便是我接触音乐的由来吧。而后渐渐长出人样,却又不愿再听祖母日复一日地哼着那两句在我看来近乎有些无聊的词儿了。祖母为了迎合我的心意果真不再吟唱,只是有些时候走路便又情不自禁地小声喏喏起来。在孩童年代,听得最多的应该是父亲的歌声了,而父亲哼唱的歌总是要比祖母的洋气的许多的,听得也更全一些。我依稀还保存着那时候的一些零碎的记忆:放学的路上,父亲骑着他的“野马”摩托车载着我飞驰着回家,只有坑坑洼洼的泥路才会放缓我们的速度,父亲似乎是有些得意的,因为那时在乡村里,这样的摩托也并不多见,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炫耀的资本。每当开到平坦的路段的时候父亲的心情似乎也格外的好起来,便顺着哼起那首杨钰莹的《让我轻轻地告诉你》。然而我却没有流连在父亲的歌声里,两只脚踩着车后面的撑子,两只手搭在父亲的肩上,瘦小的身躯伏在父亲的暖暖的、宽大的背上,全神贯注于道路两旁的花花草草、奇闻异趣之中,仿佛有看不完的景色。那时的我大概是还没有真正喜欢上音乐吧。
待到渐渐成熟起来,也正是周杰伦在卡带里唱着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双截棍》的时候,也是阿杜用他那沙哑的近乎要撕裂的嗓音唱红《他一定很爱你》的时候。那时的刘欢或许是有脖子的也未可知,但陈奕迅肯定是还没有被人称作“歌神”的。我所听到的是《江南》的烟雨缠绵、如痴如画…是《七里香》的燕雀流连、蝴蝶纷飞…是《黄昏》的烈日灼身、热泪烧伤的错觉…在那时的记忆中,这些歌的歌词仿佛比任何的一篇唐诗宋词、近代散文还要优美生动的多,更别提唱出来之后的感觉了。从此,我便走上了热爱音乐的这条道路上来,每日总是要听上几首,哼上几句。然而我终究没有能成为一个音乐人,以至于到最终也只能是单纯的爱罢了。
可能由于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的缘故,如今却又像当初一样有些不屑于听这些在我看来有些乱人心智的“靡靡之音”了。但他们实在是“毒害”的我太深,以至于偶尔在商场店铺的音响中、在亲朋好友的车中听到这些歌声的时候,又感到十二分的饶有兴致。至于在我独处的时候,我是断然不会再去感受这些歌声的,转而沉溺于清静、质朴的民谣,狂放、热烈的摇滚这样的风格了。这两种的风格共存与音乐人身上是鲜见极少的,比如你见过汪峰哼民谣吗?又比如你见过朴树吼摇滚吗?但共存于像我这样的乐迷身上确是完完全全可以实现的,而这大抵也是我庆幸没有成为一个音乐人的最后的一个说辞了。
不管是音乐人还是乐迷,最终都是音乐的拥趸。不管是古典还是流行,抑或是摇滚、爵士与民谣,所追求的只是沉浸在令人如痴如醉的声音之中。如失落哀愁的时候,听一曲杰伦的《稻香》是极好的;愉悦快乐的时候,听一曲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是极好的;踌躇满志的时候,听一曲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是极好的;安静悠然的时候,听一曲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极好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