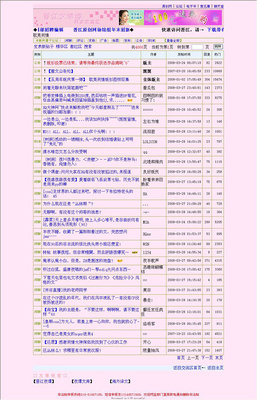北方的伏天应该和南方的梅雨季节差不多,也热,也多雨,也潮湿。记得每年的初伏都不是太热的,三伏才是最热的。今年却是不然,还没有入伏,就已经热得轰轰烈烈的。一经入伏,降水就频繁起来,有时大雨滂沱,有时细雨缠绵。即使不下雨,也没见几回太阳公公,再加上我居住的小城临近海边,空气是特别的潮了,随手抓上一把,似乎都能从中挤出水来。一颗心仿佛也被雨季所浸染,所侵蚀,湿漉漉、潮乎乎、沉甸甸的。
多半个六月整个七月,因为“腰脱”复发,遵医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大夫说要睡板床,老公给我这边撤去了床垫子,只铺了一个薄薄的褥子,每天硌得骨头肉都疼。看到老公那边铺的又厚又软的,强烈向夫提出抗议。老公笑我刁蛮。见我横眉,将他那边的暄软也撤了去,说这回陪着我一同受罪。我畅言道,这才是夫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老公笑着刮我的鼻子。
老公每日忙于上班,下班忙着进厨房,做饭烧菜。说是怕我终日躺着上火,每日回来必是大袋子小袋子的蔬菜水果往家里拎,下厨也是变着花样的做着吃。老公烧得一手好菜,只是我没病的时候,他忙,很少下厨,想饱尝他的精彩厨艺,一般须得节假日才可以。我欣然由于生病,自己才有机会每日享受夫的照顾和美味。然,看到老公每日如此的辛苦,也感心疼,表现出少有的柔情来。老公见状受宠若惊,更加尽心卖力,于我关爱倍至。我在病痛的烦扰浮躁中也渐渐的静下心来。
女儿前几天从北京回来度假,一进家门,见我卧床,就珠泪涟涟的,扬言辞了实习的工作,回来照顾我。小小年纪知道了疼人,心里就那么蓦然的暖起来。每天她爸爸上班一走,十七岁的她像个婆婆一样的管着我,不许这不许那,就是起身倒杯水,也会被她训斥。想起那些年她体弱多病,每日照顾她,怕她冷着怕她热着,精心的呵护,细心的陪着她长大,现在觉得和她替换着颠倒了位置。或许这就是常说的在收获付出吧?
难得这么有时间的读一些闲书,找来一些八九十年代的书籍,堆的满床皆是,一本一本的翻看,很多的时候只为翻翻,并不仔细去看,走马观花一样的,或许只是为了触及那些泛黄的记忆吧,像触摸着一段段久违的光阴故事似的,兴致盎然。想自己那时候,住在乡下,但凡有去城里的机会,都要去新华书店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籍,那时候书也便宜,一套《红楼梦》才九块八毛钱。日积月累,长篇的短篇的,近代的远古的,已然有三百本之多。于那些不爱书的人,或许是一种负累,而于我却是不可取代的财富。这些年颠簸流离的搬了几次家,这些书籍一直跟着我,不曾舍弃一本。它给我的快乐是一般人所不能够懂得的。
翻看中,在每一篇文字里,随时都可以看到自己在阅读时留下的一些痕迹,或者画下的标记,或者几句阅读的心得和感悟,今日再度的重温,觉得那时候自己的有些见解真的显得浅薄而拙淡,但也是有诸多的感慨和叹息。(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在一本《晨读美文》里,看到了京味小说八大家之一的苏叔阳老先生的《树叶》,或许是因为和他“同命相连”吧,又仔细的读了一遍。
由于生病住进医院,“我”从春到夏守着一个窗口,守着窗口里的一根树枝,亲历着一枚枚树叶的“一两点鹅黄翠绿蹲在枝头”,到“齐刷刷一排小巴掌似的”,再到”变得浓绿,变得稠密“的生长变化的全过程,细腻而富有哲理。最欣赏那一对喜鹊筑巢时的情景描写:“……一个接一个飞上飞下,衔来树枝在枝桠之间。那可怜巴巴的小巢在风中摇晃,可是不敢掉下来……”这个“不敢”用的该是何等的巧妙与达意,托物言志――在顽强与坚持面前,再强大的阻力都是渺小的,都是可以战胜的。
想到自己每天躺在床上,可是没有树枝探进我的窗口,更不消说树叶,和在树上筑巢的鸟儿了。我向窗外望去,眼所能及的是一角灰蒙蒙的天空,今天又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这个季节也很少看到蓝色的天空了。
没病的时候整天忙着工作,挣钱养家,那时候盼着能有一个让自己好好歇歇的理由,哪怕几天就好。每天清闲,自由,幽静,随心所欲,那该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福啊。现在病神慈悲我,赐予我奢望已久的悠闲与寂静,让这世间的一切与我抛闪隔绝,只赐我一间斗室,一角没有阳光的天空,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躺倒生息,却是觉得身心俱疲,便格外的想念那些忙碌的日子。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经过允许,小站在卧室的玻璃窗前,做暂短的目光流连。窗外朦胧的夜色中雨下的正酣,一股潮潮的空气穿过纱窗撩到面颊上,感到了潮润,此时于我是久违的惬意。街面上依然有行人在雨中穿行,或打着雨伞,或穿着雨衣,或单人,或双人。单人多是行色匆匆。双人的多是漫步逍遥。看情形多半是情人,搭肩搂腰,显得格外的亲密悠闲。
最热闹的是对面那条街。那是一条集各种饮食的商业街,有各色饭店,小吃,还有烧烤大排档。无雨的好天气,夜晚是最热闹的时候,尤其烧烤大排档那儿是最具人气的,门前的座位上往往是座无虚席,还会有站着等候的人们。酒喝到酣至,猜拳行令的声音一波一波的唱响着,热闹非凡。炼炭多选在一个角落里,在楼上观瞧,一团团的火星子,四下飞溅开,像在地下绽放的烟花,一簇簇的一直开到深夜一两点钟。眼下那些角落里依然有火星子在飞溅,只是没有了晴天的招摇,因为还没等它铺炸开,就被雨水淋灭了。
楼下两侧橘黄色的路灯下,仍然有打着雨伞招揽生意的年轻女子,远远的看去,依然可以看到妩媚窈窕的身姿。
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太阳落山以后,一名卖花的女子会准时出现在街口。
一辆自行车,后面驮着两只柳条编成的篓子,里面盛着鲜滴滴的各种鲜花,有玫瑰,有美人蕉,有月季,有百合,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子的山地野花。尤其那些野花,倍受欢迎,都是最先卖完。那些花都不曾经过修剪,随意的用一些红的绿的布条条捆扎着。女子来到那棵槐树下,把两只篓子从自行车上卸下来,并排放在一处,从前面的车筐里拿出一个折叠的小凳子,掰开,坐在两篓子鲜花的后面。女子从来不叫卖,等着买主自己上门来。她似乎没有时间限制,啥时卖完了,啥时走,大都要卖到晚间十点以后。大体说女子的鲜花生意还是蛮不错的,那些食客里不乏有情致之辈,无论多晚,她都能把花卖完。
晚饭后,一般都要在电脑前,看一些东西,或者敲打一些文字,每天临睡前,必站在窗前,做一个暂短的伫立,望一眼,她还是在。久而久之卖花的女子变成了我眼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
看惯了这道风景,今夜雨中不见,心间不免就有了一阵的怅茫失落。老公走过来,见我些的茫然若失,告诉我,那个女子已经几天没来卖花了,听说她老公去世了。我愕然的张大嘴巴,想那女子也不过三十几岁的模样,人长得也精致面容清清秀秀的,身段也窈窕,看着善眉慈目,定是一个蕙质兰心的女子,怎么会遭此厄运呢?老公说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她男人是个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瘫了三年,前几天去世了。
心便是万分的难过。为那女子,也为女子的老公。好人命运多舛,女子红颜多薄命,想那女子这两条都是占了 。
禁不住寂寞,躺了十几天以后开始上网。怀里抱着键盘,鼠标放在手能及的一个凳子上。键盘和鼠标都是有线的,拽来拽去的,首先键盘的线虚脱了,不再好用。拽虚了,就在床与主机的后面钻来爬去的。老公见状,怕我碰了病处,说去给我买个无线的,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女儿回来,老公第一时间告诉她女儿帮他完成这个任务,女儿立马办了,出去为我买了一组无线的,OK!好用极了!我高兴的像个小孩子一样,爱不释手的抚摸夸奖。女儿直笑得鼓掌宣泄我的可爱。
上网最多的是流连在网站里,看朋友们的美文。那日看到一个文友诗人的一首诗,《女人花》,其间的一节“紫色的女人”
我是风
在梦里梳理你的长发
百合花的馨香追随我
飘摇三千丈
//
我是雨
在梦里亲吻你的脸颊
谁是最幸运的一滴
渗进你的嘴角
在你的口中融化
//

我是一片雪花
期盼你想我到天涯
伸出你纤纤小手
让我在你的情感纹中
流淌
//
请你用舌尖轻轻的
把我品尝……
就喜欢的不得了,觉得自己就是诗人笔下的那个婉约的紫色女子,擎着一柄紫色的小伞,伫立在烟雨蒙蒙的江南雨巷的青石板路上,翘首凝眸之间,恰好巧遇诗人,就被诗人收进他的是花,若雾,像云像雨又像风的梦里。
女儿休假结束,要回北京了。我和她商量要去车站送她。起初她反对。老公懂我心思,为我极力讲情,女儿见我已是好于她回来时,便同意了。二十八日,我和老公一同去动车车站送她,动车站离我家三十里路。一路上老公和女儿一边一个护着我,一再提醒司机稳重行驶。为了我的安全,一再夸大其辞的张扬我的病情。
足不出户五十余天,一经走进这大千世界里,满心里都是欢喜。虽然天气很炎热,很潮湿,车里开着空调,却是清凉袭人,丝毫没有炎热之感。途径一个村庄,正是做晚饭的时候,袅袅炊烟缭绕,无边的翠绿,包裹着红砖绿瓦的村庄,路旁的花影树声还没来得及看仔细,就纷纷向车后跑去。
在车站等候了半个小时,车进站了,女儿一步三回头的走进站里,一句句的叮嘱我好好养病,嘱咐她老爸把我照顾好。听到一声汽笛长鸣,知道女儿踏上了旅程,心跟着走出去好远。老公一声长叹:孩子大了!意味深长。
往回走的时候又是细雨蒙蒙,老公与我坐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握着我的一只手,女儿走了,心里空空的,此时老公掌心里的温度让我有一种相依的温暖。
我让司机关掉空调,打开车窗。一阵阵潮湿的风裹着细细的雨丝扑过来,敷在脸颊,和裸露的胳膊上,凉爽的舒服,心爽神怡。
已是万家灯火,白天看过的景致,陷在一片烟雨朦胧里。还是那个村庄,白天路过的时候,不曾听见蛙鸣,或许是白天的缘故,或许是没有落雨的缘故,此时蛙鸣已经响成一片,清脆响亮。就想起南宋诗人宋师秀的《有约》来: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前两句,与这眼前的景致是何等的相似啊,乡村的雨夜,细雨缠绵,青草簇簇,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鸣 。那么后两句呢?是不是在这村庄的一隅,也有一间寂寞的小屋子,屋里也有一个孤独的诗人,坐在摇曳的灯光下,一边把玩棋子,一边拨落灯花,等候夜伴尚未赴约的客人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