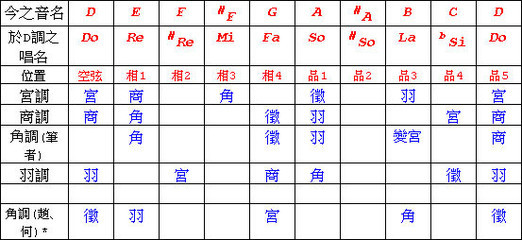摘 要:和谐美是王维《辋川集》诗最本质的美学特征,也是其反复吟咏的主题。从美学范畴上看,《辋川集》诗的和谐美呈现为优美;从诗歌意境上看,《辋川集》诗的和谐美表现为物我浑融的“无我之境”;从哲学背景上看,在禅即色观空的刹那静观中所实现的色空一体之境,是《辋川集》诗和谐美的本质内涵。
关键字:王维;《辋川集》;和谐美;优美;无我之境;
刹那静观
王维的五言绝句,空灵淡雅,意趣高远,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明人高*选编《唐诗品汇》,以“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诸名来分编定目,权衡品次。在“五言绝句”这一目中,将王维之五绝列为正宗,并评曰:“开元后,独李白、王维尤胜诸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中也称:“摩诘五言绝穷幽极玄,……俱神品也。”从这些赞美之词可见王维五绝之功力,其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王维的五绝,就其题材来看,大部分为山水田园诗,其中又以《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这二十首五绝,依次绘写蓝田辋川别业周遭的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等二十处游止胜景,其语言清丽秀雅,造境透剔圆成,显示出诗人山水诗创作上的高度成就,历来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山西大学的傅如一教授在其选本《王维集》的评解中指出:“和谐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最本质的美学特征,也是《辋川集》诗反复吟咏的主题
一、优美――和谐美的美学呈现范畴
1、两种美――优美与壮美(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优美、崇高、悲剧、喜剧在现在我国美学界一般被认为是美的基本范畴,其中,优美与崇高是最常见的两种相对的美。优美,也称秀美,是美的最一般的形态,最早被人们认识和把握,是一种优雅的美,柔性的美;崇高,也称壮美,是一种雄壮的美,刚性的美。
优美与壮美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的感性显现。但二者的审美特征有所不同:优美是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的和谐统一在对象世界的感性显现,壮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与客体的严峻冲突在对象世界的感性显现。优美是一种单纯、常态的美,它的基本特性就是和谐,其实质是因为在对象世界中人的本质力量和客体并没有表现为激烈的抗争,而是表现为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对立而达到矛盾解决,进入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壮美的基本特征则是严峻冲突,其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里并没有和谐统一,而是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尽管主体与客体抗争的最终结果是主体征服客体,但壮美所要表现的并不是这一结果,而恰恰是主客体双方矛盾斗争的过程。因此,优美包括精巧、清秀、飘逸、淡雅、幽静……一类的美,而壮美包括宏伟、雄浑、壮阔、豪放、劲健……一类的美。
2、两类诗――豪放开阔者与幽静空灵者
王维的山水诗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高山大河而气势宏大、境界开阔者,如《终南山》诗,用白云、青蔼的变化,阳光、阴晴的不同,表现终南山千岩万壑的万千气象;而《汉江临泛》则是用山色有无的视觉和郡邑远空的撼动感觉突出汉江的气势,两诗都有咫尺万里之妙。另一类则是通过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高落寞的情怀,代表作即《辋川集》二十首五绝。
如果将王维这两类山水诗与前文所述的两种美相对应,那么,前者如《终南山》、《汉江临泛》等一类的诗当属壮美范畴,而后一类的代表作《辋川集》无疑应归入优美范畴。前文所述,和谐是优美的基本特征,《辋川集》诗是优美型的诗,那么,优美也就是《辋川集》诗和谐美的美学呈现范畴。
3、优美的具体表现
《辋川集》的描写内容,从美的形态特征上看,其优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量的方面看,优美的事物一般力量较小。《辋川集》诗是以王维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墅的二十个景点为题即景所赋,诗人所描绘的正是一些小景点,而非大景观。辋川别业作为私家山水园林,其主体在山水,就《辋川集》所吟咏的来看,有华子冈、斤竹岭、茱萸泮、南*、北*、欹湖、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其中,华子冈、斤竹岭是较高的石山,南*、北*是较平缓的大土丘,泮是半月形的水池,濑是流水自上而下碰撞所形成的石滩。可见,《辋川集》诗中没有《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的汉水之浩荡无边,撼天动地;也没有《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所描写的终南山之雄奇壮阔、直入云霄、绵延千里,辋川其山不在高,其水不在深。辋川园林的物质性建构除山水(泉石)外,还有花木和建筑。其花木系统,《辋川集》诗篇所提到的有木兰、茱萸、宫槐、芙蓉、柳浪、辛夷、漆树、椒树,这些花木虽类别多样,但均无参天大树之姿。至于《辋川集》诗中所反映的建筑系统,仅有孟城坳、文杏馆、临湖亭、竹里馆四处,据金学智推论,“辋川不可能有大规模、豪华精致的建筑群” [],至于“不知栋里云,去做人间雨”(《文杏馆》)、“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的胜景,那完全是由于诗人善于在山颠水际之处标胜引景的缘故。山水清秀、花木依依、亭馆相望,王维为自己营造的是一派优雅的辋川别业。
其次,从形式方面看,《辋川集》所描绘的景物线条曲折、颜色鲜明而不强烈。王维既“妙于诗”,又“精于画”,其山水诗善于“应物象形”、“随类赋彩”。《辋川集》诗中描写斤竹岭“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意谓来到斤竹岭,便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竹林竹海,无论是山顶还是山谷,都呈现一片风姿绰约的景象,那高低起伏的无边翠绿,宛若大海的波纹;还有《宫槐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使人读后不觉产生联想:密密的宫槐树下有一条窄窄的路,由于难见阳光,显得幽深阴暗,上面长满了青苔,还覆盖着槐叶,真可谓“曲径通幽”;再有柳浪“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漪”的绰约风姿,这些都是曲线美的表现。关于景物的色彩,诗人在《辋川集》中所赋的大多是冷色,如鹿柴的“青苔”、欹湖的“青山”“白云”、栾家濑的“白鹭”、白石滩的“绿蒲”、北*的“青林”、竹里馆的“明月”等,色彩及其淡雅,给人一种恬静、清爽、温柔、和谐的感觉。即便是色彩鲜艳者,如《木兰柴》中的“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也没有《终南别业》中所渲染的“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之浓艳。
再次,从状态方面看,《辋川集》诗的优美表现为一种静态美。追求、赞颂“空寂”是王维诗文创作中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辋川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在诗人笔下,整个辋川山水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不是安乐、祥和、宁静的,自然山水不在是那种充满力度的动荡与激烈,青山、白云、夕阳、月光、秋雨、幽篁,自开自落的芙蓉花,逶迤轻柔的溪水,恬静地展示在读者眼前;而那不伤离别的诗人、乘月而归的浣纱女子、临湖对花酌酒的高士,无不传达出平和安宁的情调。
二、无我之境――和谐美的诗学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并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关于这两种境界的划分,历来众说纷纭。北大教授柯汉林先生在《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新论》一文中认为“王国维两种境界说中确实存在着从观念出发,以至有时脱离了实际(作品)的毛病,他对两种境界优美与壮美的区别,这种毛病更为突出”,这一论断是客观的。的确,王国维两种境界关于优美与壮美的区别,并非适合于所有中国古典诗词。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却适用于王维的《辋川集》诗。《辋川集》中大多诗篇都属“无我之境”,同时又是优美型的诗,最能体现主客和谐一致。
1、《辋川集》诗是“无我之境”的典范之作
很多学者都惯于把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的来源归结为叔本华的抒情诗理论,而柯汉林教授则认为王氏两种境界说的根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我”与“无我”这两种精神境界。儒家“崇有”,强调“有我”境界;道家包括玄学家及后来的禅宗则“贵无”,强调“无我”境界。两种境界的共通之处均建立于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宇宙――人生观”的基础上,但儒还是强调我是一个“有”的存在,“我”作为万物一分子与万物、他人共在并息息相通,所以应视人犹己,视天下为一家,可见,儒家的“有我”是超越了自私的我,即变小我为大我。道家强调的是以“无”为本,主张“以无为心”,“无心”便是“无我”,但其实“无心”也是一种“心”,即“道心”,它认为以道心待我,不仅超越了小我,而且超越了大我,所以能与万物真正消除区别,达到彻底的物我同一而进入自由境界,这就是“无我”境界。禅宗讲人生三境界,也崇尚“无我”,它认为人生第一种境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境界,即小我境界;第二种境界是将小我融于宇宙之中与万物合一,个人是宇宙一部分,又是宇宙之全体,所以能视人如己,爱人如同爱我,即大我境界;最高境界即第三种境界是“无我”,既超越小我,又超越大我,是物我对立全部消失、真正解脱的自由境界,最后这种境界与道家的无我境界同一。[]
王维“身属儒家而心兼禅道” [],禅宗是王维的精神避难所,他试图以次来实现心灵的超脱与救赎。在禅悟的精神体验中,王维与天地自然从而也同道家相遇了,他同庄周一样获得了与天地自然消融在一起的心灵陶醉。心境借诗境得以传达,诗境因为心境而和谐至极,《辋川集》诗正是作者达到这种“无我”精神境界的产物,从而也成为“无我之境”的典范之作。
2、《辋川集》诗无我之境的具体表现
《辋川集》中“无我之境”者有两类。一类是以“无我”化“有我”者,这类诗的前两句是较为明显的“有我之境”,但在末尾又将强烈的主观情识完全抹去。如《鹿柴》一诗就前两句来看,分明有一个“我”存在,“我”在空山之中,“我”体会着那只闻人声而不见人影的空山幽静,明显透露着强烈的主观情识。然而在诗的末尾,诗人在对景物的描写中,把“我”的存在、“我”的情识完全淡化了,或者说将“我”融化在了大自然中。“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在这里,夕阳既是一种审美对象,同时更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是短暂的、变化的、无主宰的,处于其中的人亦应如这夕阳一样,同是短暂的、变化的、无主宰的。在这里,人与自然完全同一,因而,也就没有一个“自我”所在。这种与万物同化的“无我”之境界,在《竹里馆》中亦复如此。“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从诗的外在形式来看,诗的题旨乃在描写一位幽居山林、不同流俗的高人形象,传达出一股幽深之气。诗的前两句,依然是强烈的“有我”,独坐、弹琴、长啸,让人感受到诗人那种清高、傲世、不满现实的态度与情绪。但在诗的末尾,诗人却又将这强烈的主观情识完全抹去。作为社会的人,却不为社会、同类所理解,只好逃循于深林之中,与那一缕月光相亲近。人的情志,只有在同大自然混一之中,才能获得显现,人的存在,只有在同大自然的往还中才显现出他存在的意义。因其“无我”,人的情感,依循自然的律动而存在,似乎不再有大的波动。《欹湖》中,我们领略到的是诗人不为离别而伤的平静。“吹啸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前两句以舒缓、平和的陈述语句叙出送别,在诗人心中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不舍;然而末二句没有感慨,没有议论,更没有感伤,湖光、青山、白云,让人分辨不出是诗人的幻景,还是大自然的实境,也就更难让人体会到那份自我的情识。
《辋川集》中还有一类诗,能够完全超越感情,顺随自然,从而使人化的自然,复归为物化的自然。“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漪。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柳浪》)折柳送别,借“柳”与“留”同音,来抒发人们对离别的伤感之情。无论是《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是柳永《雨霖铃》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均给人一种惆怅、伤感之意。而王维的这首《柳浪》却一反传统的用法,不再在“伤别离”的意义上去使用它,而是还其自然之面目,使其不再带有伤感之意。它本是繁茂而清雅、平和而幽静,诗人着意抹去了它人化的意味,恢复其自然之本性。这类诗中最典型者,莫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表面上看,诗人以极其平淡的笔调,写出了寂静山涧中辛荑花自开自落的景况。但对此诗再作深层的探究,读者自可领悟到,这生长在静阒无人山涧中的辛荑花,它的存在完全依循着自然的律动,该其开花时则开,该其殒落时则落,不因人喜而开,亦不为人悲而落,完全是一自在自为之物,除了自然本身,没有谁来主宰它。以花视人,毫无疑义,人应同这花一样,依循自然的律动,自在自为,亦没有谁来主宰它。在这里,人与自然已经完全同化,人的主观体验已经同自然的律动完全合拍,社会的人、人的情感已经融入自然之中,那也就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主宰,也就是一种完全的“无我”。物我浑融,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至极才能创造出的境界。
三、刹那静观――和谐美的禅学背景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视为“无我之境”,陶渊明的《饮酒》、《归园田居》等田园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达到了景与意会、物我合一的境界,他的这类田园诗同王维的《辋川集》诗都是“无我之境”的典范之作。然而正如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所说的那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禅而非道;尽管它似乎很接近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是道而非禅,尽管似乎也有禅意。”[]这说明二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哲学背景是有所差异的,陶渊明偏于庄,王维偏于禅。尽管庄、禅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但又仍然有差别。李泽厚论述了这种差别,他说:“庄所树立、夸扬的是某种理想人格,即能作‘逍遥游’的‘至人’、‘真人’、‘神人’,禅所强调的却是某种具有神秘经验性质的心灵体验。……庄子那里虽也有这种‘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但禅由于有瞬刻永恒感作为‘悟解’的基础,便使这种人生态度、心灵境界、这种与宇宙合一的精神体验,比庄子更深刻、也更突出。”[]禅与庄的不同,使王维的《辋川集》诗具有不同与陶渊明田园诗的更深刻的内涵。
1、陶渊明:亲和自然,回归“浑沌”
“先秦儒道的时空意识中,自然为无穷又永恒的绵延,它作为客体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而被动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中,自然是不断流变的,而人主体的认识能力却跟不上客体的变化,因而要求人(主)向自然(客)回归,人类的根在自然。庄子提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庄子・知北游》),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还原自然的“大美”,也就是靠向那个未分化的朴素的“浑沌”,那是一种直观自己为自然之物的状态。
从陶渊明田园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思是脱离俗世,靠向庄子的“浑沌”。陶渊明的诗中,自然之物就是自己的生存家园,一切亲切无比。他与自然为邻,亲自从事农耕劳作,把生命融于自然的节候节秦,“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人与自然已浑然一体。陶氏以亲身实践及田园诗的形式,复兴了庄子的“齐物”经验,试图通过亲和自然,来实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理想,这就是陶渊明田园诗中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深层内涵。
2、王维:现象空观,色空一体之境
张节末认为:“陶潜的伟大一步是将田园拟为脱离俗世的人间乌托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而王维则进一步植‘五柳’于‘空山’,品格上迥异与陶潜所主彻底回归自然的‘托体同山阿’(《挽歌诗》),显然‘寂寞’已经被安置为陶潜回归自然的更深沉的背景。”[]王维是在“五柳先生”与自然亲和的人格上,加上了“空”。
“空”是佛教的哲学,他导致了佛教观法与中国传统观法的不同。杰出的中道哲学家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说:“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万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这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讲万物变化,意在指出,过去之物,已经过去;今日之物,不是过去之物,而是当今的新事物。“从事物时刻在变来说,我们只见有变,不见有恒;然而就那一刹那来说,在那一刹那,事物和时间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有恒常无变化。”[]这种时间意识能够从宏观上把运动看破,认为“有”,仅只是一种“假有”,因其假而不真,故谓之“空”,这就必然要求以完全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乾坤倒覆,不能说它不静,洪流滔天,不能说它是动。
空的时间意识为以静观动的刹那直观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于是,王维出场了。王维改变了传统的齐物观法,他主张在色上得定:“色即是定非空有”(《绣如意轮像赞并序》),也就是要求,看空不执着于空,将之落实在万有之上,才能达到即色观空的妙有。换言之,其所观之对象仍然是传统的自然,不过,仅仅把它视为纯粹现象而已。在禅的刹那直观的感知活动中,对象脱离了变动不居的时空背景,失去了客观的真实性,仅仅是作为纯粹的现象而被“见”,这就是色空一体之境。这种看空的感知活动,张节末先生把它称之为“现象空观”。[]王维的“色即是定非空有”之说有意无意地照顾了向自然回归的中国传统,只是要求在基本世界观上肯认其本质为寂静。
寂静,是王维《辋川集》山水绝句意境观法的本质。“秋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木兰柴》)阳光、飞鸟、彩翠、夕岚、各种美景都在活动、变化,非常平凡、非常真实、非常自然,但它所传达出来的意味,却是永恒的静,而且也无所谓动静、虚实、色空,本体是超越它们的。在本体中,它们都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割了。这便是在“动”中得到的“静”,在实景中得到的虚境,在纷繁现象中获得的本体,在瞬间静观的直观体验中获得的永恒。《辛荑坞》写辛荑花“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也是如此,辛荑花“开且落”的动态仅仅是被静观,它并不比类着客观时间之流驶和主体生命之飘零。在禅的刹那直观中,主客同体,客观(能观)与自然(所观)完全同一,诗人已经飞跃地进入了佛我同一、物己双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那异常奇妙、美丽、愉快、神秘的精神境界。
王维的《辋川集》山水诗直观经验下的主客同体之境,并非物化即齐物的结果,他并不如庄子、陶潜般回归自然,呈现者只是一个全然寂静的自然之境。但它们仅是看似纯然客观之物,其实都是看空之人所观的“色相”。在即色观空的瞬间静观中,自然和自我完全融合,诗人感受到的是那永恒不朽的本体存在。这就是《辋川集》诗和谐美的深内涵。
综上所述,无论从美学范畴上,还是从诗歌意境上看,和谐美始终是《辋川集》诗吟咏的主题,而寂静又是其和谐美的本质内涵。如同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王维之空寂同样属于古典诗美的一种范式。又如同李白的吞吐日月、杜甫的大庇寒士,王维的物我两忘同样是宇宙情怀的一种表现。正如李泽厚在 《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王维的山水诗:“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注 释:
①王维著、傅如一解评:《王维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②金学智:《论王维辋川别业的园林特色》,参见师长泰主编《王维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③圣严法师:《禅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0―112页.
④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⑤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64页.
⑥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4页.
⑦张节末:《纯粹看与纯粹听:论王维山水小诗的意境美学及禅学诗学史背景》,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⑧同⑦
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⑩张节末:《中国诗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古诗歌运动中比兴的历史命运为例》,载《文史哲》200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王维著;傅如一解评.王维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
[2]师长泰主编.王维研究(第二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8.
[3]欧阳周、顾建华、宋凡胜编著.美学新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1.
[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
[5]王国维著;藤咸惠译评.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1.
[6]圣严法师.禅的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1.
[7]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1.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

[9]张节末.纯粹看与纯粹听:论王维山水小诗的意境美学及禅学诗学史背景[J].文艺理论研究,2005(5).
[10]张节末.中国诗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中古诗歌运动中比兴的历史命运为例[J].文史哲,2006(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