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1906―1947年7月1日),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杀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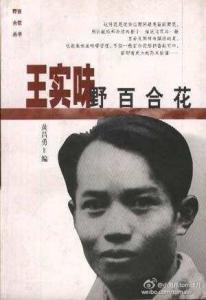
王实味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因文惹祸,写下《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起冤假错案。
王实味_王实味 -生平
王实味文存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 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王实味_王实味 -作家解读
王实味全传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王实味_王实味 -作家之死
《野百合花》给王实味带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温和的,语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恨铁不成刚的意思。披露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延安的歌舞升平夜夜笙歌的不适宜,以及在延安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说的都是实话,在以后对王的批判中,并没有谁推翻王所说的现象,只是追究他的动机和造成的影响。首先被触怒的是拥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人,也就是掌握了枪杆子的人,象王震、贺龙、甚至朱德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王实味是专家。1937年奔赴延安后,在四年的时间里,王翻译了二百多万字的马列著作。在研究理论和观察现实中,王提出了疑问:为了一个崇高理想的实现,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是否必须牺牲个人精神自由为代价。并指出“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这实在是知识分子的呆气,既然知道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却与斯大林的信徒们讨论人性。1947年,由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签署,在山西被秘密处死。用刀砍,然后推入一枯井中。三十多年,文革结束后,王实味的妻子和已长大的儿子才知道王早已不在人世。
王实味_王实味 -意义
冤案平反“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王实味_王实味 -《野百合花》原文
前 记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
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
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
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
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
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
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
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
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
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
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欧阳予倩李金发曾卓周立波路翎师陀梁遇春陈白尘
王实味_王实味 -参考资料
[1]余杰,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A],王实味,野百合花[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A],王实味文存[C],上海:三联书社,1998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