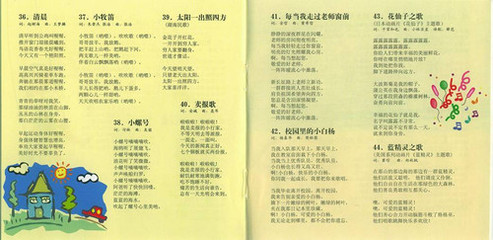《禹贡》言:“冀州地,即尧舜之都”。古冀州之所在,即在西黄河和东黄河两翼之间,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北部。“舜冀州之人”(《史记・五帝本纪》)。
尧舜_尧舜之都 -简介
陶寺遗址
在2010年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主办方将其命名为“尧舜之都”,但此举引发业界争议。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大概建于公元前2300年,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
2001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努担纲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再次大规模发掘。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
何努认为,陶寺遗址正是传说中尧舜时期的都城。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何努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质疑这些论断,认为论据还不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此前学界大多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距今3700多年。
尧舜_尧舜之都 -佐证
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
证据1
最早瓦片 突破“秦砖汉瓦”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西南22公里,临汾古为平阳。这座古城的城墙东西有130米左右,年代为距今4200年―4500年。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就是当时重要建筑的所在地。
社科院考古所学部委员刘庆柱说,陶寺遗址历史年代上与尧舜时期存在一致性。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在这座古城内,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区,其中最大的宫殿有1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制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有了瓦,意味着有了屋顶。这也打破了“秦砖汉瓦”的说法。有关考古人士笑称,这或许应该称作“尧瓦”。 本次展出中,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块瓦片,“泄露”了尧舜当年的生活信息。这件板瓦出自宫殿区,背面有泥,周边有白灰边勾缝迹象,因此考古专家判断其为宫殿屋顶上的板瓦,陶板瓦解决了建筑屋顶外装修技术上的漏雨问题,开创了古代历史上建筑用瓦的先河,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它是砖。
证据2
最早龙纹陶盘 “暴露”主人身份
在本次展出的陶寺文化中,产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彩绘龙纹陶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员介绍,在陶寺遗址内,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并出土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两个珍贵的彩绘龙纹陶盘就出自遗址的大墓当中。直径大约50厘米的彩绘盘,内饰盘龙,龙的口中叼一根松枝。
中国社科院考古专家分析,这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和等级,说明墓主是城中的统治者。当时的等级划分已经形成。考古界推测,该龙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从陶寺的龙纹陶盘开始,中国的龙形象开始演变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证据3
最早的文字 早于甲骨文七八百年
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在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用红色毛笔书写的字符――“文”字,“文”字的写法与后代甲骨文、金文中“文”字的写法非常相似。这改变了人们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的认识。
许多专家认为,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毛笔朱书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文字扁壶为残器,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同样用毛笔蘸红颜色书写的字符。这个字体尚未被确认,为上下结构,上为圆角方框,似乎象征着城;中为一横线,似乎象征着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个人做跪拜样,另外还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红色一周。说明是在扁壶残破后描绘与书写的。人们对这个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目前存在很多种解释,如命、易、尧、邑、唐等,争论很多,但是考古专家认为,无论哪一个字是正确的,都与“唐尧”、“夏雨”、“夏启”有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考古专家何努表示,以前国外考古界一直认为尧舜只是传说,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如果这个扁壶的背面是一个“尧”字,那么基本可以表明最早的文字提前了七八百年,也可以对尧舜文明进行进一步的佐证。
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由于文字不在正规的载体上,所以考古界尚不能明确肯定,但是很多考古专家是倾向于这个文字早于甲骨文这一认识。
尧舜_尧舜之都 -论证没有理据
陶寺文化早期的铜铃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发表了潘继安先生的文章《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简称《潘文》,后同),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不是很多学者所主张的“尧都平阳”,而应为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及帝喾之都。《潘文》先从四个方面分析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继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其早期为黄帝之都、中期为帝喾之都,最后以陶寺类型早期8座大墓的存在佐证该遗址为黄帝之都而非尧都,并认为“今人之所以多以陶寺遗址为尧都,以陶寺文化为尧文化,可能是由于过分相信了东汉末年的应劭及晋人皇甫谧的‘尧都平阳’说”的结果。认为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炎帝、黄帝距今5000年左右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但是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学者们从考古学文化和遗存的角度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论证和分析,相反,有少数学者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并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论证。炎黄五千年,中华民族和海内外炎黄子孙向以此自称和自豪。究竟炎黄、“五帝”是否实有其族、其人,传说中的炎、黄是距今5000年左右还是6000多年,其文化遗存是在龙山时代还是在仰韶时代,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史前研究、传说历史研究、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之一,而且也已经成为热点和中国史前研究的现实目标和方向:2002年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又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和2005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的召开[3]是其证。《潘文》的出现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打破了多年来学术界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在龙山时代而没有从考古学角度作具体分析和论证的尴尬局面,无疑有助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的深入。但是笔者认为,《潘文》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以下我们按《潘文》的结构和论证次序依次辨析,并指明其论证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方法问题,请读者和专家赐教。
《潘文》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县(清襄陵县治)东南四十一里,一名卧龙山,顶有塔,俗名大尖山,山之西峤亦曰卧龙岗”等文献,认为《尚书・尧典》(或《舜典》)说“放鹳兜于崇山”之崇山即今襄汾、翼城间的塔儿山。然后说“此山在尧时为鹳兜放逐之地 ,而其西麓即为陶寺遗址。但既为罪人放逐之地,则必非帝都所在,则其西麓之陶寺遗址,绝非尧之都矣!”此论言之决绝,但却基础无靠。同是《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慈利县・崇山”条却明确说:“崇山,县西三十里,相传即舜放鹳兜处”。又,明《万历慈利县志》亦载:“慈南裔荒服之地,在衡西北,舜放鹳兜于崇山即其域也”、“崇山,在县西百余里,舜放鹳兜于崇山即此”。道光《永定县志》载:“古欢兜冢,在县西南崇山绝顶,有巨垄,土人皆以见为不祥。”《直隶澧州志》载:“崇山,峙县西南,上与天门相连。山势嵯峨,顶有村落,其地平旷,可容千人。有八峰,最上巨垄,人传欢兜冢”。在《山海经》中,鹳头(即鹳兜)之国记于《海南外经》和《大荒南经》(鹳头同时又见于《大荒北经》,是说“颛顼生鹳头,鹳头生苗民”这种相生关系),而非《潘文》所论之晋南、中土。今湖南张家界市西南的崇山顶上仍有欢兜墓、欢兜屋场、欢兜庙等古迹,而当地民间亦多有关于欢兜在崇山征战的传说。所以《史记》说“放鹳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当有所据。尧舜放鹳兜之崇山,地在今湖南,亦为古苗蛮所在,这是自先秦以来古人和古代文献渊源有自的共识,《潘文》却自说自话,将放鹳兜之崇山自定为陶寺遗址附近的塔儿山,这种“考证”恐怕只能说服自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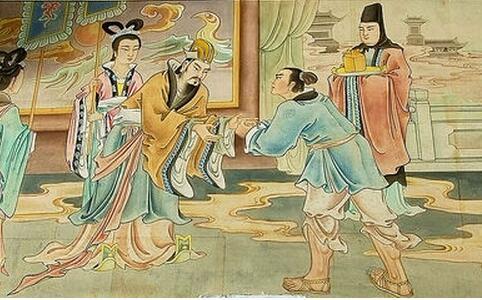
《潘文》引《韩非子》、《尸子》、《墨子》等古代文献,说“尧遭遇洪水,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尤其是在丧葬方面,尧舜都实行薄葬”,而陶寺文化“所有统治者的大墓都实行厚葬,随葬品一般一百多件,最多的达200多件,而这些华丽的随葬品,大多也是死者生前所享用之物,统治者的养生送死如此奢华,这完全同尧时的情形不相类似”,因而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这个理由看起来有据有理,实则不然。春秋、战国之际,上距尧、舜时代约2000年,其间没有文献记载、传承尧舜时代之事,韩非等人如何知道尧、舜“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以及“实行薄葬”?其记尧、舜之事只能依据代代相袭之心传口授,而关于“三皇五帝”之德行、品性,恐怕更多地会使用一些溢美之辞,乃至编造一些溢美之事,用以批评和敦促当世之统治者要施仁政、法先王。这个倾向在有关“三皇五帝”的古代文献中,自先秦自秦汉,莫不昭然若揭。学者尝以先秦文献可靠于秦汉及以下,或以《史记》可靠于其他文献。在笔者看来,关于史前之事,无论先秦或非先秦文献,无论《史记》或非《史记》,它们都需要重新考证、研究,尤其在史前考古材料极为丰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的今天。按照《潘文》的逻辑,《大戴礼・五帝德》、《史记》都说黄帝“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帝喾“博施物利,不于其身”、“取地之材而节用之”,陶寺遗址当然也非其所主张的黄帝及帝喾之都。古代文献把黄帝说得多么好:“昔者黄帝治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今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览冥篇》),而且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礼》)。比之于陶寺遗址贫富悬殊、晚期宫城和大墓被毁、早中期存在的战争(见《潘文》),它会是“黄帝之都”吗?
《潘文》说尧舜时代是儒家所盛称的“禅让制”时代,而据有些考古学者研究“陶寺墓地的大型墓葬埋葬得很集中,又有明显的排列顺序”,“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从而提供了当时部落首领已经实行世袭制的证据”,因而“当时的社会绝非禅让时代”,所以陶寺文化非尧舜文化。这个论断是将两个不确定的前提(即尧舜时代实行“禅让制”和陶寺大墓主人为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当作了确定不移的前提而得,故不可靠。尧舜禹“禅让”虽然见于儒家、墨家文献,但更多的文献却记载尧舜禹并非实行“禅让”。如《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韩非子・难三》:“舜逼尧,禹逼舜,汤伐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杀其君也,而天下誉之”;《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依据考古学文化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并结合古代文献研究,认为尧舜禹时期并非实行禅让制,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尤其田昌五先生对先秦诸子和古代文献说尧舜禹实行禅让制或非禅让制作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认为禅让说主要是孟子“按照他自己的天命观编制出来的,并无多少历史根据”、“《尚书・尧典》诸篇即所谓《虞书》,系战国时儒家后学之作……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合理史影,但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它代表着儒家的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有唐虞时代才是最理想的盛世”、“诸子百家对所谓的禅让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这种不同则直接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现实政治态度有关系。实际上,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观点编排古往的历史,而这样安排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是可想而知的”。有考古学者认为陶寺大墓反映当时最高权力的继承为世袭制而非禅让制,同样也有考古学者认为陶寺大墓反映的是禅让制而非世袭制。比如王克林先生就认为陶寺发现的9座大墓应是“属于陶唐时代为唐尧氏族部落联盟的墓葬”,是“当时部落首领权力更替前后承传实行‘禅让’制的生动遗迹”。因为唐尧、虞舜都是氏族、部落名而非私人名,依据文献尧仅有一子丹朱,所以王克林先生从尧、舜部落联盟实行最高权力“禅让制”的角度解释陶寺大墓。《潘文》依据两个不可靠、不确定的前提,推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
《潘文》引述多种考古报告和论文说明陶寺文化的年代约前2600―前2000年,并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200年一期,然后据《孟子・尽心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和“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推得尧舜之世当为前2200―前2100间,而此间正是陶寺早中期宫城被毁、大墓被掘扬尸的晚期,与传说中尧舜因“平治水患而进入天下大治的治世和盛世”不合,故陶寺晚期绝不是尧舜文化。那么“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陶寺文化”是什么文化、属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哪个部族的文化呢?《潘文》未予置论。首先,我们想指出,做史前研究、历史考证而引述《孟子》“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是极不慎重也不可靠的。《孟子》那段话的原文是:“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若禹、臬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岁余,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岁余,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这些话不过是想说明他自己想像的“五百年才(就)会出一个圣人”,感叹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当时已经没有人了解和继承了,怎么能用来作历史考证的依据呢?就算我们现在知道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岁余”大致不差,也不能据此就判定“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岁余”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尧舜、汤、文王、孔子这些圣人不是由上帝给我们安排、让他们每隔五百年就降生一个到人间来的。其次,陶寺晚期文化并非尧舜文化并不排除陶寺早、中期可能是尧舜文化,当然也不否定陶寺遗址可能是尧都。再次,《潘文》对陶寺晚期文化是建立在毁灭陶寺早、中期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一考古事实未予置评(事实上如将陶寺早、中期视为黄帝及帝喾之文化,则晚期在古史传说中就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韩建业从考古学角度结合古史传说进行的研究是可信的,即“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陶寺类型中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文化传统的衰弱,缘于陶唐氏的西迁和对西夏的征服。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晚期类型中大量北方文化因素(老虎山文化)的出现和东方文化因素的随之消逝,又是后稷所代表的姬周先民向南挺进的结果”,即陶寺早中期和晚期文化的出现及面貌的不同分别与“唐伐西夏”(《逸周书・史记解》)和“稷放丹朱”(《古本竹书纪年》)有关,而且由于“这两次大的冲突及其余波,直接导致了夏人主体东南向移动并终至创建夏王朝”。
《潘文》说:“纵观今人之所以多以陶寺遗址为尧都,以陶寺文化为尧文化,可能是由于过分相信了东汉末年应劭及晋人皇甫谧的‘尧都平阳’说,其实这‘尧都平阳’说是不足信的”。《潘文》对“尧都平阳”说不可信并未进行论证。其认识的前提是“如以陶寺遗址为尧都,按诸实情,实有种种不可能”即前述四个方面的推论。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推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因此《潘文》言“尧都平阳”说不可信只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愿望和思想。应劭的说法“年代甚晚”以及王国维也认为“尧都平阳”不可信都不是否定“尧都平阳”说的证据,甚至也不是理由。“不轻信东汉末年人和晋人之言”(《潘文》语)是正确的,但是要否定“东汉末年人和晋人之言”也需要论证和理据,《潘文》的否定则无理据。应劭“尧都平阳”说虽不明确见于更早的文献,但从另外的角度可证其说应该是有所本源的:尧又称唐尧、陶唐氏,唐、陶唐为地名、族名,《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中“唐人”即唐尧之后,证明夏之前唐人、唐尧即居于“大夏”(今晋南)。商代甲骨文有“方出其唐”、“方不出于唐”、“贞,作大邑于唐土”之语,王克林先生引陈梦家、丁山先生的考释,证明唐地、唐土在今晋南临汾盆地。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之语。可信应劭“尧都平阳”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要否定它还得努力寻找证据。
《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推论是可靠的,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之后,《潘文》又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这六个方面是:1、从陶寺一带古名大夏,论证其为黄帝所居之地;2、从陶寺遗址有早期小城与中期大城论证其为黄帝、帝喾之都;3、从陶寺城址内曾有早中期宫殿建筑存在论证其为黄帝之都;4、从陶寺遗址有早期水井论证其为黄帝所居之地;5、从黄帝以玉为兵论证黄帝之都在陶寺一带;6、从陶寺遗址出土鼍鼓特磬及发现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论证该遗址为帝喾之都。这六个方面以及《潘文》的“附考”部分都共有一个假定的大前提,即传说中的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亦即陶寺文化或遗址早期的年代(前2600―前2400年)。《潘文》在行文中说“考黄帝之年代,约当陶寺文化早期,是当黄帝始立城邑之日,正是陶寺早期小城出现之时”,又说“陶寺早中期宫殿建筑中之早期建筑,按其年代正当古史传说中黄帝之时”、“陶寺早期按其年代约当古史传说中黄帝之时,是当黄帝‘始穿井’之日,正是陶寺早期水井出现之时”。然均未见具体考证和推算黄帝年代,言“考”而未考。除了用“考黄帝之年代,约当陶寺文化早期”十余字虚晃一枪、遮掩而过,《潘文》整篇都没有一段话、一句话考证和推算黄帝年代,实际是默认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在此默认和假定前提下来“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在中国史前考古尚未开展或发掘材料非常有限的年代,人们依据古史传说资料将黄帝年代定在距今4500或5000年左右,似乎无可厚非;而在今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考古发掘材料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仍将一个传说年代用来框考古材料,作史前研究和传说历史研究的基础或默认前提,这在方法和方向上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结论的可靠性、正确性就只能依赖于碰运气了。在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分析一下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依据何在,是否可靠和可信。
现、当代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600年左右。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中国历代人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时王云五总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均是。这个年代有什么依据呢?《辞海》有一个说明,所附《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列出三种黄帝纪年:一是《民报》的4609年,二是《黄帝魂》的4622年,三是《江苏》等报刊的4402年(均以公元1911年为始点上推)。“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辞海》附表说明)。《民报》纪年又怎么来的呢?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纪年“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史式指明其推算方法是: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和皇甫谧二人均非史学家,“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 、“《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
除上所述卢景贵的方法外,现今的学者多是以《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古书所载“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禹、夏、商、周的积年为基本资料,再以一个可靠的历史纪年如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为基点进行推算。由于对“五帝”的理解不同(有的增加少昊或帝挚)、古书中关于“五帝”各自的在位年数也有差异,同时夏、商、周各王的年代也没有定论,所以不同的学者得出的黄帝纪年便各不相同,但黄帝年代大都在前26世纪――前25世纪及其左右徘徊。如翦伯赞得出的黄帝元年是前2550年,杜正胜认为黄帝年代“不会超过西元前2500年以前”。当然也有黄帝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这个框架之外的研究和认识,如许顺湛以《春秋命历序》关于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为基础,以夏代立国约距今4100年左右进行推算,得出黄帝始年距今6420年左右,曹昱将《春秋命历序》与其它资料综合考虑,得出黄帝出现时间为公元前3706―前3306年的认识。
在古代,也有学者推算黄帝年代。如《汉书・律历志》载元凤三年(前78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