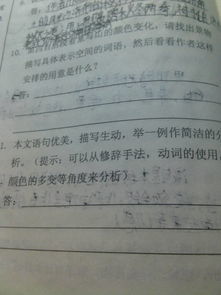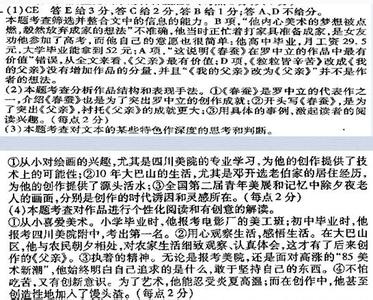文/二毛
(一)
小时候,家里盖房子,父亲总是请来木匠二叔。二叔有一套把戏:斧子、刨子、锯子、墨盒等。那时的房子,房梁、椽子都是木头搭建,门窗户扇也是木头制作的。印象最深的是二叔将一根长木头固定在长板凳子上,双手握着刨子,沿着长木头刨去,一片雪白的木花便呈现于眼前,散发着新鲜木头的芳香。我很喜欢把玩那些薄薄的、翻卷着的木花,放在掌心,犹如观赏盛开的梨花。刨好了木头,二叔用墨斗在长木条上划线。他将墨绳的一头用铁钉固定在木头上,然后使劲从墨盒里拉出一段墨绳,大约有木头长,用手拽紧,固定在另一头,再提起墨绳,用手弹一下,一道笔直的墨线便印在木头上。
二叔还会做许多家具,木桶、碗柜、澡盆、衣橱,那时常见他背着他的那一套把戏往返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如今二叔早已不做木工了。每次回家乡,总能看见硬朗的他,很想问问他是否怀念他的刨子、斧子、锯子呢。
(二)(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阴雨连绵的季节,父亲常在家里编箩筐。
他将刚砍回的新竹子堆积在院落里,用镰刀砍去了竹枝,再用细长而薄薄的竹刀将竹棍劈成竹青、竹篾。那竹青用来编筐口,那竹篾用来编筐身。父亲坐在一片片青青的、白白地竹条上面。那时我总觉得父亲是坐在云端,从神话故事中飘飘而来。青青的、白白的竹条,总让我想起《白蛇传》中的小青、白素贞。青青的竹条蜿蜒着、跳跃着;白白的竹条,蹦跳着、弯曲着。怎么看都觉得是小青、白素贞曼妙的腰肢。适逢雨天,忙完了农活的父亲一边哼着山歌,一边缠绕着竹条。一瞬间,我感受到有股暖流入心田。是啊,父亲很难和我们姐弟在一起。我第一次感受到和父母相守一起的美好。父亲手巧,半天功夫就编出一个大箩筐。
那时,父亲还会编织大筐、簸箕、筛子等。
后来,父亲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忙碌于建筑工地上的他,再也没在家编制竹器了。
父亲去世几年了,但雨天编筐子的画面,只要想起,就觉得温馨。
(三)
傍晚时分,西方的天空燃烧着一片绚烂的赤色的晚霞。放学了,我背着小书包向家的方向走去。
南街的铁匠铺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响,我循着声响朝那儿跑去,辍学的堂哥就在那儿打铁。他穿着红汗衫子,外面罩着赭褐色的大皮裙。他一手用大钳子钳住铁锹,一手拿着大锤子。抡起锤子砸下去,砸起许多火花,如空中绽放的烟花,又像天空闪烁的繁星。几分钟后,堂哥将烧红的铁锹放入水桶中,哧啦,哧啦,水桶顿时蒸腾出许多雾气,宛如秋晨池塘里的烟雾。
铁匠铺如烧透了的砖窑,幼年的我总不敢靠近。堂哥额头上的滴滴汗珠,红汗衫子上大大小小的黑洞,永远鲜活在记忆深处,难以忘怀!

后来堂哥,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走进了城市谋生。我想他不会忘记他的铁匠生涯,因为那是他踏上社会这个大舞台的第一个驿站。
(四)
节假日,父亲和弟弟最爱的去处是北街的理发店,小叔是那儿的剃头匠。他的理发店,有一个黑色的大转椅。这个椅子可以四面八方转动,还可以升高降低。他还有一把推子和几把剪刀,一个白色的大围裙。
理发时,他将大围裙给你围上,然后细细地推,轻轻地修剪。几个回合,就将弟弟的头发理得干净清爽。
我还常见小叔挎着剃头筐走村串巷,选一处宽敞的地方坐下来,不用吆喝,就有人自动找来了。小叔不单给人理发,还给刮脸、铰鼻毛、掏耳垢等。服务态度周到细致,受到村子里人们的好评。为了感谢小叔上门服务,父亲常邀小叔来家里,喝杯高粱酒。
如今,回到家乡,挎筐子的理发匠已见不到了,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个发廊如雨后春笋般长了出来,那发廊的名字既新潮又富有韵味,什么“又一春”,言外之意,你在他那儿理发了,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什么“梦舒雅”,那意思是,你在他那儿理了发,既舒服又优雅。理发师呢,多是时尚优雅的英俊小伙。
童年生活的记忆里,我那古朴的乡村,每天都能听到“抢刀磨剪子哟”“补破锅破桶哟”的吆喝声;耳畔也时常萦绕着铁匠铺子叮叮当当,裁缝铺子的哒哒哒哒声。每天都能看见石匠们背着铁钎、石锤奔向山野;总能望见木匠们背着刨子、墨盒走进建房的人家。这些匠人,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每每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的眼眶湿漉漉的。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我那曾经贫穷的山村;是他们素朴地装扮着,我最初的生命里那段隆重又清浅的时光。如今,他们都渐行渐远,只留下遥远的背影,尘封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时常想,随着父辈的逝去,我们的传统手艺还能传承下来吗?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