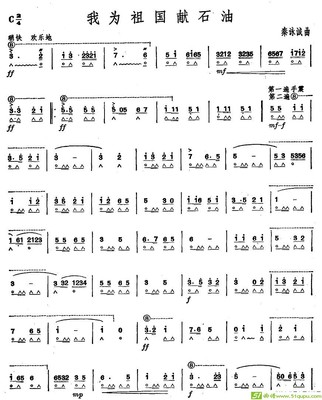在外浪荡多年,最思念还是故乡,故乡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如在昨天。故乡如陈年老酒,时间愈久愈是醇香。除过亲情故乡是我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
一九六二年我出生在秦岭脚下华山南麓洛河畔。秦岭横跨陕西东西,将陕西乃至中国一分为二,陕西秦岭以北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地势多平坦,物产丰富。秦岭以南山势陡峭,山峰秀丽多河谷,中国南北分水岭。秦岭以北属于黄河流域,秦岭以南属于长江流域.我小时候性格倔强,就像我家门前流淌的洛河一样,沿着秦岭脚下往东逶迤而去,投奔黄河最捷径,翻过秦岭是黄河,仿佛北边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北洛河在向他召唤。洛河投入黄河是真理,山里人做小梦想都去山外谋生,虽然有巍峨秦岭阻挡,我的性格像洛河一样叛逆,秦岭以南的江河多注入长江,陕南唯有洛河不辞艰难万险,依然要回归母亲河---黄河
横在陕南人面前最大一座山是秦岭,往南丛山峻岭,万仞沟壑连绵不断,我的家乡商洛山更是不在话下。山里人韧性,山里人坚毅不拔,山里人倔脾气,忍耐脾气都因这大山磨练而成。山里人质朴就像江河清泉透明甘醇晶莹,像大山一样厚重。七一年这年我一定九岁,村里的伙伴都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吃过晌午饭,来到里洛河水不远岸边玩泥巴,突然身后传来一个人的叫声:“山娃山娃,你怎么不去上学呢?”我回头看是生产队上保管何德义大叔。我看着德义大叔无奈的说:“家里没有钱!”哦,德义大叔对我说:“你上来,跟我找你家里人去,现再就在咱家门口上学,咱村里办了一个初小。”我听后高兴地跟着德义大叔去找父母。当时我们姊妹五个,大哥去当兵,只有二哥在上学,我和大妹子都一定到了入学到年龄,家里困难,吃了上顿无下顿,哪有钱上学。
德义大叔拉著我的手,见到父母后就数落父母,父亲蹲在一边一声不吭。后来德义大叔说我身上只有一块五毛钱,报名费是两块五毛钱,你看家里有了,或者那里能凑够把娃领上报名去。父母还是为难,德义大叔就把我领上去报名。学校就在村子东头生产队的仓库里。没有凳子没有课桌,课桌是几块长条木板。学生是一二三年级初小,一个老师。老师姓李,我们叫他李老师,家在我们村子下面一个村子。和我同岁或者比我小的伙伴一定在三年级二年级读书,李老师看在生产队干部份上让我报了名。我学习专心用功一个来月数学语文我就学完,老师出题我都圆满答完。李老师很高兴,同学佩服我。这是我求助我的同桌上三年级治劳教我二年级课程。二年级就是加减乘除,主要是背乘法口诀。
对我影响学习最深的是春天闹春荒,十冬腊月挨冻。春天青黄不接,一天两顿稀汤有时都喝不上,饿得头昏眼花是经常的事,没有饭吃时,我们兄妹包括父亲在内,就是家里土炕捂觉,谁也不出门,母亲拿着升子,或者一个瓷碗东借西借一点玉米面下锅。父亲身材瘦小,胆小怕事,有什么本事,家里全靠母亲撑着家庭。麦子没有熟就割,玉米没有熟就板,说不定这里推着石磨磨面,那里就等着下锅。没有煤油照明,没有盐吃,我们家里装盐的小木桶里面无盐时,用清水涮涮不知道多少回。

学校资金短缺,生产队给了我们学校几块地,就在我们学校后边,很近。我们勤工俭学,破四旧、立自新挖几座老坟墓,开垦出来在上面种上中药材。补贴学校办公和我们的学杂费,学生里我的身体棒,力气大,劳动我最积极,我就是劳动委员。一年的学杂费不要了,我的学习用纸和笔总是无着落。生产队长兼生产队会计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把废弃用完的旧账本让我在背页,算题写字。还有他没有用完的铅笔头,或者剩余墨汁。家里买不起纸笔,我在地上沙滩上,烧纸上练习写字,什么方法都用过。(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我们学校周围住着不少的五保户老人,我们下自习常常帮助老人干活。抬水扫地打扫卫生。老韩爷我经常给他挑水,老韩爷是老木匠,驼背闪腰,走路下巴接地不远,所以吃水困难,人已年事已高,经常卧床不起,但是老韩爷脾气火爆村里也是出名,村里人都害怕。最有趣是,队上拉了水力发电,老韩爷不懂科学,烟瘾犯了,老韩爷用的长旱烟袋想借火,怎么也点不着,一气之下用旱烟袋砸去,灯泡打了坏了。想想那时火柴也奇缺,谁家点火做饭,常常能看到东家西家去有火人家引火。老韩爷对我不错,每次去他家老韩爷伸出黑不溜秋的手,去悬挂横梁馍笼里摸一块黑不溜秋像黑狗一样黑的馍馍给我充饥。村里人都知道老韩爷人脏兮,接他东西让人瞧不起。而我接着后,偷偷地在没有人的地方偷着吃,我有一种感激的心情,我饿啊!
关心我不至于像何叔叔、老韩爷还有很多。十冬腊月,一定数九,我屁股上只裹着大哥从部队捎回来一件大裤头。身上没有衣御寒,脚上没有鞋子防冻。我光着脚丫子上学,实在不行了,我把脚抬离地面,悬空抖落或者伸进一定烤火取暖熄灭地火盆温灰里取取暖。天天这样子,村里人看我可怜,五保户老严叔把他一件灯芯绒的上衣送我,他说这是修洛华路发的,村里人都叫他严营长,说他在修洛华路镇旬路时当什么领导,而他真名叫严兴昌。我穿的鞋是后来村里婶婶把她的塑料布鞋送给我。这一年天依然寒冷,而我在温暖中渡过。
我在张湾初小毕业后,后来到薛湾小学上学。那时批林批孔、学习黄帅反潮流、学习张铁山缴白卷、斗批地主犯坏右。我在这段时间里,看小说,写作文,看连环画,学画画。四大名著,暴风骤雨,沸腾的群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山菊花,欧阳海之歌,杨朔、巍巍的散文等等,我看了不少的书。而我学习一落千丈,政治学习考试闹笑话。三要三不要就悬挂在戏楼上,在我的眼前我就是没有答对。我答我心里所想所理解地,同学们奚落我。
本该在七六年毕业升入初中,可是这一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我也在这一年遇到不幸。我玩炮把眼几乎炸得失明,休学在家一段时间。家里也没有给我看眼睛,右眼后来终生失明。学杂费家里从来没有给缴,还欠学校几块钱。同学讥笑个别老师看不起。上初中离家里更远,没衣没穿没吃没钱上学怎么保障我。那是离家很远的柏峪寺中学,上学要从家里自带包谷糁伙食费,被褥碗筷等等,家里根本拿不出来。我心里越来越失落,有一天因一点小事校长在课堂上羞辱我,我愤然摔书离去。这年是1976年6月15日,回家后我不知道哭了多少回,醒来枕头边常常流湿的泪,我想到了自杀,我叹息我生在穷人家,父亲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把农药藏起来,给我说几句宽心话。我不能忘记我的班主任,他姓吕,应届高中毕业生,回乡给我们带五年级语文和全校体育课,那时他风华正茂,对我是最关心的一个。送一支钢笔,纸张,一双运动鞋。常常叫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晚上和他共用一条被子窝里睡觉。回家后吕老师后脚后跟就到我家看我,希望我继续好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吕老师调到我们张湾初小兼代课老师。我年龄小生产队上活我干不了,生产队办扫盲班我就那里学习,实际就在初小里学习。我在家里没事看毛选毛主席诗词,报纸,凡事有文字的东西我都看。晚上去吕老师那里学习,吕老师有时在学校住,有时回家住。吕老师把教室和他地办公室的钥匙留给我,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学习。那时我在他那里看书就是到天亮,不小心头发让煤油灯燎过几回,这是我瞌睡打盹时的事。
八四年七月四日陕西农民报发表了我一篇豆腐块新闻,后来有陆续该报发了两篇,在洛南县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几篇我不知道了。我记得农民报每次给我邮寄两元稿费,电台每次八毛钱稿费。我喜欢的是文学写作,喜欢小说,喜欢诗歌。新闻报道是在我万不得第的情况写的。我的稿纸信封都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我付出的多,稿费根本是连我书纸都够用。我因学习别人嘲笑过我,挖苦我书呆子,秀才,作家。延河,萌芽,秦岭文学,我都投过稿。多是退稿信,也有鼓励。八十年代初我看到陕西青年上一则消息,怀揣着从朋友们手里借的七十元钱跑到湖南宁远九疑山求学。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回家无望,自卫反击战正热火朝天。这里离广西近,治安查得紧,我在郴州火车站候车室无钱住宿被赶出候车室。忍饥挨饿一路颠簸来到了安徽凤台,颍上得到好心人帮助,我就在当地砖厂打工。在这里干了两年准备回陕西老家。在我要走的哪一天突然得了疟疾病,在朋友胡秀典家里有半个月不能下床,我说胡话,高烧不退,听他们说最高到41.5度。胡秀典的母亲给我打荷包蛋,秀典给我叫医生挂针,病好后我对秀典的父亲母亲跪下磕了三个头谢恩感激。多少年过去我对他们总是念念不忘,可是这些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联系不上。胡秀典的家应该是安徽省颍上县姜店区林庄村三队。感谢你们一家好人,我一直怀念你们,想看望你们就是联系不上,2010年我从上海回陕西,晚上坐火车路过你们那里,望着车窗外黑黝黝安徽大地,思绪万千,这里曾经是我生活的地方,这里有帮助收留我的大哥大婶。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全国各地来来回回跑、包过活、做过小贩、做公路上施工员、搞过摄影,后来我来到省城西安,一直在一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做带班技术员。在西安自我感觉我遇到世上最好的老板,他们关心我生活各方面,一直到我结婚娶妻生子,在城里买下房子,户口迁进城里。三十多年过去了,送我上学给我一块五毛钱的何德义叔叔、给我一块馍馍老韩爷、给我衣服穿的五保户老人,激励我成长的班主任、救我命的安徽大娘、关心成家的公司老板,还有帮助我的少年伙伴,在部队工作朋友,给我邮寄书籍稿纸,写信鼓励,关心我生活方方面面。在县城给我吃住的一块长大的朋友们,我有病他们给我端水送药,不是父母同生,但却有亲弟兄般的感情。虽然我生活在外地,但是我时不时地打探家乡的消息,谁谁不在了,谁谁家儿子结婚了,我都牵挂。今年七月我回趟故乡,当年的兄弟朋友染上了岁月的沧桑,我摸着一位大哥的手,由不得我直掉泪,他们一定苍老。老家没有我立锥之地,我在西安上班时我的老房子一定坍塌,后来邻居占用。每年公司春节放假,我就在他们家和要好的亲亲朋友家过完春节去上班。他们安慰我的话∶“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们就高兴”老人们大都去世多年,我怀念他们愈来愈浓,就像秦岭山那么厚重巍峨,他们一直在我心里。
2013年9月11日 23:27:934 秦岭山夫 草于宝鸡凤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