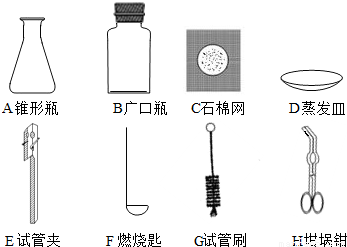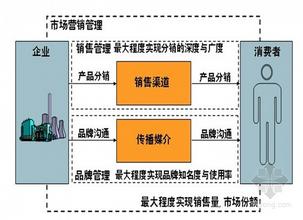“达尔文主义”通常用以指称以自然选择为手段解释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与多样性的生物进化理论。尽管这一词项中包含C. R. 达尔文的名字,但它在语用上并不完全等于达尔文自己的生物进化理论。那么反过来说,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往往也并不存在淘汰第三种蛙的因素;而且,第一种蛙的生存环境往往也并不存在淘汰前两种蛙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基因“突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变化”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话,那么,在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里就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有第二和第三种蛙的共生现象;而三种蛙共生也就应该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了。的确,连恩格斯也说过:“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任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⑦。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历史概要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观念
在 达尔文之前,大多数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解释都秉承了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 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第三版的历史概要中写道:“直到今天,大多数博物学家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被分别地创造出来。许多作者都巧妙地维护着这一观点。”
但生物进化的理念并不源自达尔文。早在达尔文祖父那一代就流行着生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而一些自然哲学家更是被看作达尔文的先驱。例如E. G. 圣-希莱尔认为,识别同源性是梳理进化关系的核心手段。J. L. N. F. 居维叶则反对希莱尔的观点,并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物种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为根据他的观测,每个物种的结构看上去都像经过了细致的调节,以至于最微小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功能受到破坏。居维叶同意地质灾变说,并认为部分物种会随着地质灾变的发生而消亡。与居维叶同时代的J. B. 拉马克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他认为物种会发生变化;动物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物种的变化是通过继承获得性状得到的。在拉马克1802年的论文中,他描绘了一种进步式的进化理论:“[物种]从最简单的上升为最复杂的……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产物会相继地产生出其它产物。” 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中,拉马克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物种的变化受到外部坏境变化的影响;第二,在物种的多样性之下存在着统一性的基础;第三,物种总是会进步式地发展。相比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拉马克的理论呈现出以下三个不同点:第一,他的解释中没有提及自然选择的机制;第二,他认为物种是朝着完美的方向发展的;第三,拉马克的理论中不存在物种灭绝。
此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上述理论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P. J. 理查森和R. 博伊德认为,“在达尔文之前,人们将物种构想为具有本质的、没有变化的类型――就像几何图形和化学元素那样” ,而达尔文则在族群的层面上思考物种。达尔文的这一观念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环境
除了这些理论先驱之外,部分社会环境对达尔文理论的产生与传播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热衷于收集化石,而这些对这些化石的研究为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人们收集化石的热情并不源自对生物学知识的渴求――这一行为主要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根据W. 佩利的想法,如果我们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块手表,那么会认为这件精致的东西是被人设计的;同样,当我们发现结构如此精美的生物时,就应该相信这些东西是上帝设计的。人们收集化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寻找上帝的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创世的自然历史遗迹》在1844年匿名出版。(后来作者被鉴定为R. 钱伯斯。)这本书中提倡“进步主义”的进化理论。其中认为物种的变化由遥远的、神圣的创造者所管制。此外,像当时许多博物学家一样,作者相信每个物种都是分别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共同的祖先。《遗迹》是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流行的“科普读物”。尽管科学界对它的反应十分冷淡,但直到十九世纪末,该书的销量都胜过《物种起源》。达尔文也指出,“《遗迹》在1844年出现……在我看来,它很好地让这个国家的人注意到这个主题……并为人们接受类似的观点准备了基础。”
此外,达尔文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相反,当A. R. 华莱士与达尔文在1858年联名发表论文并召集博物学家旁听时,大家对这一理论几乎完全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其中并没有特别令人震惊的革命性理论。甚至在1859年《物种起源》第一版出版时,公众也只是反应平平。同时,M. 鲁斯认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同源学。“适应器[这样的概念]对于尝试着辨别同源性的人来说只是一个麻烦” 。
从上述历史中可以看出,达尔文的理论并不是含着银匙凭空出世的。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为其代言、造势,并创造出“达尔文主义”一词的事实上是华莱士。但是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 辉格史观的“达尔文主义”多指华莱士所倡导的“纯粹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基本简介
达尔文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他在环球航行期间以及研究家养动植物时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自然选择的主要内容包括变异和遗传、生存竞争和选择等。变异是选择的原材料,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有利变异在种内经过长期积累,导致性状分歧,最后形成新种。生物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缓慢进化的。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还有T.H.赫胥黎和E.H.海克尔。
达尔文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新达尔文主义的由来
达尔文对批评的回应
自《物种起源》出版后,许多人对达尔文的 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了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来自St G. 密瓦特和F. 简金。
在密瓦特对达尔文的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然选择这样渐进式的进程超出了当时地质学理论所允许的范围。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 莱尔的地质学理论影响。在1830年出版的《 地质学原理》中,莱尔描绘了缓慢、渐进的地质变化过程;而他所估算的地球年龄也略长于他同时代的理论家。但是物理学家W. 汤姆森用热力学定律重新估算了地球年龄。他通过计算地球从融化金属的温度冷却到当前温度所需的时间,得出地球年龄为1-4亿年的结论。其中可供生物进化的时间为1000-3000万年。而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生物进化至少需要3亿年。汤姆森的这一结论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发现利用同位素测定地球年龄的方法后才被否定。
简金的反驳主要基于当时流行的混合遗传(blending inheritance)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脖子较长的长颈鹿与脖子较短的长颈鹿通过交配繁殖出的后代是脖子中等长度的长颈鹿。那么如果只存在一只脖子较长的长颈鹿,它只能与其它脖子较短的长颈鹿交配。数代之后,其后代的脖子会越来越短,到最后几乎与其它脖子较短的长颈鹿一样。简金把这样的后果称作“沼泽效应(swamping effect)”。如果沼泽效应是对的,那么自然选择根本无法将具有适应性的性状保留下来。
为解决这些问题,达尔文在1868年的书中提出了他的遗传理论: 泛生论。在这一理论中,达尔文事实上允许了拉马克式“获得性状遗传”的存在。达尔文认为泛子(gemmule)可以沉睡和再现,因此它不需要在每一代中都被表达出来。(具体参见 泛生论。)在引入了泛生论后,达尔文通过用获得性状遗传机制解释部分生物进化现象而缩短了进化所需的时间,并回避了沼泽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达尔文的理论大多只被应用于植物和其它较低级的生命形式;第二,就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陈述的那样,致残(mutilation)无法被遗传。他在解释泛生论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基于以上两点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A. 魏斯曼切断老鼠尾巴的试验事实上无法证伪泛生论。
华莱士与新达尔文主义
讽刺的是,“达尔文主义”一词在达尔文死后才开始流行。华莱士1889年出版了《达尔文主义》一书。华莱士希望借此推进一种“纯粹的”达尔文主义。它拒绝了达尔文的泛生论以及其它所有承认获得性状遗传的内容。在书中,华莱士提到:“……我的所有工作力图展示出在新物种产生的过程中自然选择压倒性的重要性。因此我站在达尔文先前的立场上……我认为这本书的立场是在拥护纯粹的达尔文主义。”
华莱士认为魏斯曼的理论完全支持他所提出的纯粹达尔文主义。魏斯曼的工作驳斥了“用进废退”的获得性状,并在身体细胞(Soma)与遗传物质(Germ plasm)之间放置了壁垒。但事实上,魏斯曼并没有完全否认外界因素对遗传的影响。他区分了“自发的胚芽选择(spontaneous germinal selection)”与“诱发的胚芽变异(induced germinal variation)”;只有前者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基因突变。
G. J. 罗曼斯创造了“新达尔文主义”这个词。从他的另一个表述,“极端达尔文主义(Ultra-Darwinism)”中可以看出,罗曼斯本人将“新达尔文主义”看作一个贬义词。他将“新达尔文主义”和“纯粹达尔文主义”用作“华莱士主义”和“魏斯曼主义”的同义词。“这样我们就能区分出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和与之对照的华莱士的达尔文主义,或者说,跟后者是同一回事的魏斯曼的新达尔文主义学派。”
F. 埃尔斯顿-贝克认为,新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直接从华莱士那里跳到了魏斯曼那里――其中并没有经过达尔文。“确实,即便达尔文从未存在过,我们大概也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今天的新达尔文主义。华莱士提供了自然选择的理念,并像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那样是严格的选择论者;而魏斯曼的作用显然是引入了隔离遗传物质的理念――它将除了自然选择之外的进化方式全都无效化了。”
从今天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情况看,新达尔文主义并不比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更加优秀。生物学中的 表观遗传可以被看作是获得性状的遗传,而在 文化进化理论中,社会科学家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将文化单元与基因进行严格类比的做法。因此,从适用性上看,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并不“落后于”新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重要贡献
19世纪下半叶,细胞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陆续发现了细胞核、染色体以及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等重要事实。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魏斯曼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认真探讨了遗传和进化问题。他做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实验,发现连续切割22代,小鼠尾巴并未变短,他由此否定获得性状遗传(见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提出,生物体由种质和体质所组成。种质即遗传物质,专司生殖和遗传;体质执行营养和生长等机能。种质是稳定的、连续的,不受体质的影响,它包含在性细胞核主要是染色体里。获得性状是体质的变化,因而不能遗传。魏斯曼认为,进化是种质的有利变异经自然选择的结果。1917年,摩尔根提出“基因论”,把魏斯曼的种质发展为染色体上直线排列的遗传因子、即基因。新达尔文主义是进化学说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斯曼把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结合起来,开创了进化论研究的新方向。他首次区分种质和体质,指明了遗传的物质基础及其连续性,在遗传机制上补充了达尔文的观点。这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贡献。然而,魏斯曼把种质和体质绝对对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争论焦点
达尔文主义与非达尔文主义都是进化论的分学说。
达尔文主义坚持认为进化的动力在于“自然选择”。重视环境和生态的作用。
非达尔文主义则认为在DNA分子水平上,认为生物进化所标保留下来并不都是所谓的“适应环境的性状”,而是“这个形状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这个物种的生存”。人们在研究DNA分子结构和基因结构时,发现由贮存遗传信息的核普酸分子的置换所造成的基因突变,除了有害的之外,能够保留下来的有利突变是微乎其微的,大部分则是对于自然选择来说既无利也无害的“中性”突变。如果把轻度有害、近似中性的突变算在内,中性的则占整个突变数量的大多数。因此,在进化中担任主角的不是“有利突变”,而是“中性突变”。
达尔文主义学派侧重从生物体结构的高层次、从生态角度考察进化问题,非达尔文主义学派侧重从生物体结构的低层次、从生化角度考察进化问题。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出了相互矛盾的看法,
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学说。然而,如果全面考察这两个层次上的进化机理,即可发现这两种学说并不是绝对排斥、互不相容的。高层次与低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两个层次上都存在有利、
有害和中性这三种变异。单用选择说或单用中性说都不能全面说明任何一个层次上的进化机理。从认识论上说,无论是选择说还是中性说,都是对进化问题认识的一个方面,是认识发展过程的一个片段,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都不能把任何一种学说绝对化。
达尔文主义_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的终结
进化论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自然科学基石;不用说,达尔文及其学派对进化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尽管人们往往知之不多,但早已默许、习惯了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却是一个错误的进化观!而且,达尔文主义也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
比如:恩格斯生前就曾坚定地站在达尔文一边,驳斥狂妄的杜林先生;同时也明确指出:“…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①。”而且,恩格斯还曾特地申明:我们只是“暂且承认‘生存竞争’这个公式。②”至于我们还知道的:西方现代达尔文主义学派一般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不是一回事。
可惜,恩格斯生前没有来得及作较为系统的进一步探讨,没有留下经他“大大修正”了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一百多来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中,达尔文主义一词也差不多完全被进化论所替代,以至人们只要一提起进化论差不多都是指达尔文主义。似乎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进化观;似乎达尔文主义“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再也没有人怀疑了…
那么,恩格斯生前又为什么“毫无疑问”的要“大大修正”呢?恩格斯的意见是否早已陈旧过时;原本就没有必要区分两种不种的进化观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不赞成教条主义。因此说到底,达尔文主义究竟有没有错?它的错误性质究竟怎样?是不影响进化论的发展还是已成为其发展的障碍?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可以永远建立在这个不正确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呢?
这里,我们就来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但愿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一,重审达尔文主义
美国动物学大师,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老克利夫兰,对其有一段极精当的描述,我们谨摘录如下:
“该原则乃是根据这样的观察事实:没有两个生物是完全相同的;至少有些变异是可以遗传的;所有类群都倾向于产生太多的同类;因为繁殖的个体比可生存的个体多,所以在个体之间存在竞争。按照达尔文的看法,在生存竞争中,具有能使之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的那些生物就会生存下来。如果它们生存了下来,因而比有利变异较少的生物有着较多的后代的话,那么它们的遗传特征就会以较大的比例出现在一个世代中。这种自然选择继续下来,就会产生连续的进化变化。③”
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或原理)。毫无疑问:“没有两个生物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所有个体之间都存在差异。但是,并非所有差异都是变异。同样也是观念事实:所有生物类型的形态特征、大小及颜色等都有一个大致的差异范围;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个范围内的差异,都将其视为一般差异;只有那些明显超出这个范围的差异,人们才视为变异。这里显然撇开了这个无疑十分重要的逻辑划分,直接就跳到了变异的遗传。“至少有些变异是可以遗传的”那么,哪些变异可以遗传?哪些变异又不可以遗传?差异与变异在遗传中的意义是否完全一样?决定遗传和不遗传的原因又是什么?不用说,遗传是研究生物进化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可惜这里都没有提及。“所有类群都倾向于产生太多的同类”显然,这只能一般地说;比如大熊猫就不“倾向于产生太多的同类”。这且不说,这里又撇开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观察事实:各种生物的繁殖能力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生物的繁殖能力一般总与后代的成活就率成反比。比如在自然界,虾类一次能产几十万粒卵,却只有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成活率;而许多高级哺乳动物一次只产一二个幼子。达尔文自己就曾告诉我们:生物不同的繁殖数量是与它们是否能有效的保护后代相关的。因此,我们也并没有理由来否定这样一个推论:生物各不相同的繁殖能力与各物种不同的繁殖方式一样,也是对繁殖环境的一种适应。
显然,这里的目的无非是为下面的推论服务:“因为繁殖的个体比可生存的个体多,所以在个体之间存在竞争。”不用说,这个前提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还没有被繁殖出来的个体是无所谓生存的。这样的“事实”不需要“观察”,当然也不能算真理。况且,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在蜂巢中,后羽化的新蜂王往往还没有露头就被前者消灭了。其意义不过是当第一只新蜂王意外死亡时,总还有第二、甚至第三只来补充,从而增加了该种群能够及时延续下去的保证系数。当然,两只新蜂王同时出来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毕竟很少,而且,这也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为了尽可能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先蜂王产下两枚王卵所间隔的时间总比两只非王卵多的多。
在这里,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些大型的鹰类。它们不象家禽那样同时孵出许多雏鸟,而总是分先后孵出两只雏鸟。一般情况下后者也不具备与前者竞争的能力,如果是食物短缺的年份,那么首先被淘汰的总是后者,除非前者意外死亡。因此我们说,这实际上也是对繁殖环境一种机动的适应:是在繁殖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食物短缺,以及意外事故的积极预防。“按照达尔文的看法,在生存竞争中,具有能使之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的那些生物就会生存下来…”最初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象上述两个例子,淘汰或生存的顺序其实早在新个体被繁殖之前就基本确定了,这与个体是否具有什么变异并没有什么关系。再如在马、鹿一类动物的种群中,最容易被淘汰的不也总是那些最幼小的个体吗?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主义往往就把个体之间的竞争上升到种群之间的竞争,以此来凑合淘汰论。然而,正如“没有两个生物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两个生物种群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内,两个同类生物种群所享受到的环境条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说到底,无论是对于不同的生物个体还是不同的生物种群来说,决定生存与否的因素都是多方面的,是否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充其量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只有在其它因素都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达尔文的这个推论才成立。
举例来说吧,有两匹小马,其中一匹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比如跑的更快;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才是这两个个体之间生存与否的决定因素呢?很显然,这两个个体必须同样大小、同样健壮、同时发现危险,而且,与危险的距离也同样,它们的反映速度也同样,当时的疲劳程度也必须同样等等。试想,在自然界中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又能有多少呢?再比如,我们就算一只飞白蚁比其它所有个体都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吧,那也总不至于能使之不怕风吹、雨打、蜘蛛与鸟兽吧?再如,我们就算一只小长颈鹿比其它所有个体都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颈子长的更快;那也总不至于一断了奶它的颈子就比它的父兄更长吧?
由此可见,在决定生存与否的所有因素中,有否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央台的《动物世界》里,我们常见大群角马狂奔的镜头;它们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究竟干什么去呢?原来,他们总是把繁殖的时间与区域尽可能的集中,以便于在一定的区域与时间内,它们的幼仔数量能远大于食肉动物的需要量;直到过了这段时间,各种群才带着幸存的已能与它们差不多善跑的幼仔扩散到原地去。在动物界,类似的现象很多,比如鹿、驴、大马哈鱼以及许多鸟类等。
由此可见,动物过量繁殖的意义无非是要增加延续后代的保证系数,而并非像达尔文主义所猜想的那样是竞争。这就好比那些医疗条件越差的地区,计生工作就越难做一样,谁听说哪家生的孩子多是为了要让他们“优胜劣汰”的呢?
“如果因为它们生存了下来,因而比有利变异较少的生物有着更多的后代…”
一眼看去,这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实更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我们常见到同性争偶的现象,这历来都被当作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证据。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远不是所有个体的有利变异同时也是这种竟争的有利因素。比如,有的个体跑得快是有利变异,有的个体耳朵灵是有利变异,有的个体眼睛尖是有利变异,还有的个体善于改变自己的颜色或形体是它的有利变异等等。很显然,这些有利变异都不能保证它们在争偶中取胜,因而也就不能保证它们“有着较多的后代”。
对于雌性来讲就更不用说了,“具有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异”与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显然是两码事。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粗浅的讨论我们至少也可以感觉到:达尔文主义远不象原先所想象的那么周密。
但是,由于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迷信,或习惯性的崇拜,人们不管对进化论究竟了解多少,总愿意相信达尔文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对此有必要再作稍微进一步的探讨。
二,达尔文主义的由来与困境
在自然界,生物适合于环境,环境也适合于生物;越是生态环境少受侵害的地方,生物与环境就越显得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即使我们观察一只小蜘蛛,它的外形、颜色、结构与器官的功能等都无一不与它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大自然美妙无限,以至很早以前许多先哲就被它所吸引,辛勤探索其中的奥密。在《旧约》以前,百家争鸣,许多研究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可惜,后来教会霸权,还是多门科学母体的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旧约》就独霸天下了。它告诉人们:所有物种都是上帝分别、特意地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独创论”;又叫“特创论”。
独创论认为:当初上帝所创造的各物种就是人们现在所见到的形态特征;也就是说,物种是不变的。
大约在十八世纪前后,随着造船工业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人们关于自然界中各种动植物的知识也大大的丰富起来了;还有那些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家养动植物种,几乎每天都在告诉人们:物种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变的。
于是,人们对独创论越趋不满,开始寻找新的答案。
比如康德、还有达尔文的祖父,都在这方面作过不懈的努力。而且,他们也都注意到了: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其生活方式的关系最为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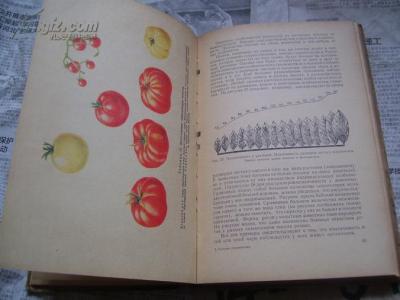
其中最著名的是拉马克,他最先高举进化论的旗帜向独创论冲击(拉马克的观点本源于他的老师_布丰,可惜布丰在旧势力面前没敢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拉马克的进化观叫做“用进废退”。他举例说:长颈鹿的颈子就是因为它的祖先总是要伸长颈子去吃高枝上的树叶。那么,长颈鹿的祖先又为什么总要伸长颈子去吃高枝上的树叶呢?
看起来,这只能是环境所迫了;也就是说,环境条件的改变迫使生物改变它们生存活动的方式;而正是在这个改变了的生存活动方式的长期作用下,生物的形态结构等也必然要随着改变了。
因此,这个观点又叫做“获得性遗传”(后来又被称之为:适应与遗传)。可是,这个观点在当时却遇到了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在当时看来,根据这个原理,似乎所有生物都应该与环境条件完全一致,并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然而事实上远不是所有生物都总是随着环境条件的而改变,而且改变的方向也极不一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康德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堕入了不可知论;拉马克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达尔文很早就读过前人(包括他祖父的)有关进化论的着作,但直到环球考察后才坚信:世界上没有不变的物种;这才完全认清了独创论的荒谬(请注意,还不是神创论),从而坚信进化论。但大量的考察与试验也没有能使他在生物变异的原因方面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他放弃了拉马克的研究方向(达尔文祖父的观点是与拉马克相接近的),比康德更明确的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观(它是由康德最早提出来的;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这个观点的萌芽),认为:变异与进化是两回事,变异的原因很多,使用与不使用只是其中之一,而进化则是具有一定方向的连续不断的变异;而且,对物种进化的理解也不需要穷尽各种变异的原因,因为,各种变异都只是物种进化的前提或基础,这里只要能证明生物总是在“彷徨变异”(达尔文语)就足够了;正是由于自然选择为那些变异规定了方向,物种才进化了;因此,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动因。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来说,确实“再好没有了”(恩格斯语),它使进化论又获得了新生,从而推翻了独创论,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达尔文对生物生存的外部条件的研究。(还须说明一点: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当时,对众多观察事实进行归纳比较,这也还是许多学科研究的主要方法;当时也正是归纳法的鼎盛时期,甚至曾出现荒谬的归纳万能论。因此,在达尔文的研究中也必然要留下这一历史的烙印。)下面就是他在《人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的研究:
一,以一百万以上的美国士兵为调查对象,结果证实:“当成长时居住在西部各洲有使身材增高的倾向”。二,调查还证实了海军生活会延缓成长。例如:“十七、八岁的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身材有巨大差别。”三,根据古尔德先生的调查:“人的身材与气候、土地高度、土壤没有关联,甚至同生活的富裕和贫困也不以任何支配的程度相关联。”
四,“但是,这一结论又同维勒美根据法国不同地方应征士兵身高的统计直接相反…”
于是,达尔文坚信:外部条件的意义只在于“可以引起几乎无限的彷徨变异…”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当年,罗伊舰长本来坚决不同意达尔文参加环球考察。因为他所崇拜的拉法捷尔曾教导说:长着象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是不具备航海所必需的精力和决心的。
再如,达尔文在归纳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自己也认为“神密的”的所谓“生长相关律”:什么蓝眼睛的纯白猫都是,或差不多都是聋子;具有反刍胃的动物同时也一定是偶蹄的动物等等。
现在看来这似乎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连恩格斯早先也曾做出过诸如鸭嘴兽那样的错误推论,这就是证明。
我们再来看看达尔文的实验。
达尔文坚信:所有家养动植物种都与人工选育有关。但是很显然,人们在选育这些物种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改变了它们生存的环境条件。为了比较外部条件的作用与选择在进化过程中的意义,达尔文作了长期的大量的试验。比如:直到现在世界上仍有最早由达尔文选育的,并以他的名子命名的观赏鸽种。正因为这些新鸽种源于其中的普通鸽种在同样的家养条件下仍是原来的形态;而且,该事实又在许多动植物种的选择试验中普遍得到证实。这么一来,达尔文就找到了一根似乎能支撑他的理论体系的擎天柱。
可惜,后人不久就发现:选择只能在生物原有的品性中进行,新品种不过是原品种中某些品性的积累或扩大。然而在自然界,一物种具有一些祖先物种所不具备的品性却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又如何解释呢?
老克利夫兰认为,这个主要弱点在本世纪初由于基因和染色体的发现变得可以理解了。他说:“基因可以发生突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变化,这种变化称为突变…
突变是进化的创造力,自然选择给它们定了方向。⑤”
可惜的是:这仍然经不住自然界的检验。
比如,我们常见的青蛙总是把卵产在水草上,直到蝌蚪变成小青蛙才能离开水;而有一种蛙只把卵产在离水面的植物叶上,等小蝌蚪出来了才掉到水里去;另外,还有一种热带雨蛙,它们一生都不在水里度过,小蝌蚪直到变成小青蛙才从蛙卵里出来。在这里,如果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那自然是由于它们共同祖先的基因发生了“突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变化”,当然也由于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淘汰了第一种蛙,第三种蛙的生存环境也淘汰了第一和第二种蛙。那么反过来说,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往往也并不存在淘汰第三种蛙的因素;而且,第一种蛙的生存环境往往也并不存在淘汰前两种蛙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基因“突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变化”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话,那么,在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里就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有第二和第三种蛙的共生现象;而三种蛙共生也就应该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了。可见,在第二种蛙的生存环境里,青蛙的祖先并没有发生向着第三种蛙演化的所谓“基因突变”,同样,在常见蛙的生存环境里,蛙的祖先也没有发生向着第二、第三种蛙演化的“基因突变”。
再比如,现在有很多物植物新品种,特别是出于杂交与基因工程的新品种,它们的优良品性总免不了要逐代退化,无论人们是多么精心地加以选择也不能扭转它退化的趋势。在这里,基因为什么就不向着人们所需要的方向再继续“突变”呢?由此可见,基因的变化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杂乱无章、“突然”和“随机”的。
早在达尔文生前就有人提出:家养物种人工选择的效果总是随着选择代数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如果这表示人工选择存在着一个极限的话,那么,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代的选择试验,与自然界物种所存在的代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选择试验又怎能证明自然界的进化过程呢?达尔文却认为: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些家养物种在我们以前就存在很久了,而直到现在它们不仍然在变异吗?
总之,对于现代的科学知识来说,达尔文时代的研究方法有许多都有已显得很陈旧落后了,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来要求前人。
实际上,在达尔文以前,人们的选种意识还不同程度地为旧说所抑制,而随着进化论的传播,逐渐成为自觉的行动。特别是选种在最初几代往往效果显着,这就为达尔文赢得了众多信徒。然而多年以后,人工选择的局限越趋明显的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没有被达尔文所重视的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受到人们普遍的注意。今天,选择早不是新品种的主要来源了,杂交与基因工程已遍地开花,这类科学知识也正逐渐进入人们的常识范围。以上现象也早已随处可见,实际上,它们每时每该都在否定着达尔文主义。
三,非达尔文主义进化原理
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适应与遗传’用不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进化原理简述如下:
首先,我们纵观整个动物界,不难发现: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活动的方式;动物的等级越低,其生存活动的方式就越简单、僵化,其内容也越贫乏、单调;各种动物的形态结构和器官的功能等都与它们各自的生存活动方式相吻合;那些生存活动方式又总与它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条件相吻合。另一方面,一般地说,越是原始的物种,它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条件也越原始,或者这个环境条件的变迁史也越简单。实际上,这就已经说明了:环境条件的改变迫使生存于其中的生物改变它们生存活动的方式,而正是在这个改变了的活动方式的长期作用下,动物的形态结构等也必然要随着改变。可是,当年在拉马克等人看来,根据这个原理,各物种的生存活动方式似乎都应该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而这与当时大量的观察、实验就远远不相吻合,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因为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并非没有不在变的物种(达尔文也承认:有些物种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间,仍然是原来的形态);世界上只是没有完全不可变的物种;关键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各物种的稳定性和可塑性也是千差万别的(请注意:各物种的“稳定性”与“可塑性”是一回事,因为稳定性越强,其可塑性自然越差,反之亦然)。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地说,越是古老的物种稳定性越强,而越是年轻的物种可塑性越好。
因此,即使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内,环境条件的演变对某些物种来说,或许还远远不足以威胁到它们原来的生存活动的方式,那么,这些物种就保持原来的生存活动方式不变,当然,它们的种特性也保持不变(这就是达尔文所始终不能明白的,为什么“有些物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间,仍然是原来的形态”的原因);而对另外一些物种来说,或许就大超过了它们变异性的范围,而且当这些物种也不能避开(比如迁徙)时,那么,这些物种就要被淘汰了;只有这样一些物种,环境条件的演变对它们来说,既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它们原来的生存活动方式,却又在它们的变异性的范围之内,而且,它们也不能徊避这个演变着的环境,这时它们才不得不逐渐改变自己原来的生存活动方式,以适应环境。正是在这个改变了的生存活动方式的长期作用下,它们的形态结构等也必然要随着相应的改变了。
这里,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家猫是肉食性动物,显然,我们在肉食的范围内怎么改变它的食物种类,都不会改变家猫的食性;而且,如果一下断绝了肉食,家猫也就会饿死了。不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用在肉食中逐渐增加素食的办法也是可以训练家猫完全以素食为生的(现在就有许多养貂户这样来节省肉食)。当然,一代两代是不足以训练出一个素食“猫”的物种的,但训练的代数越多,这种训练就容易,可见这个趋势不管是多么微弱也总是存在的。当然,这个新物种就不再是猫了。正如专吃竹叶的大熊猫,其祖先不就是杂食性的动物吗?大概没有人怀疑大熊猫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吧?顺便说说,如果说大熊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在家猫生存的一般环境里也并不存在淘汰素食猫的因素,为什么我们就没见过或听说过一只偶而也愿意素食的猫,以至于让自然选择能够发挥作用呢?
再比如,我们要想把热带植物直接移栽到北方,这显然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现在就有许多原产于南方的植物品种,正逐渐的向北方延伸。
相反,原来生长在干旱或者相当贫瘠地区的野生植物,一般都具有一些能适应其生长地的特殊本领(比如根系特别发达,具有针状的叶等等;据说野生马铃薯不但能获取空气中的养份,还具有捕捉昆虫的本领);而一但得到人类的精心照顾,它们原来的特殊本领也就必然要逐代退化了。
实际上,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遗传的基本规律:在整个生物进化过程中,那些在生存活动中作用越大的器官与性能(比如人的大脑和手)进化的越快,而那些在生存活动中负作用越大的器官与性能退化的越快(比如人类远祖的尾骨);有些器官在生存活动中虽然没有什么作用了,但也没有什么负任用,往往也就残留在生物机体中了(比如人的盲肠与动耳肌等)。
另外,有遗传就必有遗传信息,而且这个遗传信息也就有可能在遗传过程中,受到某些外力的直接作用而改变。从前,这个规律完全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起作用,因此就被认为物种会产生了所谓“突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突变”。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遗传变异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因此,现在越是那些野生物种聚集的地方,即使从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处所,也越是被看成了无价的基因宝库。正因为那些野生物种一般都具有一些特殊的本领,诸如特别能耐旱、耐寒、耐瘠薄;特别能抗风、抗盐碱、抗病虫害等等,而且越是古老的物种它们的这些性能也越稳定;而现在的科学家们已能够获取这些野生物种的某些基因,用以创造出他们所需的动植物新品种(比如据报载,现代科学居然还能把动物的基因,比如把鱼的耐寒基因移植到蕃茄上)。
由此可见,基因工程本身并不能创造基因。
最后,局限于个人的学识与研究程度这里还远不足于给整个生物界的进化主动因作一个结论;但至少就动物界来说,这样一个结论应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是基本吻合的:
生存活动才是进化的主动因。
四,讨论的意义
或许有人会说,这两种进化观并没有本质区别,适应与遗传也是自然选择的题中就有之义,因此也没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进化观。的确,连恩格斯也说过:“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任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⑦。”
这是因为在当时,没有自然选择,适应与遗传还不能完全解释全部进化的过程。而且,无论如何,自然选择也必竟是一种进化观,它总比独创论要先进,因此,在反对独创论的意义上说,这两种进化观必竟是同盟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暂且承认‘生存斗争’是个公式”。
不用说,自然界存在生存竞争,但是,有竞争也有依存。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⑦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在达尔文的学说刚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⑧”显然,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原来,当时正处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在经济领域刚刚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正愁不能在理论上也战胜封建领主,达尔文及时地为他们送来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观。一时间,那些在自由竞争中侥幸成功的机会主义者和投机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冒险家们,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聚集在了进化论的旗帜下:适者生存!这就是当时曾风行一时的口号。更有甚者,当时还曾冒出一个所谓“存在即合理”的反动论调,当即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现在,进化论与独创论的斗争早已结束,而彻底清除神创论又是自然选择所不能胜任的了。而且,在许多科学领域,比如考古学与遗传学,历来起指导作用的实际上都是“适应与传”的进化观而不是自然选择观。特别是在人类起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面,它不但没的积极是的意义,而且是极其有害的。比如法西斯主义就是自然选择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典型事例,甚至直到今日,法西斯的幽灵仍在西方的夜空中飘荡;试想,难道我们没有必要彻底清除法西斯的理论基础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