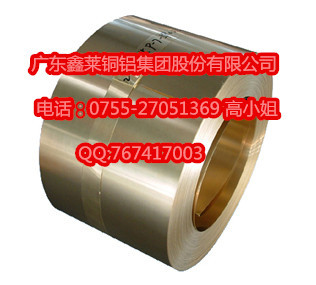每到九月初三的夜晚,一枚精致的檀木书签便在我的脑海中神秘出现,通过它我在泛黄的线状诗集中找到了这两句诗: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正是这句诗将这个充盈着诗意的夜晚,拉向亘古与永恒。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久居庙堂,案牍劳形的白乐天,对官场的尔虞我诈,道貌岸然,愈生厌恶,决定远离权力争斗的中心,自求外任,将牛李党争的喧嚣,像抖落自己身上的尘土一样,鄙弃于历史的污垢之中。

他就这样闯入了九月初三的傍晚,伴随着如钩的残月挂起了一段跨越千年的默契。
我倚栏眺望,他暮江行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因不变的主角――――――那一钩九月初三的新月,把我与他紧紧地绾结在一起。“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当他褪去了党人互相攻讦的惨淡背景,磊落青衫、潇洒赴任之时,便在内心深处重新布置下的屏风,让上面的清风流岚、如钩残月,直对自己的灵魂。我当然没有他那样复杂的经历,但我却读懂了今夜,至少在今夜像他那样体会到一份旷达与闲适,诚如苏子瞻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许今晚便是我,白居易和这钩残月三个“闲人”的相约之时吧。
相较于月亮那样永恒与唯一,露珠是平凡而又短暂的,但我服膺诗人布莱克说过的一句诗:一滴露珠一个世界。它虽小,但透彻,虽转瞬即逝,但会继续凝结。它谨慎地停伫在一片被压弯的小草上,依旧保持着它那卑微而又神秘的颤栗,像人的思想附着于芦苇,用上千年的时间来感应着、摸索着外在于自己的巨大力量。
我像当年香山居士那样俯下身子,透过这滴剔透的露珠来窥望公元822年的世界,想必当年居士也是通过它来窥探未来的世界吧。我们像是处在跷跷板的两端,把彼此都从时空的巨大隔阂与局限中翘起,如庄周梦蝶,列子御风一般失重于天地宇宙之中,面面相觑,惺惺相惜。相比较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自怆然的陈子昂,这种互动使我们的要幸运许多。(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今夜的月曾在千年以前被先贤所仰望,今夜的露珠曾在千年以前被先贤所俯察,使我突然有一种时空被折叠与扭曲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一种超脱吧。
法国17世纪著名的数学家与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的时候,看起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中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傲标志出来。”这一钩残月,一滴白露不就是茫茫宇宙的定点吗?他们像千年以来未曾眨眼的澄澈眸子,一个徜徉于深邃高邈的天空,一个根植于广袤厚重的大地,以超脱静穆的姿态遥望着人间沧海桑田的变迁,而白居易的这首诗恰给这一定点加上了诗意的注脚。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我通过白乐天的诗句来将今夜诠释成我的诗句,他也许亦通过我笔下的文字来感知玄黄巨变的张力吧。2011-9-29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