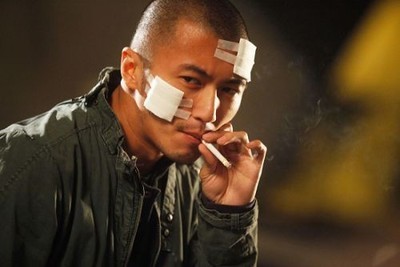马家辉说的小君君是谁?
周轶君
周轶君,女,上海人,70年代出生的正宗处女座,199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随后进入新华社工作。2002年6月,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2005年出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记录她在中东的所见所闻。2006年进入香港凤凰卫视任职至今。曾多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第二届 CCTV“中国记者风云榜”得主。她的《在埃及数骆驼》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论坛实录
4月25日,周轶君作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与网友就各种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我是主持人小力。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
有点特殊,许多媒体都对她赞赏有加,她就是周轶君。今天她带着她的故事,和她新出版的一本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与网友交流。我们知道你也是一个网虫,你是什么时候接触网络的?
周轶君:那很早了,我在2004年写自己的博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主持人:开始的上网环境怎么样?
周轶君:开始用电话线上网,用宽带上网的话,非常昂贵。为了工作嘛,我们必须要保持24小时在线。
主持人:当时你怎么考虑的?
周轶君:我在加沙的工作主要是写新闻了,新闻有一个时效性,新闻背後有更多人性化的故事,可能是没有办法用报道承载的所以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些报道背後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才会想这个。
主持人:当时想过出书吗?
周轶君:当时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写书。后来有一些朋友,出版社他们建议出书。因为新闻会随着时间而淡去,但是他背後的故事他的闪光点是永恒的,所以我要把他记录下来。
主持人:受到了网友的鼓励?
周轶君:我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方式,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与全世界各地的人交流,可以与他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主持人:我们的网友知道你要来我们的直播室,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已经非常踊跃的留言,现在让他们直接的与你交流沟通。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认真的阅读了你写的文章,他很想了解你作为一个女士,在那样的环境下如何工作的?
周轶君:其实我回想起来,有一点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更多的是与当地的人同喜同悲,甚至我会觉得自己过得很麻木。因为自己的情感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女人很不方便,才去的时候,还会掉掉眼泪。但是到后来,时间长了以后,与其变的越来越勇敢,不如说变的越来越麻木。有很多东西,能够让我触动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我能想到自己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女人,在那边可能有很多不方便的事,在我的博客里面可以看得到,因为我在那里必须戴头巾,没有戴头巾,在当地还遭到过围攻。回国头去看,会觉得很有趣,这是文化之间的碰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小趣事,我的办公室楼下就是地中海,但是我从来去畅游过。
主持人:你到了加沙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或者比实际预期想象的情况更困难?
周轶君:我想的不多,我怕到那里会失望。我去的时候,我是先到的以色列。以色列方面,就说他的环境,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好,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小美国。加沙就是一个房子破破的,人也穿的脏脏的,大街上面,车都是在抢道,墙壁上都没有空白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压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共365平方公里,生活了150万人,而四面被封锁,你看到这个,你想到就会觉得很闷,一种绝望,一种沉闷在里面。
主持人:在加沙呆了两年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提前回国呢?
周轶君:那没有。我经历过挫折,也想哭,想放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职业的荣誉感,我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不能放弃。
主持人:那我们再来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说你觉得在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工作,你觉得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周轶君:我感到的最多的是和当地人同喜同悲,你面临同样的恐惧和压抑。我记得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幸福。我当时在那边的街道上,有很多当地的小孩子卖口香糖去赚钱。我有一天停车在马路边上,有一个小孩子让我卖他的糖。我当时在打手机没有搭理他。结果发现他在马路边上哭起来了我马上去问他。他说他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他的父亲失业了,他妈妈常年都有病,兄弟六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在卖糖,在卖报纸。他已经十几岁了,从来没有喝过牛奶,更不要说吃肉什么的。我当时听了挺感动的的,我就把他的糖全买了。后来楼下的警卫都笑话我。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他,我说我可以买你的糖,但是他特别有尊严。他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一下子让我感到肃然起敬。有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会给他买一些奶粉,我说你可以上学。他说家里比较穷,他们那里虽然是义务教育,但是他们要收书本费。过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他,但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告诉我,说他上学去了。那一刻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主持人:你觉得最大的失落在什么时候?
周轶君: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挫折感,在工作当中,会感到很寂寞。最大的失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了。特别是到后期,承受力也强了。
主持人:我们这里有一位网友说你觉得你和闾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周轶君:与其说区别,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共同点还是很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认同职业荣誉感。你要说区别的话,只能是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主持人:也有网友称赞你是铿锵玫瑰,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周轶君:我认为任何标签都是别人添的,别人对我有褒奖,我也很感动。说玫瑰的话,我觉得这个形容太优雅了。
主持人: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呢?
周轶君:我认为只会是一个小菊花。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觉得你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能处理的妥贴吗?你能不能说说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回来以后,会有什么计划?
周轶君:我还没有成家,更多的是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很愧对他们的。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去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去耶路撒冷,那里也很危险,但是相对来说,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跟我妈妈说,我去耶路撒冷。他当时去我机场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去机场的路上,,我记得那天是八月一号,七月三十一日,耶路撒冷一个大学发生爆炸,当时在去机场的路上,就听到了这个新闻。我妈妈一下子听了受不了,不知道该不该让我去那里。我想如果耶路撒冷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说我在加沙。如果加沙出了事,就说我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一直看到我发电的报头,他们才知道我是在加沙。其实我跟他们,我其实也不能总是说好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不跟他们联系。我一般一个礼拜跟他们联系一次。
主持人:那回来以后怎么补偿他们?
周轶君:补偿也说不上,因为我是在北京工作,他们人在上海,隔的也比较远,其实怎么去补偿,这就让我更愧疚了,我连补偿的办法有没有。但是现在联系比较多一些。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特别关心你回来以后的生活,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的人为了金钱,有的人为了荣誉,有的人为了责任而活,他想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他说人不能一直在光环中生活,你离开了光环,你怎么生活?
周轶君: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光环,我去做宣传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我没有什么架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当然不应该有架子,我如果有架子,我怎么去采访呢?我认为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来说,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平常心,能够和采访对象一样的位置上面,你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我有什么光环,所以这方面的失落感几乎是不会有的。
周轶君:我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社,更多的会做一些国际报道。我更多的是想学习一些东西,在加沙这两年,主要是一个输出,现在我想,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笔进补一些。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很难想象一个女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生活了两年,并且出色的完成报道。他知道你获得过很多的奖,他说,你觉得你获得这么多奖,是因为你采访的人物或主题受到关注还是你自己的行为受到关注?
周轶君: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编辑说过,只有好的报道,才能引起别人的重视。就是说当然你这个报道的行为本身,比如说我当时去采访亚辛,当时他是一个黑名单上的人了,我去采访他,这事本身就是受人关注的。但是我报道的内容,我觉得是好的。也只有好的报道,才能长久的被人记住。所以我觉得光有一个噱头,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能给你的读者传递多少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过你的文字,觉得你幽默,机灵,你是如何做到的?
周轶君:我本身是一个挺喜欢开玩笑的。但是在巴以冲突当中,你很难用幽默的语调写一些东西。所以在我的新闻报道里,也不可能笑的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写的书,就有当时写的一些随笔,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很幽默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放松的的幽默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话,你会获得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笑容本身是有力量的,他会去掉一些虚伪的东西,让你用一种正确的心态去关注你所生活的环境。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改变了我对传统上海女人的看法。
周轶君:我觉得大家对上海人的看法可能,可能对这个定义狭隘了一些。上海人有很多种。其实上海人真的有很多种,其实我的性格当中,很多人都说更多的象北方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我是一个南方人,南方的东西还是在我的血液里面。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我更向往去北方,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的文字很有味道,看的出来只有大智慧的女子才能用这样的文字描述如果的经历,你觉得加沙的经历对你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轶君:我很希望变的更智慧一些,大智慧称不上。加沙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一生当中很宝贵的财富。至于说他带给我的影响,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呈现出来。有一些东西我自己感觉他,他会在我体内生长,他会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而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你工作很忙,你是用什么时间来完成这本书的呢?
周轶君:写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习惯。我当时在那边睡眠比较少一点,因为不停的在写东西。我自己平时也会写日记,更多的是在当时的时间的碎片里面去找功夫写这些东西。包括我回来以后,这本书其实是我回来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很长的时间了。
周轶君:我去采访以后,一定会写东西,要保留当时最新鲜的感觉。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现在有很多名人陆续出书,你的书是围绕经历写的,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能不能谈谈?
周轶君:西方写的比我更职业更专业一些。我在加沙的时候,读过一个美国的记者写的书。他们的书里面,我觉得更少的谈到他自己,更多的写到他看到的事。就是他是一个载体,是读者的眼睛,他替读者去看去感受,而不是谈他自己。我记得巴尔扎克说过,一个合格的作家应该更多的描述别人的痛苦,而不是自己的。我在那里是跟当地人感同身受,可能会提到我自己。但是我想,即使是提到,我也是更多的是希望拿我当一个镜子,更多的反映当地人的情况。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如何看待战争当中传媒的作用?
周轶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曾经有人说一个名记者比十万精兵都厉害。特别是在越战当中,大家都认为图片和文字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因为记者不断的从前方发回来报道,看到了美国兵伤亡惨重的事实,才使得在美国本土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去进行反战的活动,才使这场战争提前结束了。其实传媒的作用,我自己感觉不是得心应手的,不是你能够把你想说的能做的事都做完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几乎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我想只能更多的唤起别人的良知,希望能给别人提一个醒,人在战争中会变成麻木的,他会做出很多我们不能理解无理智的事。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提醒,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人是很容易变麻木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作为一个女性去穆斯林国家,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险情?
周轶君:麻烦事很多的。我就说我当时学这个语言的时候,没有想到在那种天气下面,戴头巾是很热的。因为当地的妇女,他们穿袍子,戴头巾什么的,但是他们的活动量是比较小的,一般都是很淑女的样子。不象我戴着头巾还要拍照片,还要奔跑,有的时候流汗就象小溪一样。我有一次镜片被冲跑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跑回来。有一次比较危险的,就是在他们最大的难民营的入口处,发生一起爆炸。我就很着急的赶到那边,但是我忘了戴头巾,穿袍子。我挤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背後有人喊:中国女人中国女人。我想麻烦了,因为那里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我想拍照片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把手伸过来,说你拍这个拍这个。我没有理他,但是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说,你不要碰他。他们两个就先打起来了。旁边就有人说,你要不要站到旁边去躲一躲。但是我看到旁边人群太密了,根本不可能出去。我就跑到车顶去躲一躲,当时那里有摄像师和记者。我爬上去以后,下面的人就去摇车子,想把我们摇下来。当我下去,还没有着地的时候,我的脚就被他们抬起来了。当时无数只手就来抓你,当时我没有办法,只有拳打脚踢。最后是几个人兜了一个圈,把我给抬出来了。那天是非常非常惨的。当时我就跟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能去那里了。但是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去了,第二次又被别人砸一次。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他说你能想象你在自己六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吗?
周轶君:我在加沙的时候甚至会想,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六十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做记者是我最爱做的事,可能我这一辈子还是会做这一行。
主持人:他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战地女记者,是不是勇气最重要?
周轶君:有的时候我也很疑惑。我是不是很勇敢,我不知道。有一次在夜里11点多钟,当地遭遇了爆炸袭击。有一个爆炸的地方离我很近,当时我就坐在地板上面。我也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那一刻我勇敢吗?我不勇敢。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会有一种使命感,如果我不去报道,新华社就没有这个图片和文字,中国的人民也就不能了解发生了什么一些事。所以我觉得敬业精神是很重要的,做报道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在做报道过程中,你们会接触到国外的一些记者,会不会受到他们的观念的影响?
周轶君: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能我们报道的角度有的时候会不一样。但是职业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以职业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是一样的。我和我他们更多的是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他说你书中写了一段此时开口的文字,为什么选此时开口?
周轶君:当时的感觉是很闷的,我虽然还有几个月就要离任了,但那段时期是加沙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加沙是一种人心惶惶的时候,也是两年当中,最危险的时候。当时有人要我写书,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个书。所以我才想到这段文字。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无论如何有一天会走的,但是当地人在那里,是没有一个头,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主持人:我们的周小姐也带来了他在加沙拍来的一些图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拍的图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直接的画面的冲击,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退却吗?
周轶君:当时并不是只有我一个记者。我觉得我们做记者我们很残酷的。我们面对尸体的时候,我们只会想站在如何的角度去拍到最好的画面。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个孩子在我拍摄的过程中,就死去了。当时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在八分钟以后死掉了。我甚至拍到了最后给他盖上白床单的样子。虽然我看到的死亡很多了,但是那个孩子是我亲眼看着他死亡,非常的难忘。后来我多次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的书里就写到过他。你真的会觉得生命太无常了。
主持人:这次你是带着你的新书来到杭州的,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周轶君:今天还没有拿过来。
主持人:我想跟网友说,今天会在枫林晚有一个签字仪式,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与我们周小姐直接的面对面。
周轶君:感谢你们能给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与网友交流,谢谢你们。
主持人:也感谢今天到直播室的网友,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再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