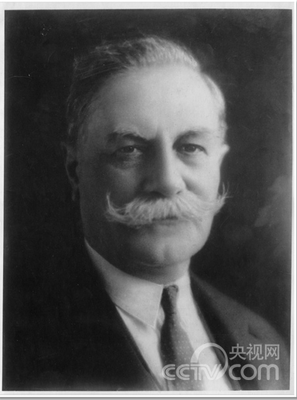(一)
那是两年前一个平静的冬日午后,我的父亲一如往常的躺在床上享受午睡给他带来的片刻安逸。阳光穿过玻璃窗在室内留下一道道倾斜的光柱,仔细看去会发现一些纤细的尘埃在那片温暖中升腾。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这样的午后,坐在墙角看那些在阳光中浮动的尘埃成了我大大的乐趣。
这样的时候,阳光会光临院子里每一个向阳的角落,那些枝柯裸露的高大庭院植物在地上留下恐怖的倒影。我的父亲后来回忆说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对这个午后的所有幻想,继而把他从一个温暖的角落带到了与之相对的另一个世界很深很远的地方。
电话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打来的,同时也把我的伯父,父亲的同胞兄弟出了车祸的消息传达了过来。我无法想象父亲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悲痛,后来他语气轻缓略带沧桑的跟我讲,在那个温暖的午后,他在梦里看到很多陌生人在对他笑。我不知道人是不是会在脆弱的时候失去信仰,然后从生活中寻找认为可以预见未来的任何蛛丝马迹来慰藉自己不堪一击的心灵。
父亲说他和伯母一行人赶到车祸现场时医院的人和警察已经先他们赶到了。事故发生在工业区一处车流稀少的路段,据说是肇事方在急速行驶的情况下突然调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的伯父当场就离世了,那辆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有着响亮车牌号的桑塔纳也几近报废。之后发生的事就像走程序一样不带波澜,医院的急救车呼啸着拉走了已然气绝伯父,例行公事似地实施抢救,然后宣布抢救无效。颤抖着双手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我的伯母在亲人的搀扶下哭喊着看着伯父被推到太平间等待法医的鉴定。
家里的长者把家人分成了三拨,一拨人负责跟交警队和肇事方沟通,其余两拨人分别负责料理医院和家里的事。我的父亲被安排在医院的法医鉴定室守护伯父的亡灵,家里的女人们在家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一定不能让两位老人知道这样的消息。(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最后一次看到伯父是在他离开一天后了。同样是有阳光的中午,当我还在教室的后排跟一道数学题较劲的时候,我的哥哥出现在教室的后门口轻轻地叫了我的名字。他脸上带着些许的疲倦,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整个人看上去并不是很精神,我带着欣喜走出教室问他怎么来了,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请假回家吧,伯父走了。似乎在那一刹那间,我整个人都木然了,像个木桩似地站在光影交错的走廊里,来往的行人似乎都漂浮了起来,像云一样游走浮动,而我就仿佛脱离了这个世界,然后一步步挪动自己的脚步,继而快跑起来……后来在办公室跟班主任复述这一切时我应经哽咽难言。
走出学校,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在寒风中颤抖着点燃,狠狠地吸下去来强作镇定,却依然无法克制自己浑身的颤抖。哥哥过早的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我们沉默着走完一段路,然后一前一后的走上公交车,在后排靠窗的座位,我平静的打量着冬天的小城:一晃而过的行道树、穿着臃肿艳丽棉衣的中年妇女、脸蛋冻得通红,排着队横穿过人行道的小学生……阳光是这一幅幅画面的背景,冷风的浅浅勾勒让岁月慌了神。
公交车在医院前面的广场上停了下来,北方干燥的冬天,阵阵朔风夹杂着地面上的尘埃来来去去,仿佛风都有了形状。我拉紧了衣领,在哥哥的带领下低着头向太平间的方向走去。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太平间。不算宽敞的室内充斥着专属于死亡才有的气息,松香味更添了我对这所有未知的恐怖。我把视线转移到玻璃棺前摆放的伯父的遗照上,是一张全身像,他穿着蓝色的西服,系着领带,脸上满是春风得意的样子。所有的这一切让我觉得心痛,一个人不管生前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地位,这一切在死亡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就是在那一次而我却不曾看到我平生最尊敬的伯父。哥哥缓缓拉开掩在玻璃棺上的毛毯,躺在里面的我的伯父不知在何时被人用一床干净的棉被盖得严严实实的。或许这样也好,在我一生的记忆中,可以永远只记下他志在必得的样子。
(二)
在医院外面的汤馆里,我和哥哥吃着简单的午餐,巨大的悲痛让我们都说不出话来。他拿出手机无所事事翻弄着,我把目光停留在窗外街边的女贞树上,不知何时,这种四季常青的植物站在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边,她们静默站立的姿态常常让我认为是一种等待。相对无言,我们就这么沉默着。
远远地,哥哥看到太平间的门半开着,我们快步走过去――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来了,正弯着腰在香炉前续香。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眯着微红的眼睛示意性的笑了下,然后转身一边随便收拾着什么一边对哥哥说下午给你伯父换衣服(寿衣),你留下来吧。
太平间外面向阳背风的角落里,哥哥说这些天爸爸一直呆在这里,晚上就把暖气打开睡在车里,时不时的还要去给香炉续香……我在想像这样一幅画面:北方寒冷的冬夜里,我的父亲一个人坐在温暖的车里,或许没有开灯,也或许他的指间还夹着一截燃着的香烟,音响里播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凝神去看那疏星点缀的漆黑夜空,他的眼前是一幢幢耸起的高楼,是千家万户亮着的温暖灯火,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此刻,我的父亲应该感到了些许的颓唐,人到中年,林林总总的际遇已然让他变得坚强,抑或是麻木。夜空里有流星坠落,拖着长长的一闪即逝的尾巴,我的父亲知道要给香炉续香了。我问为什么?哥哥说这是规矩,香火不能断。
到了午后,太平间外聚集的亲人越来越多。父亲走过来对我说,你回学校吧,你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我迟疑了一下,很不情愿的对他说不了吧,没事的。我始终不懂得父亲为什么要在那一天要求我离开,那是我第三年读高三了,经历了两次高考失败后,曾经有那么几年,高考就像一个紧箍咒,时时刻刻左右着我的心情。我终于还是没能拗过父亲近乎无情的要求,他说去给你伯父到个别吧!在他的带领下,我再一次走进了那间冰冷的屋子,堂姐伏在棺材上哭得泣不成声,我跪在伯父意气风发的遗照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站在旁边的小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点什么吧。迟疑了片刻,我带些吞吐的说伯父我先走了,你好好的。这样一句永远得不到回应的话在我此后的梦魇中常常被重复,而那一别,却也成了永别,我所有关于伯父的记忆都停留在了那个有阳光却格外寒冷的冬天,定格在他意气风发的遗照上。
(三)
再回到家已是寒假了,同样是个中午,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坐在沙发上,我的归来似乎并没有打断他的沉思。我试着去理解父亲的心情,就像我一直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自己情同手足的哥哥一样,而在那么一段时间里,这种担忧就如同我抬起头时,时时都可以看到的一片云。
去拜访我的另一位伯父是后来的事情了。他在退休后迷上了周易和中医,日日在家鼓捣一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草药,这种怪异的行为常常让人难以接受。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阳光下翻弄晒在竹筐里的东西,我认出那是一味草药,我们那里管它叫翻白草,在我还小的时候他曾拿它治过我流鼻血的毛病。我的出现让他先是一惊,然后他笑着说回来了。我嗯了一声算作是回答。他轻轻的拍了下手,掸掉了粘在手上的灰尘,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以后会有很多,你们长大了,我们就要老去嘛!
我们坐在阳光下聊着天,但聊的更多的还是我刚刚离世的伯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很多地方,但仅限于北方。那一年在延安,他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先生,从不迷信的他在随同的人的鼓动下就算了一卦。那位先生告诉我的伯父不要在牛年的大月出远门,否则……我的伯父只是笑笑,没有当真。随行的一位叔叔付了钱后那位先生给了他一个类似于符的东西,并要他在牛年的时候将此物扔在一条向南的路上。
延安归来后那位叔叔将信将疑的把那个东西交给了我的伯母,并给她作了交代。时间一晃就过了几年,这段小小的插曲渐渐被人遗忘。2009年,牛年;一月,所谓的大月,我的伯父卒于一场车祸。收拾他的遗物时,我的伯母在柜子的角落里看到了那个算命先生给的东西。我怎么那么傻呢,他后来哭着告诉了我的父亲这样一件事,言语中充满了自责。
冬天还在继续,属于那年冬天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结。
(四)
家里人一直没敢让爷爷奶奶知道伯父死亡的事实。事发之后一个寒冷的夜里,在两位老人熟睡了之后,伯父的葬礼就悄悄的举行了。没有送葬的哀乐,没有爆竹,行至人烟稀少的地方时,家里的女人们才敢哭出声来。阵阵朔风穿过原野上的树林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嘶鸣。四野是离离的荒草,黑暗让每一个人都走的缓慢。我的伯母,依然是人群中哭喊的最厉害的一个。
伯父被葬在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家里的人想尽了一切办法去避开爷爷奶奶的耳目。甚至不让我们在二老面前提起伯父这个人。春节渐近,没有看到伯父,最先变得不安的是我的爷爷,他很严肃的问了家人伯父的去向,得到的却是一致的回答――他去了满洲里。我的这个伯父常年在外,但孝顺的他会记得爷爷奶奶的生日以及每一个节日,这样的反常,是爷爷奶奶以前所没经历过的。
春节前的那天,伯父似乎依旧没有要归来的意思,我的爷爷像意识到了什么似地,在天刚亮的时候就敲开了伯父家的门。我的伯母依旧把在门口不让他入内,在经过了一遍遍的盘问之后,我的伯母终于败下阵来,嚎啕着对爷爷说――你那孝顺的儿子带着别的女人跑了,你满意了吧!然后恨恨的甩了门就跑到屋子里哭了起来,留下我的爷爷木然的站在那里。
除夕夜里,满世界都是烟火、爆竹燃放的声音以及人群的欢呼声,我们聚在爷爷家里,他背靠在沙发上,什么也不说,只是偶尔会把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我的伯父和一个女人私奔了,这或许是个很好的借口,至少是个可以隐瞒爷爷奶奶很久的借口。我不知道我的爷爷奶奶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变得沉默了,不敢再面对我刚刚失去丈夫的伯母眼睛,似乎对这个苦命的女人充满了愧疚。
春节过后的一个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醒来后这个世界都成了一片素白。天晴了,阳光照在厚厚的积雪上,白茫茫的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院落,麻雀在枝桠细密的石榴树上跳上跳下,扑簌簌的抖落一片片雪花。几个调皮的孩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大大的透明冰块,在上面打了孔后用绳子穿起来挂在油桐斜出的树枝上。冰块在阳光下闪耀,在风中打转,像一道旋转着的光柱,晃动在我溢满心事的眼睛中。
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了吧,我们保守着我们的秘密等待春天的到来。在那些冗长又恐怖的夜里,听着窗外悬挂的冰柱消融时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我常常幻想那是我的伯父行走在另一个世界的足音。
(五)
正月将尽。
按照家乡的习俗,要给前一年逝去的亲人上坟。我们依然做得小心翼翼,绕行很远,踩着初春刚刚消融的冻土去看望伯父。我似乎不那么容易从悲伤中走出来,随行的堂哥堂弟在这方面俨然做得比我好,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而我更多的是沉默。
翻过一个小土坡,继续前行,在沟谷间的一块平地上的一座新坟前停下。用铁锨给坟墓添土,然后摆好祭品,洒些酒,点上香……我们在冬末春初的阳光下做着这一切,我的伯母趴在那座土堆上哭的涕泪混合,风把纸钱燃尽的灰烬吹得到处都是。不敢回望,我身后对面很近的山坡上是一片陵园,左手边更远的地方是我们家的祖坟。每一天,阳光从这个山岗爬到另一个山岗,然后在更远的山岗后面留下一抹晚霞,遁于无声,像极了我们仓促的一生。
香火燃尽的时候也是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收拾好祭品,把依旧趴在坟旁哭泣的伯母扶起来。转身,抬头,不远处,我的爷爷不知何时站在对面山坡上的一棵树下看着我们,仿佛被人窥见了隐私似地,没有人敢再向前走一步,我们看着他默默的转身。
我的父亲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似地,不顾一切的跑过去,我知道他在担心爷爷。我依旧站在原地,看着对面山坡上那棵突兀生长着的树,忽然想起那些生长在街边的女贞,它们用相同的姿态各自站立在原野上、在街边……
那是种被我叫做等待的姿态,现在它也让我明白:等待本身就像一棵树,伸出双手去捕风,去捉影。
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在等待中站立成一棵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