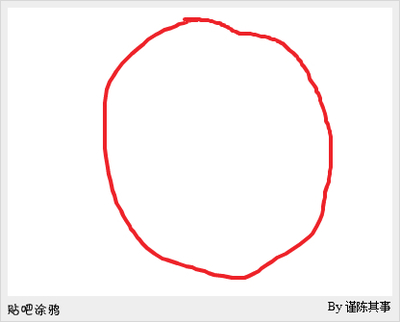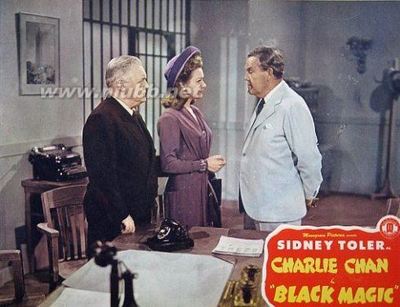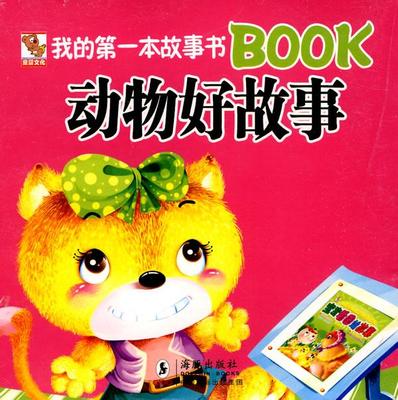《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而写就的短篇小说集, 2006年8月1日由文物出版社发行。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基本资料
![鲁迅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故事新编》[鲁迅作品]-基本资料,《故](http://img.aihuau.com/images/b/09390503/3921030509391425884584.jpg)
《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 、《起死》八篇。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像丰富,是鲁迅作品中仅有的以远古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本书收录了鲁迅的《故事新编》,由陆燕生绘图。陆燕生将古代壁画跨越时空、集故事发展于一体的构思构图手法,运用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绘画创作,此书无疑是关于鲁迅内容的美术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成果。这组作品每幅插图一般都从原著中撷取了三至五个情节,构图层次分明,主宾得当,保持了画面的统一美。但画家又没有平均使用笔力,而是突出了每篇作品的主要情节,比如在《非攻》中突出了墨子跟公输般用木片攻守九回合的场面,在《采薇》中突出了迂腐的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到头来被穿盔甲的士兵推倒在地的狼狈相,在《奔月》中突出了后羿须发飘动开弓射月的雄姿和嫦娥奔月后的无奈,在《起死》中突出了汉子拽庄子道袍、剥巡士裤子的滑稽场面,用事实说明庄子宣扬的无是非观是“放你妈的屁”!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内容简介
《故事新编》
序言
补天
奔月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非攻
起死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创作背景
《故事新编》八篇小说中,有五篇写于1935-1936这个时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鲁迅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处在一个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的境地,然而他的小说风格却如此从容、洒脱、幽默。鲁迅自己对《呐喊》、《彷徨》并不完全满意,大家都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代表作。但鲁迅在一篇文章里公开表示:“我的《狂人日记》写得太逼促,不够从容。”他最满意的小说是《孔乙己》,而《孔乙己》的长处就在于写得非常从容。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标准――从容。但追求从容之美又和前面所说的他的小说内在的紧张,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矛盾。象《故事新编》、《孔乙己》、《在酒楼上》都很好的处理了这种矛盾,而有的小说处理这种矛盾就会露出某种破绽。比如《狂人日记》,“我看来看去,从字里行间看见了‘吃人’两个字”,这样的描写从艺术上讲太逼促了,太急于把自己的看法表白出来,显得不够从容,不够含蓄。反过来看《故事新编》,显然有内在紧张,但表达出来却是如此诙谐、幽默、从容不迫,这种笔调,就能使读者在大笑中感受他内在的紧张。幽默是一个大境界,不仅是文学的大境界,更是人生命的一个大境界。《故事新编》是鲁迅思想和艺术的一次超越,所以小说家的鲁迅以《呐喊》、《彷徨》开始,以《故事新编》作为结束,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故事新编》也是一个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的作品,因为他写得毕竟太匆忙,而且是在大病的情况下写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故事新编》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杰作。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写作特点
封面
小说里讲的故事的主人公,有古代神话里的英雄,比如射日的后羿,造人的女娲,治水的大禹,还有一些古代的圣人、贤人,比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神圣的光圈。鲁迅突发异想:这样一些身上有着神圣光圈的英雄、圣贤,如果有一天走到百姓当中,成了普通人,神变成人,圣人变成常人,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奇怪的遭遇,奇怪的命运呢?他的整本《故事新编》就是围绕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想象展开的。
最能体现鲁迅构思的是《奔月》。这篇小说写的是后羿的故事,但写得很特别。后羿的故事本来是说:天上有十个太阳,老百姓被晒得受不了了,这时后羿出来,把九个太阳射了下来,留着最后一个保证人们的生存发展。对于这样一个英雄,鲁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他当年怎么射日,怎样创造丰功伟绩,而是描写英雄业绩完成以后,后羿有什么遭遇。――“以后”,这才是鲁迅所关注的。鲁迅对很多问题都喜欢追问“以后怎么样”。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在五四时期谈到女子解放,有一个共同的命题,是从易卜生《傀儡之家》那里拿来的,就是“娜拉走出家门”:这是五四很有名的一个命题。大家都这么说,鲁迅却要问:“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他回答说:“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他的思考就是这样彻底而特别,老是追问“以后”。现在同样的,鲁迅也要追问:后羿完成其英雄业绩以后,会怎么样,有什么遭遇。
后羿射下九个太阳之后,同时也把天下的奇禽异兽都射死了,这就出现一个生存问题。尤其是他的夫人嫦娥,是天下的美女,作为一个丈夫拿什么来给这样一个美女夫人吃呢?天下所有的奇禽异兽都被射死了,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所以每天只有请他的夫人吃“乌鸦炸酱面”。这样,夫人就大发脾气了。于是,这天一大早,嫦娥起来就娥眉直竖,对后羿说:“今天你给我什么吃?还是乌鸦炸酱面?那不行,我吃腻了,必须给我找到别的东西,否则不准回家”。这就是所谓“妻管严”,是普通老百姓生活里很常见的事。就象天下所有的丈夫一样,后羿也只得听夫人的话,骑马到了几百里之外。他远远看见一只肥鸡,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有鸡吃,回家就好交待了。他一箭射去,那鸡应声落下。但就在他赶过去想拿鸡的时候,被一个老太婆一把抓住。――这是谁?鸡的主人。
“赔我鸡来!”
“这鸡我已经射死了。”
“那不管,你得赔。”
后羿没办法了,就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她了。
“不行,还不够。”后羿万般无奈只有亮了相,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我是后羿呀!”
“后羿是什么东西?”
人们已经把他给忘了。
他没办法,最后只得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准时来,拿更好的东西给你。”
就这样,后羿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刚走没多远,只见远处一只箭飞过来,后羿“啊”的应声倒地。这箭从哪儿来呢?这是他当年的学生逢蒙射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后羿,人们都把他遗忘了,他的学生也背叛他了。逢蒙看到他倒下去,就赶来想杀害自己的老师。后羿却从地上翻身而起,说:“你小子,幸亏我留了一手!”这一手又是什么呢?――原来,箭飞过来以后,“啊”一声倒地不是真的倒,而是用嘴把箭衔住了。这样逢蒙就很狼狈,逃走了。但后羿到家后,仆人过来报告说:“不好了,先生,夫人跑了!”――嫦娥奔月,到天上去了,连老婆都背弃了自己。后羿就发怒了,说“拿箭来”――他要重新射日,这次是射月亮。这里鲁迅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只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这一段描写是非常精彩的。后羿虽说已经落魄了,但雄姿仍在,可这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因为当所有的奇禽异兽被射死以后,他就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对象,面临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且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整天纠缠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这就导致了他自身精神的平庸化,使他无法摆脱内心的那种无聊和疲倦感。这里写的不仅是一个被遗忘、遭背叛、被遗弃的外在的悲剧,更有一种内心世界的变化所导致的内在生命弱化的悲剧。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是讨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先驱者的命运问题,不只是指后羿,实际也渗透了鲁迅自己的生命体验,五四过去之后,先驱者都面临类似后羿一样的遭遇与命运。
另外还有一篇叫《补天》,是写女娲造人的故事。这篇开头非常漂亮,用笔很华丽,在鲁迅的作品很少见。我们看其中一段,大家要注意他用的色彩。
“粉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目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
我们可以想象:“粉色的天空”……“石绿色的浮云”……“金球般的太阳”……“冷且白的月亮”……,是一副色彩艳丽浓烈的壮阔的场景――女娲就在这种场景下造人、补天。而鲁迅最关心的,是女娲在造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开始时,她精力充沛,兴趣盎然,拿泥捏成一团,扔出去,“哇”的一声,一个人就诞生了。她创造了人,有一种创造者的喜悦。但是不久,她发现,在她胯间出现了一个小人在嘀嘀咕咕告状,说别人的坏话。大概人都喜欢做这种事,尤其是中国人。女娲见到这样的人心里就烦了,想:我怎么造出这样自私的、委琐的人呢?顿时一种无聊感袭上心头,她不想造人了,觉着造人没意思。就不象以前那样用心捏了,而是用树枝蘸着泥水一甩,甩出人模人样的一些东西来。她前边用心捏的都是聪明灵俐的,后面的则都一个个獐头鼠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眉清目秀的人,大概就是女娲用心捏的;那些贼头贼脑的,就是甩出来的。最后她疲倦了,以致累死了。
她刚死,那边就有一彪人马来了,打着一个旗号――女娲之嫡系,在她的肚皮上安营扎寨。为什么在肚皮上呢?因为那里脂肪最多,是最丰腴的地方。这有点滑稽,细细一想,又透出残酷:女娲是人类之母啊,她为创造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却连她的死尸都要利用,还打着“嫡系”即所谓忠实的继承者的旗号。前面我们看到的那段壮阔的场景、绮丽的色彩,到这里就全都消解了。我们就会感到荒诞,而荒诞背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感,这就是《补天》。
还有一篇小说《理水》,写夏禹的故事。夏禹的故事大家很熟悉,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怎么写夏禹:“面目黧黑,衣服破旧”,而且“不穿袜子”,他一坐到椅子上就把两脚伸出来,大脚上长满栗子般的老茧。在鲁迅的笔下,夏禹是一个平民实干家的形象。不仅是他,他的助手也像“铁铸”般地坐着,“不动、不言、不笑”,构成一个黑色的家族。鲁迅作品里就有这么一个“黑色家族”,而且鲁迅自己就是“黑色家族”的成员。许广平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对鲁迅有个一回忆,讲鲁迅先生给她们上课的情景。当时鲁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期待着他的上课。铃声一响,滚过来一团黑,只见鲁迅穿着一身黑衣服,黑浓的头发又粗又硬地直竖着,可不就是“一团黑”。在鲁迅作品中也就有这么“一团黑”:《理水》里的夏禹,我们刚读过的《奔月》里的后羿,下面就要讲的《铸剑》里的“黑色人”,还有《孤独者》里的魏连殳,《野草》里《过客》中的过客等等,都是黑色的人,鲁迅也就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生命感受都渗透到这些黑色的人的形象中。
他写夏禹,也不着重写他怎样创造治水的英雄业绩,仍旧写功成名就“以后”。首先是称呼变了,不再叫“禹”,而是叫“禹爷”――成为“爷”了。大街小巷的老百姓都在传颂禹爷的故事,而且越说越神,越说越玄。说他夜间变成一只熊,用嘴和爪开通了九条河;说他把天兵天将请来,把兴风作怪的妖怪压在山脚下。这样,在老百姓的传说中,禹就被神化了。本来治水对于夏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严肃的事业,现在却变成了老百姓聊天、谈笑的资料,大家只是觉着好玩。这样,大禹的一切努力、奋斗都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变成一个故事了。于是就出现了万头攒动、争相看禹爷的场面,出现了鲁迅最为关注的“看客”现象。鲁迅有一篇小说《示众》就是专门写“看客”的:小说开头写北京的夏天,天气极热,大家都觉得无聊,没什么可干。这时在马路对面,突然有一个巡警牵着一个犯人出现了,这可是一件有刺激性的事,于是,大家就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看犯人。开始是大家看犯人,后来是犯人看大家,再后来是大家互相看。每个人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就形成了“看”与“被看”的模式。这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人间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大家不妨想想,你们和周围的人是不是这种关系。一方面看别人,一方面被别人看。比方说,今天我坐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大家看,同时东张西望地看大家。这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一切都成了表演,成了游戏,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这是内含着一种沉重的,因为就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切真实的不幸与痛苦,一切严肃、认真的努力与奋斗,都被消解了。所以“万人攒动看夏禹”的场面实际是包含着内在悲剧性的,表面是一个喜剧,热闹得不得了,但热闹的背后是一个悲剧,夏禹治水的意义,被遗忘了,价值也消解殆尽了,他成了全民观赏的对象了。
还不止于此,当时的司法部长皋陶还下令全国向夏禹同志学习,否则就要关进监狱。一强制学习,就变成专制了。夏禹实际上就成了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了。而且最后还危及到了自身,他自身也异化了。既然成了“禹爷”,就要有符合“爷”的身份的一套行为方式,必须遵循应有的规矩。比方说,作为一介平民,夏禹平时穿衣服很随便,但现在是“禹爷”,上朝廷就必须穿漂亮的官服,这叫“入乡随俗”。结果呢?他就异化了,也就成了统治阶级里的一员。小说最后一句话鲁迅写得非常轻松:“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果真是“太平盛世”了,禹这样的为民请命的人,现在也不成为威胁了,皆大欢喜了。但就是这“太平”二字掩盖了天下多少不平事,“太平”的背后又有多少血和泪!读到这里,人们不能不感到这轻松背后的沉重,从而引发出无限的感慨。
还有一篇《非攻》,是写墨子的故事。大家知道墨子的老乡公输,他发明一种攻城的机械,献给了楚王,楚王就决定用他的发明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消息后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着楚王的面,和公输般斗智、斗法,一攻一守,最后还是墨子技高一筹,公输般认输,战争也就制止了。这战争是怎么打的呢?不是双方士兵面对面地直接厮杀、打斗,而是双方主帅斗谋略、斗军事武器、技术。这就很有点现代战争的味道,就像美国当年的海湾战争,现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决胜在战场之外。《非攻》写的就是一场现代意味的战争,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制止了这场战争“以后”,他来到了宋国,这个刚被他拯救的国家,他遭遇到了什么呢?他“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为什么?因为他穿得太寒酸,土头土脑的,所以,就被当地警察不放心的搜检了两回。然后“又遇见了募捐救国队”要向他募捐,连破包裹也捐掉了。“到得南关外,又遇着大雨”,想到亭子里避雨,因为他的衣服太破旧也被两个警察拒绝了。一个为民请命的人,到最后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他战胜公输般令人非常敬仰,但现在又让人觉着非常可怜,一下子把前面的庄严感都消解掉了,留给读者的依然是透骨的悲凉感。
所以,我们读鲁迅的《故事新编》,无论是《奔月》、《理水》,还是《非攻》,都会感觉到他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先驱者的命运的问题,一切为民请命者的命运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两种“调子”:崇高的与嘲讽、荒诞的,悲壮的与悲凉的。两种调子互相消长,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而且小说后半部分情节都忽然翻转,把前面的情节颠覆,很像现在所说的先锋派小说和后现代小说。而这样的复杂化的叙述与描写的背后,隐现着鲁迅的怀疑的审视的眼光:他要打破一切人、我制造的神话。
现在我要讲《铸剑》,它是《故事新编》里写的最好、表现最完美的一篇,因此我们要作一个文本细读。
小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有一天楚王的王妃白天摸了一下铁柱子,晚上就生下了一块铁,这自然是块奇铁,楚王就把当时楚国最著名的铸匠莫邪找来,命令他用这块铁铸一把剑。莫邪铸了一把雄剑和一把雌剑,他知道大王善于猜忌又极其残忍,所以就献出雌剑留下了雄剑,交给夫人,嘱咐她将剑埋在地下,待儿子长大,到十六岁时再取出来,让儿子为他报仇。他的儿子果然长大了,叫作“眉间尺”,就是说,双眉之间距离有一尺之宽――当然,古代的一尺没有今天这样宽,但总之是很宽的了,我们可以想见,浓眉大眼宽距离,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小说一开始就是十六年后的子夜时分,母亲向眉间尺追述当年他父亲铸剑的情景,那真是惊心动魄――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
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式的颜色:白的,红的,黑的,“通红”以后的“纯青”。还有鲁迅式的情感:从“极热”到冰一样的“极冷”。鲁迅正是这样外表“极冷”而内心“极热”,这把“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的“剑”,正是鲁迅精神的外化。而在小说里,真正代表了这性格、这精神的,是“黑色人”。
这黑色人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天晚上楚王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拿剑刺杀他,便下令全城搜捕眉间尺。正在最危急的时候出现了“黑色人”。
“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他并不言语,只向眉间尺冷冷地一笑……”。
“眉间尺浑身一颤,中了魔似的,立即跟着他走;后来是飞奔。……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黑色人对他说,“我为你报仇”,“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眉间尺毫不犹豫地割下头,“‘呵呵!’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黑色人确实像冰一样冷酷无情。但当眉间尺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报仇呢?”“黑色人”却这样回答:因为“我的灵魂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就告诉我们,黑色人有一个受了伤的灵魂。我们可以想见,黑色人原来也有火热的心灵、热烈的追求,但他受到一次又一次打击和侮辱,他的心变硬了,排除了一切情感与追求,只剩下一个感情――那就是憎恨,只有一个行为――那就是复仇。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复仇之神。可见黑色人同样外表冰冷而内心火热,他同样是“黑色家族”的一个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即是鲁迅的化身。在小说里,他的名字叫宴之敖,而这恰是鲁迅的笔名。“鲁迅――黑色人――剑”,三者是融为一体的。
我们再看黑色人如何复仇。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玩杂技的人,宣称有绝妙的杂技表演。而楚王此时正觉得无聊,想找刺激,就把他召上宫来。
黑色人要求将一个煮牛的大金鼎摆在殿外,注满水,下面堆了兽炭,点起火来。“那黑色人站在旁边,见炭火一红,便解下包袱,打开,两手捧出孩子的头来,高高举起。那头是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笑容;头发蓬松,正如青烟一阵。黑色人捧着向四面转了一圈,便伸手擎到鼎上,动着嘴唇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随即将手一松,只听得扑通一声,坠入水中去了。水花同时溅起,足有五尺多高,此后是一切平静。”“……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他已经伸起两手向天,眼光向着无物,舞蹈着,忽地发出尖利的声音唱起歌来: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乎呜呼兮呜呼呜呼!
随着歌声,水就从鼎口涌起,上尖下广,像一座小山,但自水尖至鼎底,不住地回旋运动。那头即随水上上下下,转着圈子,一面又滴溜溜地自己翻筋斗,人们还可以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过了些时,突然变了逆水的游泳,打旋子夹着穿梭,激得水花向四面飞溅,满庭洒下一阵热雨来。
……黑色人的歌声才停,那头也就在水中央停住,面向王殿,颜色转成端庄。这样的右余瞬息之久,才慢慢地上下抖动,从抖动加速而为起伏的游泳,但不很快,态度很雍容”。――请注意,这里对眉间尺形象的描写:“秀眉长眼,皓齿红唇”,“颜色端庄”,“态度雍容”,还有那“玩得高兴的笑容”,这样的年轻,如此的秀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生命!但不要忘了,这只是一个头,一个极欲复仇的头颅,这其间的反差极大,造成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头颅“忽然睁大眼睛,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采”,就这么“开口唱起歌来”,依然是听不懂的古怪的歌:
“王泽流兮浩洋洋;
克服怨敌,怨敌克服兮,赫兮强!
…………
堂哉皇哉兮嗳嗳唷,
嗟来归来,嗟来陪来兮青其光!”
唱着唱着头不见了,歌声也没有了。楚王看得正起劲,忙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黑的人就叫楚王下来看,楚王也就果真情不自禁地走下宝座,刚走到鼎口,就看见那小孩对他嫣然一笑,这可把楚王吓了一跳,仿佛似曾相识,因为小孩正像他的发出父亲。“刚在惊疑,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这时,黑色人也有些惊慌,但仍面不改色,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他的头一入水,即刻奔向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这就结束了复仇的故事。
你看,在这一段文字里,鲁迅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把这个复仇的故事写得如此的惊心动魄,又如此的美,可以说是把复仇充分的诗化了。小说写到这里就好像到了一个高潮,应该结束了,如果是一般作家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如果真到此结束,我们就可以说这不是鲁迅的小说。老实说,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描写,尽管很不凡,但别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可以写得出的。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在写完复仇的故事以后,还有新的开掘。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本意,或者说他真正兴趣所在,还不是描写复仇本身,他要追问的是,复仇“以后”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小说写到复仇事业的完成,还只是一个铺垫,小说的真正展开与完成,小说最精彩,最触目惊心之处,是在王头被啄死了以后的描写。
当王死后,侍从赶紧把鼎里的骨头捞出来,从中挑拣出王的头,但三个头已经纠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辨头”的场面――
“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
“到后半夜,还是毫无结果。大家却居然一面打呵欠,一面继续讨论,直到第二次鸡鸣,这才决定了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鲁迅的叙事语调发生了变化,三头相搏的场面充满悲壮感,三头相辨就变成了鲁迅式的嘲讽。也就是说,由“复仇”的悲壮剧变成了“辨头”的闹剧,而且出现了“三头并葬”的复仇结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从国王的角度来说,国王是至尊者,黑色人和眉间尺却是大逆不道的叛贼,尊贵的王头怎么可以和逆贼头放在一起葬呢?对国王而言,这是荒诞不经的。从黑色人、眉间尺的角度说,他们是正义的复仇者,国王是罪恶的元凶,现在复仇者的头和被复仇者的头葬在一起,这本身也是滑稽可笑的。这双重的荒谬,使复仇者和被复仇者同时陷入了尴尬,也使复仇本身的价值变得可疑。先前的崇高感、悲壮感到这里都化成了一笑,却不知道到底该笑谁:国王?眉间尺?还是黑色人?就连我们读者也陷入了困境。
而且这样的尴尬、困境还要继续下去: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全民“大出丧”的场面。老百姓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跑来,天一亮,道路上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名义上是来“瞻仰”王头,其实是来看三头并葬,看热闹。大出丧变成了全民狂欢节。当三头并装在灵车里,在万头攒动中招摇过市时,复仇的悲剧就达到了顶点。眉间尺、黑色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仅余的头颅还和敌人的头颅并置公开展览,成为众人谈笑的资料,这是极端的残酷,也是极端的荒谬。在小说的结尾,鲁迅不动声色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这段话写得很冷静,但我们仔细的体味,就不难发现看与被看的关系。百姓看她们,是把她们当成王后和王妃吗?不是,百姓是把她们当成女人,是在看女人,是男人看女人;她们看百姓,是女人看男人。就这样,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全民族从上到下,都演起戏来了。这个时候,复仇者和被复仇者,连同复仇本身也就同时被遗忘和遗弃。这样,小说就到了头了,前面所写的所有的复仇的神圣、崇高和诗意,都被消解为无,真正是“连血痕也被舔净”。只有“看客”仍然占据着画面:在中国,他们是唯一的、永远的胜利者。
不知大家感觉怎么样,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觉得心里堵得慌。我想鲁迅自己写到这里,他的内心也是不平静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鲁迅的信念,鲁迅是相信复仇、主张复仇的。他曾经说过:“当人受到压迫,为什么不反抗?”鲁迅的可贵,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复仇”主张也产生了怀疑。虽然他主张复仇,但同时又很清楚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复仇是无效的、无用的,甚至是可悲的。鲁迅从来不自欺欺人,他在情感上倾心于复仇,但同时他又很清醒地看到在中国这样的复仇是必然失败的。――这就表现了鲁迅的一种怀疑精神。而且这种怀疑精神是彻底的,因为它不仅怀疑外部世界,更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一些信念,这样他就把怀疑精神贯彻到底了。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在《故事新编》里,鲁迅所要注入的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的现代精神,把他自己非常丰富的痛苦而悲凉的生命体验融化其中。这样一种怀疑精神表现在他的艺术上又是如此的复杂:悲壮的、崇高的和嘲讽的、荒诞的悲凉的两种调子交织在一起,互相质疑、互相补充,又互相撕裂。很多作家的写作是追求和谐的,而鲁迅的作品里找不到和谐,那是撕裂的文本,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就写作结构而言,小说各部分之间,尤其是结尾与前面的描写,常常形成一个颠覆,一个整体的消解。这些都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刻,艺术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这样的小说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是全新的创造。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相关书评
《故事新编》
鲁迅的作品中,《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概是最令评论家为难的一部,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生了关于它是属于什么性质作品(是历史小说,还是讽刺作品)的争论。其实对于《故事新编》的争议远不止于它的归属,令许多读者困惑的问题是:这些小说,到底在写什么?
少年时对《故事新编》最初的阅读经历并不愉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不懂。找一些评论文章来帮助理解,也无非说这些小说是“英雄的颂歌”,表现了“作者的战斗意志”,仍然不得要领。不过,却因此对《故事新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觉得里面隐含着很深的东西。
前些时读到林斤澜谈《故事新编》的随笔,他曾就其中《奔月》一篇的主题当面请教端木蕻良,这位前辈作家说了四个字:“斩尽杀绝”。沿着这条思路再读《奔月》,一种如入“无物之阵”(《野草・这样的战士》)的孤独感出来了,善射的羿射死过“封豕长蛇”,射遍了大小飞禽和远近走兽,最后“射得遍地精光”,不再有生机。这是千古英雄的寂寞,还是天下“独夫”的茫然?而射死母鸡的尴尬、路遇逢蒙的失望和嫦娥无言的离弃,这一切又为这种孤独增添了更多的无奈和嘲讽意味。同样,摆脱“英雄颂歌”的定位重读《铸剑》,也读出一种文学史上罕见的绝望的、悲壮的美。《铸剑》(发表时原名《眉间尺》)取干将铸剑、其子报仇的故事。复仇自然是其主题,但在初出茅庐的刺客“眉间尺”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他仿佛生来就是为了代人复仇,有一种热到极致反显冰冷的性格。眉间尺把复仇的使命连同自己头颅和宝剑一并托付,黑衣人不负所托,劈下国王的头,并砍下自己的头颅,投入到沸水中追咬仇敌,直至三颗头颅都在烹煮中变成了白骨,无法分辨。复仇完成得何等怪诞又是何等惨烈!
于是我知道,对于这些小说内涵的理解需要摆脱思维定式,也需要阅历的支持。但重读《故事新编》获得的还不仅是这些,我以为自己还获得了一种重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角度与方法。当年不喜欢《故事新编》,除了对其主旨难以把握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觉得《故事新编》“不像历史小说”:这些小说缺少“历史感”。 重读《故事新编》时发现,这些小说不仅不同于那些借古讽今的小品,其“随意点染”之中的深意也超越了对现实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深思熟虑。
从阅读层面上看,《故事新编》确是属于那种游戏之作,但游戏不仅需要特别的才气和手段,更需要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在鲁迅的笔下,历史呈现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图景。即使公认的伟大历史人物,在《故事新编》中一概还原到以吃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的凡人,放回到日常生活中,于是真相毕露、妙趣横生;对于所谓英雄、圣贤的事迹,鲁迅也没有采用歌颂的方式编织盛世神话,而是写出这些高尚行为下的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鲁迅超越时代的历史观,更通过他对一系列“正史”狡黠的颠覆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尚书》、《左传》、《史记》这些历史著作并不比《山海经》、《淮南子》之类可信,种种传说、记载莫衷一是,历史的真相总在叙事的彼岸,难以捉摸。
《故事新编》的背后隐藏着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子,当然,这里没有德里达、罗兰・巴特或者海登・怀特。鲁迅用极其机智的叙述、富于穿透力的眼光将这种后现代的困惑织入文本内部。鲁迅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质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各个角落。如果说《呐喊》、《彷徨》以沉重和严肃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冷峻剖析;那么《故事新编》正是以它略带“油滑”的戏说,表现出另外一种深刻。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许可资当今古装影视剧编创人员借鉴――既没有对历史人物顶礼膜拜、编织光环,也不是无厘头的扯淡,而是一种来自深刻把握后的舍形取神――用他的智慧和“通脱”,从古老的传说中变化出来,探求历史深处内在的真实。也许正因为此,鲁迅在编定这部小说集后会不无自得地说:《故事新编》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故事新编_《故事新编》[鲁迅作品]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字豫才,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作品有小说集《呐喊》(1923年),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乡》、《社戏》、《一件小事》、《风波》等14篇作品;《彷徨》(1926年),包括《伤逝》、《祝福》等11篇作品;《故事新编》(1936年),包括《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作品。
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10篇作品。
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包括《秋夜》、《过客》等24篇作品。
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且介亭杂文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