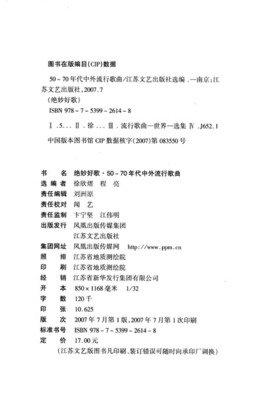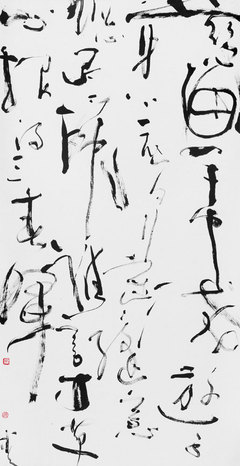从我记事起,妈妈的手上,总带着一枚闪闪发亮的顶针。顶针是用薄薄的铁片做的一个箍,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浅窝,戴在中指上,做针线活的时候帮助针鼻那头顶在浅浅的窝里,不会戳破手指。顶针是每一个农村女人必备的东西,不用时和针头线脑剪刀布头放在一个编制精美的小笸箩里,摆在妈妈的大木箱子上,妈妈一有空就戴上它缝缝补补,那些原本艰难苍白的岁月,在妈妈一针一线精心的编织下,竟也过得有声有色。
记忆中,妈妈做得最多的,就是我们脚上穿的鞋子。那个时候的农村,几乎人人都穿家做的布鞋,可那做鞋的过程,却繁琐而费劲。做鞋子前,妈妈先比对着我们脚的大小,用牛皮纸绞出个鞋样来。我们的脚年年长,妈妈压在炕沿毡底下的鞋样,也就年年放大,还会不时地变着样式,松紧的,方口的,系带的。妈妈是巧手,鞋样绞得又合适又漂亮,村里的大婶大嫂们经常来我们家,让妈妈绞鞋样。农村的女子,基本都会作鞋,可能绞出鞋样来的却没几个,听着她们叽叽喳喳地夸着妈妈,我们的脸上也多了几分自豪。
妈妈做鞋子用的底料,是用家里的破旧衣服上的布片一层层粘起来的,先在桌子上铺一张旧报纸或者牛皮纸,刷上粘稠的面浆,把事先拆洗好的大大小小的布片拼凑好粘在上面,要粘四五层。底料干透了照着鞋样剪出底和帮,鞋底子要用四层合在一起,毛边用白布条裹紧,底部包上白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千层底”,鞋面多用黑色的条绒,女孩的鞋子就漂亮多了,用花布料或者彩色的条绒。粘好了的鞋底鞋帮,一双双摞在一起,上面压两块砖头,码在柜头上,有半米高,看起来白花花的,一派壮观。可这才是鞋子的雏形呢,要把它们一针一线做好,穿在脚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年秋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妈妈就开始给我们做一年的鞋子。纳鞋底用的麻线,是用一种亚麻皮捻成的,捻麻线要用一种特别的工具,我们叫它陀螺子,可不是小孩们玩的陀螺,它是铁制的,上面短粗,下面细长,中间有一个圆圆的铁片,下面细的那头还有一个小钩子。妈妈把一大把束好的麻皮挂在墙壁上,右手拿陀螺,左手拿麻皮,把陀螺靠在大腿外侧,用手在那圆柄上一搓,陀螺飞速地旋转,麻皮就拧成了紧紧的麻线。小时候,看妈妈捻麻线,觉得特好玩,尤其是看到一团乱麻也能在妈妈的手里变成细溜光滑的麻线,更是好奇,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学着妈妈的样子盘腿坐在炕沿上,去转动陀螺的手柄,才发现它压根就不听我使唤,急出一头汗,也不能像妈妈那样捻出一根麻线。
整个冬天,妈妈除了给我们做饭,干家务,其余的时间都在给我们做鞋。鞋帮要沿上黑色的鞋口,白色的底边,针脚要粗细匀称,包条要裹得紧紧的。纳鞋底更是力气活,用长长的锥子先在厚厚的底子上扎个洞,再用穿着麻线的大号针穿过去,拽的紧紧得,一天的功夫,才能纳好一只小孩的鞋底。做好鞋帮和鞋底,把它们上在一起,一双崭新结实的新鞋就完工了。妈妈总喜欢在一双鞋子做好后,把鞋底对在一起“梆梆”地敲,从那清脆的声音里,也听得出妈妈做鞋子的功力。
小孩总爱穿新的,每次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给我做好一双新鞋,我都会迫不及待地从妈妈手里先抢过来,穿在脚上左瞧右瞧,再跑到外面在同伴面前炫耀一番,在大家羡慕的眼神中,连走路都觉得飘飘然。(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冬天冷,妈妈每年都早早给我们做好棉鞋,细心的妈妈还会纳一个棉鞋垫衬在里面,穿在脚上热热和和的,大冷的天也不怕脚冻伤。穿着妈妈做的布鞋,我在那条蜿蜒崎岖的小路上来来回回地跑,上完小学又上中学。
上初中的时候,生活条件已经好多了,有些孩子开始穿买的球鞋或皮鞋,也有女孩穿很讲究的布鞋,和妈妈做的布鞋比,那些从商铺里买的鞋子无异有着炫丽的外表,鞋的主人往往也摆出一副公主般骄傲的姿态,让家庭条件差,买不起鞋子的同学们又妒又羡。
爱慕虚荣是女孩子的天性,十五六岁的我,已经懂得了爱美,看到某个女同学脚上好看的鞋子,曾经在我眼前引以为傲的妈妈做的鞋,却已经黯然失色。我不止一次在妈妈面前念叨,妈妈架不住我的纠缠,在秋天卖完公粮后,带着我和妹妹去了趟城里,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双好看的花布鞋。我迫不及待地扔掉脚上的旧鞋,把新鞋子换上得瑟。可没高兴几天,就发现它压根就是样子货,一点也不禁穿,塑料做的鞋底太薄,走一天路脚心疼,鞋帮子太软,走路老掉,穿着它上体育课跑步,不小心一只鞋就跑掉了,惹得同学们哈哈笑。我回家把新鞋塞到立柜底下,再把旧鞋换上,才知道,还是妈妈做的鞋,最舒服最合脚。
除了给我们做鞋,妈妈还要给我们夏天缝褂子,冬天缝棉衣棉裤,过年时给我们每个孩子缝新衣赏,那时候家里没有缝纫机,所有的针线活都得妈妈一针一线去做。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就没有空闲的时间,尤其是冬天,我经常在半夜里醒来,还能看到妈妈在昏暗的灯光下穿针引线,那根小小的银针在妈妈手上来来回回,清贫的日子里有心灵手巧的妈妈,我们也倍感幸福快乐。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布料都是棉织的,没现在的纤维结实,再加上学校的课桌凳子又破又粗糙,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勤洗勤换,孩子们的衣服裤子一点也不耐穿,屁股上和衣袖上经常露着破洞。妈妈细心,每次看到我们的衣裤刚破个小洞,或露出毛茬子,有欲破的迹象,妈妈就赶紧让我们脱下来缝补。妈妈打补丁的方法和别人不同,大多数同学穿的衣服补丁都露在外面,有些懒惰的妈妈们补衣服甚至不管补丁与衣服的颜色是不是合适,蓝裤子上缝一块绿色的大补丁,又扎眼又难看。妈妈补衣服可就细心多了,她不厌其烦地挑挑拣拣,找一块颜色和衣服相同或者相近的布头,修剪得大小合适,衬到衣服里面,针脚细密,平整,甚至让人看不出衣服缝补过的痕迹。
过春节前,是妈妈最忙碌的日子,全部的被褥都得折洗。妈妈每天起大早,拆掉一床被子,在做早饭前就洗出来,那时候没洗衣机,洗的衣服也无法脱水,只能使劲扭干,趁太阳出来的功夫晾晒。下午,被里被面晒干了,妈妈再赶着缝制,缝被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跪在炕上好几个小时,长长的大针在她的手上灵巧地舞动,我和妹妹一边看电视,一边给妈妈穿针。妈妈做的针线活太多了,眼神已经不好,穿针的时候对着亮光高高举起,眯着眼睛,把线头在嘴里抿一下,捻细,对着针孔穿过去,却常常穿空。每次看到妈妈穿针费劲的样子,我心里就像被那针扎了一样,一下一下地疼,从妈妈手里接过针替她穿好,眼睛总是涩涩的,想哭。
哥哥和我都相继出门打工,妈妈用羊毛絮成厚厚的被褥,缝得又细又密,妈妈说,离家一里,不如屋里,到了外面热了冷了没人关照,凡事都得自己操心,要学会照顾自己。青春年少的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对妈妈一夜不眠重重的叮嘱过耳就忘,还嫌烦,听得多了,甚至顶上一句:“知道啦,罗哩罗嗦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妈妈被我们一呛,目光一下子黯淡了,不再说话,只是细心地给我们打点行李,从被褥到内衣袜子,都用手捋得平平整整,一样一样塞到行李包,看着妈妈失落而不舍的表情,我为自己的无知薄情而后悔,喉头哽咽着,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哥哥是家里的独子,从小被妈妈宠着,脾气却很坏,出门打了几天工,开始怨我们家贫,怨爸爸妈妈没本事,没置下一份像样的家业,他执意要去遥远的外地,说要凭自己的本事去打拼未来。对于哥哥的埋怨,妈妈哑口无言,她精心准备的行李在哥哥眼里,一文不值,临走时用冷漠的目光跟我们道别,背上妈妈用新里新面新棉花缝制的被褥,头也不回就走了,一去好几年,连封家书都很少寄回来。多少个夜里,妈妈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儿子的离家远行让妈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甚至有些寡言少语。我开始恨哥哥的无情,一次次写信,让他有空回家看看爸妈,他偶尔寄来一封短短的信,妈妈让我念了一遍又一遍,那久违了的笑容,在我眼里却像一枚尖刺,扎得我心都在流血。

我进城打工的那个冬天,天气很冷,我和两个小姐妹住在一间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的屋子里,尽管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房子是老板租的,为了省电,禁止我们在床上铺电褥子。每当半夜里被冻醒,爬起来望着漆黑的夜空中那一颗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就想起妈妈温暖的眼睛,想起妈妈在深夜里,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缝补补的样子,耳边也回响声妈妈的话语:“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天冷了多穿件衣裳,吃饱穿暖,睡觉关好门窗,盖严被子,小心感冒着谅。”这样的话,每次回家妈妈都会重复好几遍。我淡淡地应着,心里其实还是有点烦她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