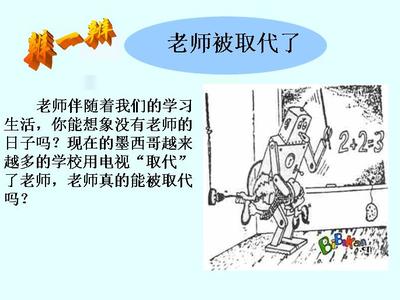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温庭筠
出自晚唐诗人温庭筠的《更漏子》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赏析
这阕词写的是梦醒之后的感觉和追忆;和另一首《更漏子・柳丝长》的手法近似又不似。近似的是都是在最后一句点明是梦。那里“梦长”是明说,而这里“觉来”则是暗示。但都是从梦中醒来的这一点则是无疑的。所不同的是:第一阕没有写梦境,只写梦醒后的苦苦难眠,这一阕却是专写梦境,而把醒时的苦况则轻轻一笔带过。章法极具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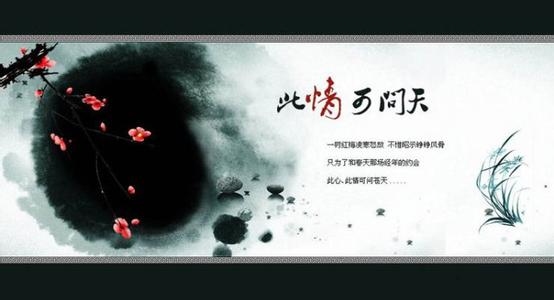
“金雀钗,红粉面”,应当是指梦中于“花里暂时相见”的人;不像是说自己。因为人不好自己夸自己是“红粉面”的。所以他紧接着用醒时的口吻说:“花里暂时相见”。“暂时”是过后的衡量,是追叙的回忆;也是对于梦的一番惆怅。“我们”在花里暂时的、也就是匆匆的又见了一面了。这是自我安慰,因为聊胜于无;但也充满了惆怅,因为毕竟是梦。相见在梦中,而又匆匆地醒了,所以他要突出地点明“暂时”二字,以示惆怅。正因为写的是暂时在花中相见的一段情景,所以“金雀钗,”、“红粉面”当是相见时见到的那人的模样。这种重复梦中的情景,正是在回味,在念念不忘。然而奇怪的是,这梦中的人居然是女子。这点很新奇,也很重要,不亚于在禁锢的思想中,却透漏了一丝缝隙。有的学者认为温庭筠的词写的都是什么商女、黄冠、青楼之情,而此处忽然跑出了一个男性在思念梦中的妇女,匪夷之思。这至少是在那些牢不可破的说法上,找到了一条裂缝;点破了陈说的缺少真知灼见。
上三句写梦中之景,下三句写梦中之情。“知我意,感君怜。”这里分明有一椿冤事在。为什么感“君”的是“怜”呢?怜,是包括爱与哀的意思。唯其爱,是以哀。这两者有连带关系。哀,哀其冤的吧?而爱呢?正因为他人好而被冤,这才所以爱而哀。唯其知道爱而哀,所以他才要说:“知我意”。唯知我意者,斯所以感君怜的。感不在怜而在知。否则,虽怜亦无可感!太史公说过:“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又说:“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她们互为知己的基础,正是你知我意,我感君怜。也许梦中的她问到了他的冤情,他说“此情须问天”者,是此冤情极大,而几乎人间没有,所以这才说要问天的吧?至于这是一个什么冤情?其实温庭筠可以说一生甚至至今都沉在诬罔之中,至于他具体的指的哪件事,这就要论世而知人,找找这词的背景。那么,这又违背了某些人的论点,以为温庭筠的词是没有什么寄托的。其实,有不有具体的事实倒也无所谓,读其情可以。这正是无可申诉之冤久郁于胸中,所以这才有这个梦。这梦正是自己冤之极,而对人思之深的双双结合。读来深有感于为什么人之知己,端在红粉!这很悲,也很美!这就给了这个每多缺陷的人世以悲剧性的色彩而最动人心,否则身居人世,岂非也太没有人味了!
梦醒了,眼前是“香作穗,蜡成泪”,想到梦中那么哀怜地相对,则这香灰、烛泪,还真如两人相对时的样子。一则是自己,如烟穗之灰暗而低垂;一则是她,为之泣血有如红烛之泪。睹物伤情,是人醒了,而情犹在梦中。
正是刚才的梦是那样的美,其情是那么的感人而温暖,是以这才感到醒了,这枕头油腻腻的、冷冰冰的,连锦缎的被子也没有一丝丝暖气!以实来衬起幻之美,而以幻来写实之悲。这样的反差,最具现实的批判性。
这阕词很为前人所称赞:陈廷焯许之以“绝唱”,胡元任不仅整个地肯定了温庭筠,认为他“工于造语,极为奇丽。”更特别欣赏此词,认为:“此词尤佳!”它妙就妙在首先给人一个极美的意境,然后一下让你落于冷寂的现实,造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而在这巨大的落差之间,如瀑布一样的不是空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充满感情的芬芳,溅射出忠贞的奇姿异彩。是以给人以感情上的纯洁化,这在技术上较之从头说起,有着极大的震宕。其实,如果按词的内容来排列,恰好应当调过头来,把末句放在开头。更残、梦醒,一个人睡在冰冷的被子里,想到刚才居然还梦见了她!她还是那样的漂亮,从服饰到颜色,然后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从而想到彼此之间的深情厚意。从深情又感触于眼前的香穗和烛泪,于是想到:也真如我俩一样,看来不死,这情是不会断的!他为了在写法上突破一般化,是很懂得蒙太奇的手法的,一下把主人公最美的情景推到读者的眼前,然后再夹以回叙。通过现实情与物的化入,最后才使人知道;啊,原来竟是一个梦!不由人不升起一缕惋惜之情而对于现实的理解。
由于温庭筠的词几乎是完全诉之于视觉,他只是加以组合,通过这画面的组合变化,使读者去理解他的创伤及思想。因此,这倒很合乎当代的电影语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