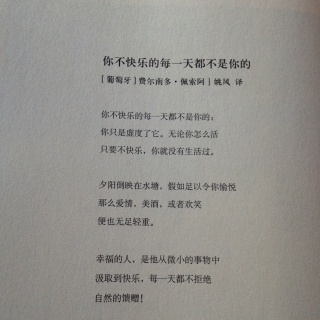包身工,旧社会一种变相的贩卖奴隶的形式。多指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文中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迫害,针对帝国主义这种残暴掠夺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严厉的抨击,它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21世纪称为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又称人才派遣、人才租赁、劳动派遣、劳动力租赁,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由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向派遣劳工给付劳务报酬,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之间,但劳动力给付的事实则发生于派遣劳工与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用工优点:简化管理程序,减少劳动争议,分担风险和责任,降低成本费用,自主灵活用工,规范用工行为。
包身工原文_包身工 -介绍
含义
1、指被贩卖的工人,多是青少年,由包工头骗到工厂、矿山做工,没有人身自由,工钱全归包工头所有,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
2、在包身工形势下做工的人。
著名文学家夏衍先生曾为此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有血有泪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另一本集体创作小说《纱绽怒吼》,也有同类描述。
3、还有网络游戏斗地主中最低级的意思。
历史起源
包身工制度(Peonage)起源于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统治下的拉丁美洲地区和美国内战后的美国南部地区,是美国奴隶制度废除后美国资产阶级建立的一种变相奴隶制度。
英文包身工(Peon)和包身工制度(peonage)衍生自西班牙语,基本意思是指强制劳动力,从事简单劳动的下贱人士,在美国英语中,包身工的历史和法律含义特别指在不自由劳动制度下工作的人士,美国的包身工制度通常是指债务奴工制度(DebtBondage)或契约奴工制度(IndenturedServitude)。包身工制度引发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由此触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但美国利益集团通过黑人管制法典系列(BlackCodesintheUSA),使得包身工制度得以变相延续。
中国包身工制
中国的包身工制度是近代西方资本家引进到中国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西方资本家在上海纷纷创办企业,并建立包身工企业制度。在讲英语的外国企业中,外方管理人员用Peon一词称呼中国工人,往往故意发成(Pee-on),字面意思是在其头上撒尿,引申为下贱人士,有明确的侮辱性。
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纱厂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资本家害怕工人,就企图用包身工来代替成年工,欺侮他们年纪小没有斗争经验。据统计,1937年上海共有包身工达七、八万人之多,占上海纱厂女工三分之一左右。
包身工是由包老板买回来的,这些包老板是流氓地痞,与厂家、工头(拿摩温)及农村恶霸勾结。他们到农村或灾区去诱骗农民,将他们的未成年女儿骗去城中当工。包身工一般只有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期限一般是三年。愈是年龄小的身价愈低,期限也愈长。在包身期间所得的工资全归包老板所有,包老板只供食住。工资比一般工人低40%左右。大多集中在纺织厂工作。
包身工的生活
包身工一入包老板之手,就与世隔绝。包老板怕她们逃跑,不让她们与外界接触,上下班由包老板押送,或由厂中派人来领。包工期间不得回家,甚至连父母亲属也不准来探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二、三十人,还要轮流睡觉。有的是二层架,三层架,人叠人。有的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房内通常只有一支洗脸用的木桶,一支大小便用的马桶。没有洗澡场所,身上又脏又臭。1934年,上海有一位记者报导:“每个铺位铺着一些稻草,稻草上盖一床草席,有的铺草席上堆着一些破棉絮,其余的草席上连破棉絮也没有。问包老板为什么不见被子,包老板说,习惯了,没有被头也会睡觉的。”
包身工的衣服,合约上是包老板供给的。事实上,包老板只供给两套衣服,一单一棉。单衣是用质量最差的布做的,棉衣薄得可以照见阳光。她们是靠家里带来的衣服,补了再补,渡过三年。包老板不给她们鞋袜,包身工要省下饭钱,积起来买些鞋袜穿。
包身工吃的就更令惨不忍睹。包老板给他们两粥一饭,但轮到做夜班时,老板就只给吃两餐粥。下午四点多钟吃了去上班,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才吃到第二顿,午饭就没有吃了。所谓粥实际上是碎米汤,还限制每人两碗。饭是上工前才给吃,有时是发霉的糙米、烂菜汤。
在这种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下,包身工很容易染病。她们几乎没有不是患有烂脚、红眼,和皮肤病等。还有许多人有肺病、胃病、黄疸病、妇女病,经过几年,她们都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在工厂里,她们身上没有标记,但由于他们都是蓬头赤脚,面黄骨瘦,眼睛凹陷,生疮,烂脚,红眼睛,所以一望就知道她们是包身工。
包身工如同奴隶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每清早三、四点钟起床,由包老板押上厂。晚上,在月光之下排队回工房。她们不能转厂,不能转业,不能请假。经年过着没有阳光,没有自由的生活。
工厂内,包身工与其它工人一样,站在车间旁一边工作,一边吃冷饭。大小便没有自由,要领牌子才能进厕所。车间内絮尘飞扬,蒸气如雾,空气污浊。夏天,气温高达华氏120度。工头稍有不如意,她们便要挨打,挨骂,过着非人的生活。
包身工制度的结局
49年后,永安纱厂的包老板回忆说:“包身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为10至12元,每年130元至150元。而每月支出最多6元,每年为72元。每人每年可赚70至80元,最多可达96元。因此,当一个包工头,只要包三、四个人,自己便可生活。”当时的包老板通常包三、四十人,所以每月净收入大大超过工头。
包身工最初的反抗只是逃跑。由于工运的发展,她们得到其它工友的支持,不断与资本家交涉,使她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包老板和工头的方法。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后,日本纱厂停工,包老板把她们送入难民收容所。包身工一和社会接触,她的悲惨遭遇就传开了。这时正值抗日运动高涨,有人对包身工进行了采访,真相公布后,群情激愤,舆严厉指责。上海市社会局立即颁布了八项“处理包身工制工人问题之办法”。以后,纱厂老板再不敢用包身工,这个制度也就此趋于灭亡。
包身工的卖身契

“立自愿书人×××,情由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少女××自愿包与招工员×××名下带到上海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满期,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期限×年×月×日满工,满工后,当报招工员数月。恐后无凭,立此承认。”
作品简介
《包身工》,中国现代作家夏衍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于1935年。
《包身工》一文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叙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的待遇,以及带工老板等人对他们残忍的压榨。
《包身工》文学体裁
《包身工》属于报告文学(同类题材有初中的《地质之光》、《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散文的一类,是文艺通讯、速写、特写的总称,是文学创作中的“轻骑兵”它是一种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品种可以写人,可以写事,也可以写问题因为它是“报告”,就要求所反映的真人真事;又因为它是“文学”,就要求反映出来的真人真事是有典型性的,允许一定的艺术加工
“报告文学”的特点: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
作品背景
作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为了创作这篇报告文学,夏衍亲自深入东洋沙厂采访调查。他得到一位女工的帮助,混进包身工中两三次,但是这经后,他就被工头盯住了。从三月初到五月,夏衍为了看到包身工们上班的情景,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他在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便写成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包身工》。
1929年末,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损失和渡过难关,资本主义各国纷纷加强对外掠夺。日本政府迅速法西斯化,加紧了侵占我国的步伐。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经济的掠夺
随着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我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高涨,上海工人运动十分活跃。为了避免罢工的威胁,日本资本家大量雇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
包身工原文_包身工 -作者简介
概况
夏衍夏衍(1900―1995),中国,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浙江人。因家境贫穷,
夏衍作品
小学毕业后做过染坊店学徒。1914年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明治工业专科学校、九洲帝国大学攻读工科。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1923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7年被驱逐回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左联的工作。抗战期间,任《救亡日报》总编辑。1932年进入电影界。1941年奉命赴香港创办《华商报》。后到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品《包身工》已被选入人教版高一教科书
作品
夏衍一生著译丰富,电影、戏剧、杂感、电影评论、报告文学的写作均有较高造诣。他创作和改编的主要作品有《狂流》《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
包身工原文_包身工 -原文欣赏
包身工的剪影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东洋纱厂的工房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她们是包身工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没钱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包身工人多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代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生活场景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顾正红事件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体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是工价的低廉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就表示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经过红头鬼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
“总得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文明的惩罚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又会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了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头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节礼巴结拿莫温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地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劳动强化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的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包身工原文_包身工 -有关资料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娣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娣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夏衍报告文学漫议(张宝华)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选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3月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