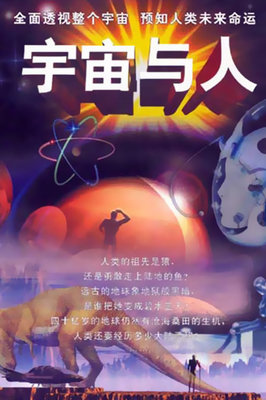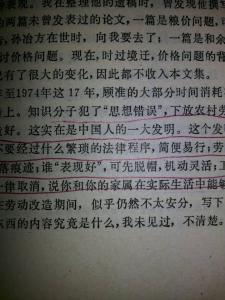
随手从书架上拿起《顾准文集》。竟然无法停止下来。一直到凌晨,天亮。虽然多年前,我就在书市上听人神秘兮兮地说起一个叫做顾准的大右派,他的书很敏感云云。但直到如今,我才真正地读到了他。我并不想夸大顾准的地位,我也没有这样的知识能力和人生阅历去评判他的思想地位。我只能说,我的阅读告诉我,他感动了我。透过历史的烟云,他的文字给我一种来自理想主义覆灭之后的寂静和安宁。
关于他,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说他是那个黑暗年代的一个意外,发出了微弱但却坚毅卓绝的人类良知和理性的声音。他的坚持导致了个人悲剧,却成就了我们民族的一件幸事。因为有他,整个民族和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才不至于沦落到人性和理智丧尽的地步。《顾准日记》忠实地记录了这个个体顽强思索的历程,以及他个人在世命运的悲剧。但这倒不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最触动我心的,仍然是他的言说中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和基于自由主义信念的经验主义立场。
《希腊城邦制度》言必称古希腊,其实时时刻刻不在流溢出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如今学界,真有中国问题意识者又有几何?光顾着采集它山之石,却对脚下的土地视而不见,却对他的人民置若罔闻。在那种极端险恶的条件下,顾准以一己之力从古希腊挖掘民主的根,再反观中西政治传统差异,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民福祉提供镜鉴。且不论他的证据是否全面、确凿,他的结论是否合理、周密,但其研究之最后指向终究还是剖析中国本身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关于他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哲学言说。这种言说之所以如此掷地有声,乃是一个个体在命运沉浮的惊涛骇浪中看清了革命乌托邦虚妄的本质。是残酷无情的历史现实,而不是纯粹的哲学推演,把他引向了彻底经验主义的道路。他发现,左倾激进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运动是彻头彻尾的唯理主义,而这在本质上又不得不是一种神学。这种神学,正是个人崇拜与极权主义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神学乌托邦不得不设定一个高于一切的终极因,从而迫使一切信服于它的事物臣服于它,不惜一切代价,无论这种代价是人伦亲情,还是个体幸福,甚至是生命。顾准看到,他自己的个人悲剧,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乌托邦运动中被一种神圣不可抗拒的意志所写就的。
因此,哲学的思辨和个体命运的疼痛,都迫使他不得不彻底抛弃唯理主义的理想主义叙事,抛弃那个宏大、神圣的唯一性和整体性,坚定地走向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社会立场。恰如他自己宣誓的:“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时至今日,在“民主”的口号响彻各种话语空间,以至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的标签之时,我们有必要重温走向经验主义的顾准对民主的真知灼见。我们一定会发现,在这个话语喧嚣的时代,我们依然没有超越顾准这座巍然挺立的山峰。难以想象,在万马齐喑的1973年,他写道:“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但权威主义必须被打倒”,“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识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他还掷地有声地指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目睹着文化革命史无前例的无政府混乱局面,顾准一定对此心有戚戚焉。只可惜,“ 人民当家作主”依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修辞,成为对“巨大优越性”的论证。其结果,恐怕“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 ”。因此,不要奢望人人当家作主,而是要在制度安排上追求“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权力必须允许被觊觎,这样通过民意的合法性授予来彻底消除政权陷入皇权的可能性。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说在政治上,我们告别了传统,走向了现代。如此观之,时至今日,我们要建设何种模样的民主?是披着民主外衣的皇权,还是真正被授权的民主统治?
斯人已逝。然而其言却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然光华卓绝。顾准的这种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与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相比,或许显得凡俗不堪,锁碎而毫无感情。但在一个乌托邦过剩,而经验匮乏的国度,这个选择才真正显现出他的价值。这是一种无声的感情,也是一种对苍生社稷最大的怜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