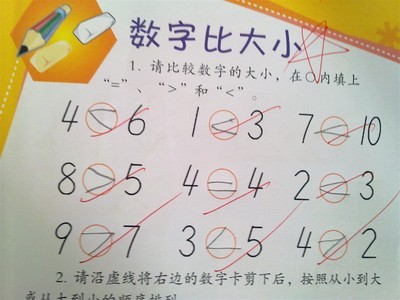大概易士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以后的绰号会被叫作“易拉罐”。
他是我第一个提前认识的同学,可那时候天真的我哪里能想到这个第一次见面就飞奔而来给我一拳的朋友,日后会成为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呢。
在那个科技还没有日新月异的90年代,年轻人的娱乐活动除了等待新片子的盗版碟上市,就是偶尔去夜总会唱个歌跳个舞,后来又出现了迪斯科和溜冰场,但不管怎样,任天堂FC红白机的出现都是具有历史革命意义的。
在那时好像哪个男孩子家里没有一台红白机,那么天哪,你就不要再说自己是个男孩子了好吗,回家去跳橡皮筋吧。
彼时的我还很小,站起来只有餐桌那样高,因此我姆妈不辞辛苦地将差不多高度的桌椅四角都包上柔软的布条,她怕我整日疯跑,磕到脑袋撞成一个傻子。但总之,还没成为傻子的我,也感受到了时代洪流的召唤,连梦里都是超级玛丽的背景音。
尽管因为年龄的关系,我永远只能是吸着鼻涕的旁观者,以及大孩子们背后的人肉背景墙,可这一点也不妨碍我痴迷地看他们打《魂斗罗》《赤色要塞》,在那里紧张地看着那些参与者们摁手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好好好,放大招了,暴击了,KO!
命运的时刻悄然而来。那只是一个平凡的傍晚,已经玩耍了一整天的表哥疲倦地将手柄丢了过来,我难以置信地握着手柄,激动地吸着鼻涕将画面调到《超级玛丽》界面,然后跳跳跳吃蘑菇,变成大玛丽,又跳过乌龟,顶出金币。我是如此高度投入,以至于没注意到表哥家里来了人。
正当我要跳下水管时,一个小男孩旋风一样冲了过来,冲我照脸就是一拳,将还在感冒的我鼻涕眼泪一起打出来。尔后他身手敏捷地夺过手柄,拔出《超级玛丽》的游戏卡插入《魂斗罗》,这番动作一气呵成,一看便是个中老手。
因为忙着打游戏而来不及擤的鼻涕此刻全部糊到了脸上,狼狈不堪之余又觉得备受屈辱,于是我立刻躺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他老妈便骂道:“易士冠,你怎么能打人呢!”
姑妈便在一旁和稀泥道:“哎呀,小孩子嘛,闹着玩的,不要紧的。”
为了平息事端,我爸立刻小跑过来将我拖走,用热毛巾在我脸上胡乱地抹着,将鼻涕糊得满脸都是,因此我便哭得更加起劲了。
尽管我们是同龄人,但那时的易士冠比我要高上一些,而我又打小就是个识时务的俊杰,见他身手这般敏捷,之后几次在表哥家里见了他,立刻一跃而起躲得远远的,决不靠近红白机半步,看着他痛快打游戏的背影在心里默念不久前才习得的台词:“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其实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两年后我上小学时,竟然又在教室里遇到了易士冠。那时他却要比我矮上许多,坐在第一排,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格子衬衫,小短腿晃啊晃,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发型像半个西瓜皮倒扣在他脑袋上。
哎,谁能想到,看起来这样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却是个如此狠辣的角色,他好像早已忘了我是谁,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并未表现出什么惊讶的神情来。我想,大概我只是他揍过的无数小孩中的某一个,也许他学龄前的爱好就是揍别的小孩然后抢他们的游戏机吧。
这样一想,我不禁就释然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相安无事地做了三年同学,彼此之间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易士冠还是没怎么长个子,稳稳地坐在第一排,念书不大灵光的样子经常被老师骂。除此之外,我也没再注意过他别的事情,也许按照这个势头下去,到小学毕业时我便会忘记我们更早之前就认识过这个事实。
这种美好的趋势被一次借作业所打断,念书不大灵光的易士冠不知怎么就来找我借作业抄:“那个……赵曾良,你数学作业写好了是吧,借来抄一下。”
这时候被他揍过的记忆便及时地涌上了心头,我立刻拒绝道:“不借,”并且不怀好意地低头看着他,慢吞吞地念道,“矮冬瓜。”
易士冠冷哼一声,白眼翻到头顶上,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大声说道:“哟,也不知道是谁,小时候被我揍得鬼哭狼嚎,鼻涕眼泪都糊在脸上哦—”
闻言我立刻就坐不住了,口不择言道:“那……那也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了,现在……现在又谁怕谁呢?”
班里的同学们立刻就沸腾起来,大声嚷嚷着“原来你们之前就认识啊”,“到底是谁揍了谁”。大家很快聚拢过来,易士冠这个小个子便得意扬扬、添油加醋地将那件事叙述一番,不要脸地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我简直就是一个贼眉鼠眼、胆小如鼠的瘪三。
要是他平日里写作文能有今日一半精彩,语文老师恐怕都要乐得合不拢嘴了,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原来这家伙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件事情。
而这也着实让我非常焦虑,感觉除非我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揍出屎来,否则无论怎样都难以雪耻。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没过几天易士冠就因为考砸了数学而被老师点名批评。头发已经花白的数学老太太推了推老花镜看着面前这个小个子,痛心疾首道:“易士冠哦,你看看你,脸倒是像个可爱的红苹果,怎么既不长个子又不长脑子呢?我看你哦,是个长僵掉的小苹果。”
易士冠立刻不好意思地举起手里的《金苹果数学练习册》将脸埋在里面,我们便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脸很快就涨红到了耳朵根。
那时候因为要听英语磁带的关系,几乎人手一个复读机,但我们的心思很快就飞到了各种各样的磁带上。在小商品市场里,不论香港的还是台湾的,无论邓丽君还是范晓萱,一律都是五元一盒,我们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一就是交换彼此的磁带。
徐怀钰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我是女生》终于在那几年红到了我们之间,似乎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同名主打歌《我是女生》。
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数学课下课后,一堆人便围着易士冠唱起来:“你不要这样地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劳勃狄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
一看到此等好事,我立刻飞奔过去加入其中,起哄、加油、助威这期间就数我最起劲,我不但跟着唱还引导大家跟我一起喊:“易拉罐,红苹果!易拉罐,红苹果!”
由于我实在是上蹿下跳得太起劲了,上课铃响了还浑然不觉,最终被班主任拎出去罚站。易士冠看着站在走廊上的我,偷摸做着鬼脸。哼,那又如何,反正我的脸可不像红苹果。
我可能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完全忘记了这个红苹果脸的家伙本质上是个多么阴险狡诈的人。易士冠的复仇很快就来了。
中秋节的家庭聚会上,姑妈突然话锋一转,用略带责备的目光看着我,语重心长道:“我前几天可是见到了易士冠啊,我都听他说了,你因为上课唱歌被老师叫出去罚站了。”
“呃……我……”
我爸妈立马震惊地看着我,那神情仿佛之前从来没见过我似的。我连忙解释道:“不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其实不是上课唱歌,而是唱着歌就上课了。”
“易士冠还说了啊,你功课不行,老是被老师点名骂,数学一直考不好。”
“我没有啊……谁老是被骂了,明明是他……”
可刚说到这里,亲戚们便哄笑起来,说我这是狡辩和恼羞成怒,便教诲我说:“现在知道难堪了吧,平时就要好好学习啊,争取考个好中学,不然被易士冠比下去了我们不也没面子。”
原本明明没有恼羞成怒的我,被他们连番教育得果真恼羞成怒起来,哇啦哇啦大喊大叫,最后被我妈揍了一顿才算完。
这下我便更加讨厌易士冠了,觉得他是个阴险又卑鄙的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认真思索揍他一顿的事情。但直到我升上五年级时他已经足足比我矮了一个头,如果我当真去揍他,会显得相当胜之不武,就好比当街揍一个侏儒,算怎么回事呢。同学们一定会嘲笑我的,思来想去最终还是作罢了。
原本事情到这里就该彻底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交集,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小学毕业后各自开始新生活,而我小时候被揍了一脸鼻涕的故事也将蒙上时间的尘埃,从此被尘封成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然而并没有,中学开学第一天又在教室里见到易士冠时,我的心情和见了鬼没什么两样。“啊,真是阴魂不散啊这家伙。”我苦恼地想道。
这一次他并没有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仍旧矮矮的像个长僵掉的小苹果一样坐在第一排,在我从他身边走过时嬉皮笑脸地说道:“哟哟哟,这是谁啊,不是赵曾良嘛……看来我又可以和你姑妈汇报你的……”
“闭嘴!”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再敢多事,信不信我像捏扁一个易拉罐一样捏扁你?”配合着说的话,我伸出右手张开五指又狠狠地旋转着握拳。
“好怕怕哦—”他摆出一副超级贱的表情来,“我要告诉你姑妈你想打我。”
要不是因为开学第一天在新同学面前大吼大叫或是动粗实在是不太好,我真想脱下鞋子扔他脸上,或是将他挂在旗杆上,脖子上套一块板,上书“矮冬瓜”三个字。
可我是个有理智的人,所以我克制住了这一切,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扎了会儿小人。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古惑仔系列的出现,如果不是有了古惑仔这样一个更为真实的江湖,那时候的我们还只能继续假装自己是圣斗士,并且会因班里没有足够漂亮的女生可以让我们假装她是雅典娜而非常失落。
总之随着2000年古惑仔系列的最后一部结束,随着DVD机在家家户户的普及,刚上初中荷尔蒙刚过剩的男孩子们都开始幻想自己能成为陈浩南。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老朋友矮冬瓜易士冠同志,他人矮志气高,想成为史上第一个苹果脸陈浩南。为了更好地cos陈浩南,易士冠找了片木头插在书包里假装那是砍刀,并且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他开始不断地挑衅别人,试图制造气氛打架。
那段时间,他成了一个表演欲望非常旺盛的人,也就是这样,我们发现了一个本来并不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易士冠是个轻微的结巴,每当他激动、紧张或者语速加快时,说话就会有些结巴。
而所有看过《猛龙过江》的人应该都知道陈浩南有个马子,叫作小结巴,她是个结巴……而我们的易士冠同学不但是个结巴还因为苹果脸有些男生女相,于是班里的男生建议他可以角色扮演一下小结巴。
“谁……谁是小结巴……叫……叫我浩南哥,你……你当山鸡!”感觉易士冠快要气疯了。
而班里另一些想当浩南哥的男生则毫不客气地嘲笑他痴人说梦,他们时不时便因这些问题而推搡起来,好几次易士冠都涨红了脸,学着古惑仔里的粗口,边高声叫骂边死死扯住对方的领子,试图营造出一股狠劲来唬住对方。
就这样直到初二,他第一次真的被人揍了。那时候易士冠已经惯常于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小流氓样子。尽管念书仍旧是不大灵光的样子,可也不见他为此担心,总是努力表现出一副看透一切的无所谓的样子来。明明还稚嫩得很,却偏偏要装作自己是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的老油条。
与此同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曹国仁便是大家的老大了。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刚入学时他总说自己是曹操的后人,注定要成为一代枭雄,后来又让大家喊他曹国舅,平日里又表现得像个老娘舅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管。我心里烦得要死,心说,帮帮忙呢,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但曹国仁没有感受到我的心意,之后变本加厉地将手伸得到处都是,不但主动要求帮老师批作业、办班会,还积极充当纠纷仲裁,其中有一次就帮助他手下的一位小弟金雨强抢了我一盒新买的跳棋。
我原本就坐在此君身后,曹国仁因而一度想要收归我为小弟,但那时我别扭性格的雏形已经形成了。至于我的性格究竟如何,简单来说就是,明明自己也很不怎么样,却老是瞧不起别人。
几次面对邀请,我都顾左右而言他地推脱了,这之后曹国仁和金雨之流的班级风云人物便不怎么搭理我了。在初二的结尾,我恰巧也因为总是上课说话而被班主任暂时调到了最后一排,如我所愿地远离了他们。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鼓噪的夏天,我似乎只是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便被我的老同桌李书笑给急急忙地推醒了:“快醒醒,看好戏啊!”
“啊,什么?”大梦初醒,我颇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随即,我立刻被教室中间的巨大争吵声吸引。曹国仁恶狠狠地掐住易士冠的脖子,用挑衅的语气说着:“小结巴还想造反啊?”
说着,他给了一旁加油助威的金雨一个眼神,金雨立刻会意,模仿着《只手遮天》里东升乌鸦枪杀小结巴的那场戏,一边手脚不协调地跳着舞,一边双手比出枪的样子,嘴里发出“biu biu biu—”的声音来。
围观的众人不断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起哄,有时是嘘声,有时是噫声,但没有一个人想要上前去阻止事态变得更严重。
很难说这是因为大家比较怕曹国仁还是因为大家比较讨厌易士冠。
被掐住脖子的易士冠脸涨得血红,双脚乱踢,同时双手死死地扣住曹国仁的手,嘴里挤出最后一丝力气来骂娘,一副发了疯要和他拼命的架势。
但是曹国仁完全不为所动,他粗壮的手臂牢牢掐住易士冠,嘴里还不紧不慢道:“捏扁易拉罐,真是易如反掌。”
“曹国舅,要不还是松开他吧。”金雨这时有些害怕了,开始想要拉开他们。
“哼,结巴还想当老大。”曹国仁边说边松开了手。他甫一松手,易士冠立刻沙哑地号着扑过去,用头顶着曹国仁的胸,双手牢牢抱住他的腰,要把他推倒。
曹国仁也毫不客气双手握拳噼里啪啦地在易士冠背上一阵乱敲,直把他打得跌到地上。我们围上前去,一看,易士冠已被打出了眼泪,哑着嗓子在号哭,嘴里还不服输地骂着娘。
这时班里一位向来以果敢利落著称的女生张佳晨突然过来,出人意料地用跳绳将易士冠给反绑了起来,呵斥道:“你服不服?”
“我不服!”易士冠躺在地上挣扎。
“怎么他们之间也有仇啊?”我转头问李书笑,李书笑说她也不知道。
接着,张佳晨和曹国仁一起将易士冠抬起来搬去了隔壁的杂物间,他们又叫嚷了一会儿。午休结束前,其余人便没事人一样回来了,杂物间也没了声响。
下午上课时,老师奇怪地问道:“易士冠呢?”
众人也不回答,于是便照常上课。
临近放学,大家都开始收拾书包了,张佳晨跑来找我:“听易拉罐说他也揍过你,怎么样,现在他可被绑住了,大家都有仇报仇啊。”
“那也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啊……”能报仇雪恨当然好了,只是易士冠这个家伙太过阴险狡诈,真揍了他,不晓得他要和我姑妈怎样添油加醋地哭诉了。
我离校前去杂物间看了一眼,易士冠还被反绑着,狼狈地躺在地上,眼泪冲开了脸上的灰尘,形成了两道泪沟,看起来活像一个等着被撕票的人质。
看见我来了,他昂着头喊道:“赵曾良,你滚,我不要你来救!”
原本是打算他若求我的话,给他松个绑也不是不可以,没想到他这样嘴硬,于是我扭头就走完全不给他反悔的机会。
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怎样收尾的,也许他们之间还进行了一番骂战,也许第二天所有人都当作没事情发生过一样继续上课。总之,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和别的事情一样,湮灭在中学的时间线上。
很快,我们就毕业了。由于分流的关系,这一次我终于不用再和易士冠做同学了。
偶尔几次从我爸那儿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诸如,易士冠入室偷盗被学校开除啦,易士冠的父母为了他大打出手啦……
只觉他的生活也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学同学聚会上。应当感谢校内网的出现,如果不是在校内网和手机还不太普及的中学时代,相忘于江湖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上了大学,毕业后再也没见过彼此,在饭桌上惊叹着这些年来同学们身上发生的变化,热热闹闹地叙着旧。
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同学,其中有个非常漂亮的瘦高个男生看了我一眼后径直走来在我身边坐下,我们都以为这是谁的男朋友,因此也不好去搭理他。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喂,赵曾良,不打算和我打个招呼吗?”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是?”
“易士冠啊,我们很小就认识了。”
“哎!”我们其余的人一起不由自主地喊起来,“你是易士冠啊?”
当年那个长僵掉的小苹果也不知在哪年哪月,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时节突然苏醒了过来,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疯长,从比我矮了一个头到现在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四肢都被拔得细细长长。当初红苹果一样的脸蛋也完全长开了,成了一张漂亮的脸。
“哟,有女朋友了吗?”当年绑过他的张佳晨凑过来问道。

“哪一个女朋友?”他油腔滑调地回应着。
我们一如当年那样起哄起来。“那你说,你有几个女朋友?”张佳晨举起酒杯问道。
“每去一次酒吧就会有一个女朋友,但我不保证早上起来的时候那还是我的女朋友。”他耸了耸肩,展现得游刃有余。
于是我们只好继续起哄,装作我们也在社会上混过好些年的样子。
没想到金雨也来了,因为迟到了,他一坐下便立刻客气地和我们道歉。他穿着一身笔挺西装,长成了硬朗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当年跟屁虫金雨的模样。
“我去,金雨你也穿得太正式了吧!”易士冠一边打招呼一边递过一根烟去。
金雨摆摆手拒绝了他的烟:“不抽不抽,我现在改名字了,不过大家还是叫我金雨吧。”
“这个事情我知道,金雨是刚从英国回来的,人家现在是海外侨胞不得了了。”张佳晨冲着金雨举了举酒杯。金雨立刻拘谨地站起来端起自己的酒杯:“就是很早就去了英国,现在回来探亲。”
“你什么时候去了英国啊?”我好奇地问道。
“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啊。”金雨整了整西装坐下去。
吃喝到一半,张佳晨突然一拍桌子:“怎么曹国舅不来呢,曹国舅应该最喜欢这种聚会了!”
“是啊,是啊。”我们应和道,“他怎么不来呢?”
此时,一直在笑嘻嘻听我们说话的女生周敏放下筷子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被她这个异常的举动吸引,所有人都看着她。她试探着问道:“你们都不知道曹国仁的事情吗?”
“曹国仁怎么了?”金雨问道。
“曹国仁是我高中同学,他在高二的时候—”说到这里周敏欲言又止起来。
“说呀,曹国舅怎么了?”易士冠不耐烦地催促起来,“大家都是同学,有什么不能说的。”
“高二的时候,他老爸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了,他好像不能承受这些事情,就—就疯了。”
“疯了?”我们惊讶地看着彼此。
“不是不是,疯了是什么意思?”易士冠追问道。
“就是疯了啊,”周敏咽了咽口水继续说道,“先是上课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出怪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后来上课的时候他会突然站起来,张开双手绕着教室跑。”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听见的这些,当初那个霸道、蛮横、热爱做大哥的曹国仁竟会因为不能承受家庭的变故而发疯。
“呃……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我高三的时候还见过一次曹国仁呢。”沉默了一会儿,张佳晨慢吞吞地说道,“那时候,我在教学楼的楼梯口看见一个打扮奇怪的人,染着红色的头发,用发蜡抓成大背头,穿着带铆钉的黑色机车皮夹克。那时候我看了一眼,觉得他特别像曹国仁,可我又觉得曹国仁不可能打扮成这样啊。”
“那应该就是曹国仁吧。”周敏想了一会儿说道,“他高二后期就退学了,他妈妈领着他来退学的。”
余下的时间我们纷纷就此事议论了一会儿,感到一阵奇异的沉重。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重,易士冠站起来鼓动大家拼酒聊天,于是不一会儿,气氛又热闹了起来。
喝酒喝到第三轮,就算是啤酒也有些上头了,我开始觉得自己的反应迟钝起来,于是便站起来和大家道别:“我要走啦,再见啊。”
“再坐一会儿啊,他们待会儿还准备去酒吧续摊呢!”不知是谁挽留了我一下。
“不了,明天还有事呢,趁着还能自己走,我要回家了。”我拒绝了这番好意。刚打算走,突然想起来,怎么说和易士冠也算是老朋友了,得再和他打个招呼吧。于是我找了一下,发现他正在人群中高谈阔论,也许是因为酒的缘故,脸又变得红扑扑的,可是现在啊,不像红苹果了。
“去酒吧你能怎么办,不可能认怂对不对,上次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开口就要点一千块的酒,你说我点不点?那个时候你不点可不行,那就下不来台……”他一手夹着烟,一手举着酒杯,边谈边劝酒,“你喝不喝,我都口渴了,赶紧的!”
我想起了当年那个矮个子,圆圆的脸蛋,又要学着社会上老油条的样子,有时装得流里流气,有时装得阴险狠辣,但总之都不太像。可是现在,现在好多了,也许他已经成了希望成为的人吧。
“再见啦,易士冠。”我远远地喊了一声。
他好像听见了,侧转身子冲我挥了挥手:“再联系啊。”
恍惚间觉得自己似乎刚刚做了一场梦,梦醒来,发现自己还在中学时代的课桌上。
(此文收录在我的新书《岁月如风小少年》中)
购买地址:、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