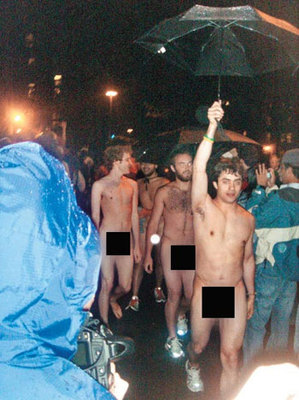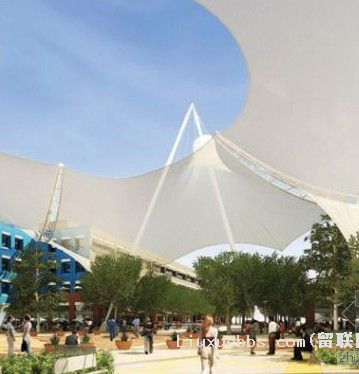1
历史系博士班,通常阅读量是比较大的。比如,以下是我们欧洲中世纪史某一周的阅读:
至少已经700页出头了。这庶几代表了平均水平:大概一本专书(500页左右),加一些文章或章节。一学期上三门课,就是2000页左右。
虽然很多,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读得很快——其实这些书也不可能读很快。
粗略算一下,如果一小时读20页,那一种也只需要100小时,每天13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了。所以,至少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刚转历史的时候在复旦大学听课,我们的老师讲:作为职业的读书人,一天读书八小时是必须的。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而这其实不难做到,如果吃完晚饭,看了一部电影,也就八点钟,“还有四个小时可以看书。”所以,说起来课程紧张一些,其实也就是把看那部电影的时间也用上。大概生活本身就是充满选择和取舍的,选择了和那些作品交流,总有一些其他需要割舍。
2
就我这边课程的阅读而言,我觉得最有帮助的地方在于老师对我们的阅读会有比较细致的指导。通常,在我们开始阅读之前,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在这些读物中,我们可以略过哪些细节,应该追索哪些基本线索。
以上面那一周为例,我们要读Documentary Culture and the La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非常专门的文书学的内容,要追索起来非常不容易。老师就会先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背景。大体是有一个叫Rosamond Mckitterick的教授,她认为我们对早期中世纪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仿佛知识、甚至书写只掌握在教会手中,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法兰克王国的时候,世俗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要用到法律、契约的文书。所以这本书是在这个指导精神下编成的,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擅长的文书,讨论教会之外,书写扮演的角色。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即使能够读拉丁文,那些特定的文书都有自己的研究脉络,这些讨论是我们不可能深入地追索的。无论我们读得再认真,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所以一开始老师就提醒我们这一点,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的功夫。所以,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开始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当这些作者在说世俗而非教会的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一些什么?比如,一个贵族的家族把土地赠与了教会,或者用土地捐建了修道院,那么这些贵族家庭所签署的文书是不是属于世俗文书的范畴?换而言之,对“世俗”的界定是如何影响这些作者的论证的?
这样一来,即使对于初学者而言,就可以比较好地把知识地图建立起来了。

3
概括中心论点是必修课。黄宗智先生在教暑期班的时候就有很详细地指导:
我个人认为,学术专著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注意到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总结的时候,必须要精确,但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
我基础比较差,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这些很困难。用自己的话概括,我觉得像射箭一样,要射中靶心很困难的,一次不中——再尝试一次不一定会更好……也许更偏了……所以我笔记中自己概括的部分会比较少,如果有的话,都会把我的依据都一起抄在上面,以后看的时候可以核对一下。所以Evernote中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本书是Goffart, Walter. Barbarian Tid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蓝色的部分是自己写的,最上面对这本书的很粗略的小结,只是说是我对这本书的总体印象。之后是梳理一下该书的结构。外语书的话就更加重要了,比如Devroey, Jean-Pierre. Puissants et Misérables: Système Social et Monde Paysan dans l’Europe des Francs (VIe-IXe siècles). Bruxelles: Acad. Roy. de Belgique, 2006:
以后回来看的时候,大致知道这书陆续说了些什么事情。以后回来看的时候,大致知道这书陆续说了些什么事情。
但通常我自己写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对摘录的评论为主,比如Wickham, Chris.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大部分时间其实就在码字,感觉效率是低了一些……主要是把阅读中的感受和问题标记一下。我自己的话,长时间的阅读以后,不做比较长的摘录是很难保持状态的。因为有这些摘录、梳理和记录想法的过程,在加上间或总要开个小差,平均一小时20页真的已经是很理想的节奏了。
要之,阅读量大并不意味着阅读速度变得很快——只是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也许开始思考如何系统地管理自己的阅读和笔记。
4
我写得差不多了。
我记起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看电视里下围棋。经常是一个一般性好看的姐姐和嘉宾一起讲解人家的比赛。我就问:“爸爸,爸爸,他们这么厉害,为什么自己不去参加比赛?”我爸就会服一下眼镜,露出深邃的微笑。“因为去参加会输啊,”他说,“围棋这个事情很奇怪的,你出来怎么讲怎么下,自己就要开始连败了。”于是他就给我举出日本围棋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加以佐证,并引申到古今中外炒股票等其他领域……正当我五体投地的时候,他会顿一顿,“这大概是内心有个地方,已经开始骄傲了。”
所以初中的时候我一直谨记满招损谦受益的教诲。但隐约,我似乎又觉得这不是我的做法。我原本就习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也许形诸的文字是面向外面的一个窗口,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是一个请教的过程——是我的贫乏的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一种沟通方式。写这个回答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爸爸是对的,在讲解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和骄傲。但我想,分享的过程也是在面对自己的骄傲。写完了着一些,我想正可以重新开始。
这一年还有许多天的,还有许多书可以看,许多笔记可以记。也期待你的批评意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