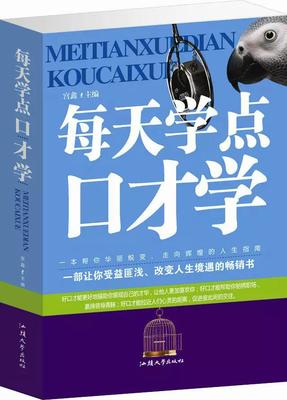张爱玲有句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我父亲自小教导我关于“品味”的重要性,他年轻是极聪明的人,博闻强识,过目不忘,可惜生错了时代。过了玩世不恭年纪,将许多憧憬给了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母亲好艺术,小的时候翻看她的《文心雕龙》,密密麻麻注释,同样的手画过花鸟工笔。嗓子好,被叫“小周旋”,唱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许多热爱被上一辈打压,瞧不起。同样,是生错了年代。
关于品位,他们给我最早的启蒙。
首先是书。
小的时候很着迷父亲在饭桌上信手拈来,家境不算富裕,饭桌搁厨房,很挤的角落,背靠碗橱,大黄顶灯在茶色玻璃上照出一瘦的影。像茶寮里的说书人。说些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侃侃而谈,自诩地理最厉害,其实东南西北分不清,是个全无方向感的人。
我很崇拜,想着读足够多的书大约同他一样厉害。但论及爱买书,我父亲只屈居末流,不及我母亲,更不及我爷爷。我爷爷书法好,这点我记得清楚,其次爱买书。最重要是爱给我买书。
小学里最快乐的日子是每月八号,爷爷买一沓书给我,有一套绘画本中国通史,红砖色,实在很好,后来人事变迁不知搁哪了,一直想把它们找回来。母亲也是,当姑娘时仗着自己工资优渥,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能买都买了,清一色白封皮,边是橙的,也有绿的(印象中是),两三毛一本,文史哲都覆盖了,花钱太多,成了月光。到头来还是最爱那本《文心雕龙》。
倒使我在读书上百无禁忌。爷爷四层书柜最底下放金瓶梅,角落里尤利西斯。父亲的书大多是政史类。我没精读,看哪本名字好抓哪本,翻一翻往下跳,不求甚解。
初中爷爷过世,临走前,给了我几百块钱买书。是我得的最丰厚一笔书钱。
不知道怎么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受益的,对书的品味在所有品味里起提纲挈领之用。事实是,会选书的人,其它品味都不至太差。这里所指品味,又不仅局限音乐,画,舞蹈或艺术。还要更广些(后面会提)。
当然,音乐也重要。
后来上小学,我成为邻里小孩里一起学琴的一个。主要是氛围影响,那时候一个班近三分之一的孩子学乐器。我是钢琴,邻里四五个小孩共聘请一个老师。钢琴属奢侈品,老师一堂课100也是奢侈,录音影像琴谱,且每月到鼓浪屿听一场音乐会。到最后,我也没像母亲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钢琴家。有一次回老家翻看她早年替我买的肖邦夜曲,动也没动,觉得非常惭愧。
上高中,不练琴了,只单纯喜欢听。把省下的钱用来收古典CD,到小贩那淘碟,又是一笔花费。
听不懂很正常,没甚可耻,但总有一些会至流泪。大学去听音乐会,买最便宜的票,现场下来与听碟又是全然不同感受。我是没信心写乐评的,太多人优于我,古典乐评讲求严谨,写了怕人笑。一直只是默默喜欢。今年安德拉斯·希夫来旧金山演出,其中一首是舒伯特奏鸣曲D.960, 论平常,我心中最好的版本属于Wihelm Kempff和Grigory Sokolov,都说希夫音色腻,但第一段落下,就让我掉泪了。是对舒奏的D.960品味变低了?不,不是。
现场,听众,音乐厅中打一束光,黑色钢琴。于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让人动容。这不是版本不版本所能带来的快乐。
我认为的品味,本没有绝对高低之分。所谓高低,只在乎有没有一颗追求品味的心。
比如我父母,在养女儿上十分之舍得花钱,纵如此,也没能将我培养成什么大师艺匠。可又有何妨呢?是美,是好,心向往之。只因这美与好所产生的一点点快乐,就让人觉得生命不是索然无味。又比如有些人,对颜色敏感,音符敏感,以至气味,文字,由此生出情感,情感不断递进,短短长长,背后都与品味休戚相关。当然,喜欢这些也该是光明正大。
是光明正大,不是喧哗。
又比如一个女人说,“我喜欢香水。”这一定是媚俗?也不见得。
悦人之前必先悦己。人与人境遇不同,际遇有别,但无论如何,能在随遇而安中成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一点悦己之心,于我而言,本身就是件品味相当的事。由此又引发许多周边的品格,比如不逢迎的勇气,不刻意边缘或激进,在小事上保持大无畏坚持,逆水行舟,我愿一人前往。这些都是美好。
什么又是美好?
记得两年前学抹茶道,第一次进茶室,七月夏木茏葱,其叶翳翳。两年时间,从浓薄二茶学到中级的唐物,台天目,再到高阶的行之行台子,大円草,许多时候被美得一塌糊涂。这种美说不清,有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奇妙所在。
道和艺又有所不同。
艺是做茶做得美,举手投足间行云流水。是赏心悦目。道是心,自然之心,体察之心。
记得几处细节。有一回问老师,为何茶会上主人穿iromuji(一种全素色的和服)客人随意?老师说,放低自己,让客人的美得以展示。还有一次要在新年茶会上做茶,某个步骤记不清,问老师,老师有些模糊,自己做了一遍,说,“就是这样,只有这样最自然。”
最自然的是最美好的。
同我学茶有一日本老太,今年八十二,喜欢做简单的薄茶与浓茶。见过她做茶的模样,抚触茶具的手不美,刷茶慢,每每跪久便要挪身,步骤也错记。去年夏,她做茶给我,颤颤递茶的手满盛谦敬之心。忽然便想,若我至耄耋,是否会如像她这般久跪茶席,去刷一碗涤人清明的抹茶?后来我接过她递的盏,她窄小的影子照在茶室素壁上,无意间成全我这懒人于茶事上善始与善终之心。
有一部电影叫《寻访千利休》,里面有一段记忆犹新,织田信长接见外国传教士,命千利休为其奉茶。席间,织田信长试问,我是否是定义美之价值之人?利休说,殿下只是定义天下,而天下之美,由我定义。
他说,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
人在追求美好的路上影子越长,心该越低。到斜阳夕照,心该低到泥土里,有点来去赤条条无牵挂的意思。这时便不再求品味不品味了,太表象,麻衣草葬,唯心而已。
由生说到死,又想到张岱《自为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半段说的是品与位。后面说的才是品与味。
真的是这样,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若是短的人生里也无品无味,想来,才是磨难中的磨难吧。
答主的其它回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