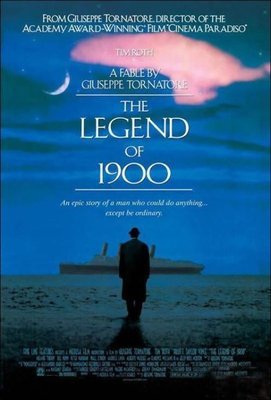因为《海上钢琴师》,是一幕向旧日告别的挽歌。
这一切要从那场精彩无比的斗琴开始说起,当年反复看那一段,心里总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大抵是金庸小说中毒,郭靖和欧阳克在桃花岛那一场比斗,不懂的人看着和懂的人看着,定然不是一个结论。
那么,这三场斗琴,胜负到底是如何的?背后又有什么深意呢?
一时间也想不了然,就搁下了很多年。一直到去年,我看了另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布达佩斯大饭店》。三刷之后,我越来越笃定,这两部电影其实是在说同一件事。
《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主题是什么呢?欧洲文化传统的沉沦。
二十世纪是一个太迅速的时代,伴随着不可逆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到了北美。而接踵而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摧毁了欧洲这块文化昌盛的土地。欧洲传统文人、哲学家或流亡他乡,或抑郁而死。
向那逝去的贵族的、优雅的、繁盛的传统欧洲文明告别,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海上钢琴师》所说的,恰恰也是这个主题。
带着这样一个视野去观察,你会发现有很多以往刻意被忽略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为什么把故事发生的场地,设定在了一艘从欧洲开往美国的船上?美国在这部片子里象征着什么?
正像我所说的,世界的中心,从传统欧洲转向了大洋彼岸的北美,烟雾中的自由女神像,高楼耸立的纽约,那是现代化社会、工业化文明的象征。人们纷纷背弃了伟大欧洲的传统,离开欧洲,漂洋过海,他们对这一切欢欣鼓舞。
而为什么,故事的开端,又设定在了1900年?同样显而易见,二十世纪的主题,就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古老而矜贵的传统文化在这一切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你看,导演的情绪很显而易见,那是这「该死的世纪」的第一年,为什么是该死的?
是的,被抛弃的优雅传统。这也就是为什么钢琴师以弃婴而形式第一次登场了,也正是为什么他被炉工命名为1900。
是的,孩子的父母,奔向了美国,抛下了婴儿,而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节点,正如丹尼说的,我是在这「该死的」新世纪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捡到他的,我要叫他1900。
所以,1900背后真实的隐喻是什么呢?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人么?
不是,他是一个优雅而传奇的神话,是欧洲昔日辉煌的文明、今日被背弃的传统的象征。电影中有一组很短的片段,张伯伦,爱因斯坦,这其中所说的正是这样伟大的传统:
我们在这部片子,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看那衣着或华贵或寒酸的人群,在那驶往美国的船上,簇拥在1900的身旁,深深陶醉,翩翩起舞。这是欧洲悠久传统最后的余晖。
而忽然,有人叫:America!
美国到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奔向那更新的未来去了,只留下1900一人。
其实这部电影说的很明显,只不过我们之前不曾从这个角度想过而已。到这里,我想我已经能解释那场绝世的斗琴了。
1900,对阵爵士乐的发明人,杰利.罗尔。
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杰利.罗尔在历史上是有真人的,但这个人却不是个黑人。
而为什么在电影中,他被改成了一个黑人呢?虽然有政治不正确,但我觉得导演想把白人留给那传统而优雅的欧洲,而用一个黑人来代表美国的新文化,这其中褒贬的意味,太明显不过了。片中的爵士乐发明者,倨傲而粗俗,这一切都与优雅的1900相对应。
这场斗琴,是新文化向旧文化气势汹汹的宣战,而也恰恰如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场比斗的背后,或许也真有其他的深意。我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杰利的出场,极具夸张的威压,屏风上巨大的黑影子,压抑的配乐,人群一霎肃静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他走进来,告诉1900,我想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了,而且拒绝与1900握手。
第一首曲子,杰利弹奏的是《Big Fat Ham》,轻佻动人,而1900托腮,无奈地弹奏了一首简单的《Silent Night》。是谁赢了呢?就现场观众的反映,1900没有认真对待,是杰利赢了。但我们却不曾注意杰利弹奏时的旁白:
杰利.罗尔.莫顿不是在弹奏钢琴,他是在爱抚那些音符。琴声如同丝绸划过女人的胴体,他的手就像蝴蝶,轻盈无比。他是在新奥尔良的红灯区起家,他的弹奏技巧都是在那些妓院学会的。在楼上办事的人可不喜欢被打搅,他们想听到那种掀动帷幔、划过床底,却又不打扰激情的音乐。他的演奏就是这种风格。在那方面,他的确是最出色的。
这段话是导演想告诉我们的,让我想起久远的中国,礼崩乐坏之际,有一个词叫「郑卫之声」,儒家认为其音淫靡,不如宫廷里的雅乐高雅。所以把它贬斥为「淫声」,是可以「乱国、衰德」的。与这里的评价何其相似啊。
而1900的回应,清晰而简洁。《平安夜》是什么音乐呢?宗教颂歌,是高雅的,中正的,与杰利那首媚俗而轻佻的曲子相比,所说的意思很明显,欧洲式的贵族文明对美国新兴工业文明的不屑,无非是些淫词艳曲,不值得回应。你看那1900坐在钢琴前,面上是一副慵懒而毫不在意的表情,还不够说明问题么?
观众哗然了,他们不懂没关系,杰利心里是明白的,他在底蕴和格调上,被耻笑了。
到了第二首曲子,两个人都演奏了《The Crave》。
为什么1900要搞这么一出呢?他首先在听的时候就流眼泪了,觉得这是一首好曲子,难道他是太喜欢了么?不是的,这也是一种观众不懂杰利懂的方式。这首曲子其实是拥有着大量的演奏小技巧的,而1900在听了一遍之后能完整复刻出来。
这是在说,图样,你能弹的我也能弹。新文化无非是脱胎自传统,被传统包括在内。这里的态度依旧是不屑的。
第二城,又失守了,杰利彻底被激怒了,于是就有了第三场惊世的决斗。
杰利弹奏了《The Finger Breaker》,而1900则弹奏了《EnduringMovement》。速度对速度,满场皆惊。
这一场其实最好理解,也最显而易见。关门门前耍大刀,你想要比速度?既然你能弹的我能弹,我还要告诉你,我能弹的你不能弹。
这是欧洲传统文化,对工业文明的绝对自信,360°无死角全方位碾压。

这三场斗琴,其一是自矜,其二是自得,其三是自信。导演对传统欧洲文明最深沉的感情即蕴含在了其中,这么好的东西,可惜就是被人们背弃了,头两场比斗中那嘈杂的观众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漂洋过海,去过工业文明的生活。那贵族式的优雅中正,早被抛弃了。
麦克斯下船的时间,是1933年。几年后,欧洲的战火熊熊燃烧起来,那伟大的文明渐次毁于战争,1900就那么在船上弹奏着,像是一个孤独的幽灵。
这一段,导演不曾演绎出来,原因等同于金庸不写襄阳城破,非不能也,是不忍也。《布达佩斯大饭店》中浓墨重彩的战争因素,在这里简化到了一小段台词当中,但这战争的沉重却绝不是简单。我们再一次看到这艘大船,是战后了。当年风光一时的大船,已经破败不堪,就像是战后衰败的欧洲大陆。
这样具体而显露的象征,其实并不需要多言,一切尽在其中了。
而1900他为什么不下船呢?到这里,我们还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么?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旧秩序旧传统的象征啊,他一生不曾下船,不曾走向大地,这是一个太明显的象征了。
他最后的时间里,对麦克斯说,钢琴上有88个琴键,可以弹奏出无限的音乐,那是诗一样地缅怀那旧日的传统了。他不肯面对那数千条街道的城市,不肯面对那无数的琴键,他说,那样就弹奏不出音乐了。
对旧秩序的坚守,对新生的工业文明的惶恐与不屑,对技术时代的恐慌。
我们不必说1900如何了,我们回到《布达佩斯大饭店》,来看看茨威格最后的几年时光,发生了什么。
1940年经纽约去巴西,时值法西斯势力猖獗,作家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感到绝望。
1942年,完成自传《昨天的世界》,2月22日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茨威格的自杀,或许才是1900拒绝下船最好的注脚。那是一个欧洲文明的遗老,对整个文明的告别。而1900的告别亦是如此。
以上,偶然得之,一家之言,方家见谅。
==========================================
欢迎关注专栏,微信公众号:二十四帧(frames-2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