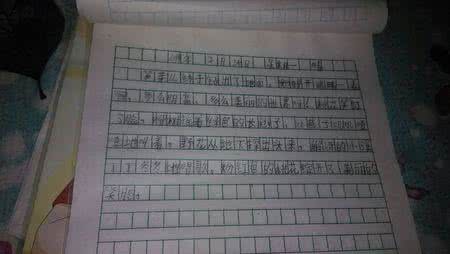《鬼铠》
相比于和平的城镇,这个国家的边境总是战火弥漫,如果缺少牺牲者,那么每个人都将成为牺牲者。
于是就有制度的存在,将军与鬼铠成为守护边境的利刃。魏黎作为将军,镇守边疆近百年,他的鬼铠换了一代又一代。
我并非生来就是鬼铠,在我少有的对人世间的记忆中,寒冷和困窘概括了我短暂的一生。
天大寒,破旧的窗户挡不住风雪,母亲抱着我和弟弟,我的意识在弟弟的嚎啕大哭和母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气中渐渐模糊。她没有发现我正在死去,只是看着窗外的大雪,把满是冻疮的脚压在我的身下。
母亲在等雪停,等父亲回来带一些饱腹的吃食,我也在等,想等天气暖一些去更远处看看。只是这一年的冬天太冷,我没有等到父亲回来。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再一次睁开眼睛,环顾四周,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身穿黑色布衣的男人来来往往,我低头,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穿着。
“这里是?”没有人理会我的问话,他们来来去去,在一阵不算短的沉默之后,我身侧响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嘿嘿,他们不会理你的,他们觉得你就要再死一次了。”说话的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他又继续说“这里是鬼铠营。”
鬼铠军重在一个鬼字,召鬼魂为士兵以此增长战力,士卒生前不得寿终正寝,死后才能发挥全部实力。但在战役中死亡,就会魂飞魄散,永远失去投胎的机会。
死去的人是不能投军的,如果死者的家属将其锁骨取下一块,用红绸包裹送去军营,死者的灵魂就会被封锁在军营之中,家属将领到不菲的抚恤酬劳。我突然觉得喉咙发苦,似乎有冷风穿过,这风里混杂着弟弟的哭声。
“女娃子,我劝你最好早作训练,嘿嘿,这战斗可不会照顾你年幼。”中年男人咧着嘴抛下这样一句话。
“您是?”我问。
“嘿嘿,只不过是个不用训练的饿死鬼罢了,这鬼铠营里谁也没有名字。”就在这男人与我说话的时候,地面突然发出震动,就好像远处有大量巨兽接近军营。一声尖锐的哨声划过,所有黑衣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
“有蛮人突袭。”饿鬼表情一凛,紧接着所有人有序的向门口移动。我茫然的跟在饿鬼身后,看他从队伍的末端穿越到前端。门从外部打开,我再一次见到外面广袤冰原,只是这一次,已经感受不到寒冷。
左右皆是一模一样的军营,大约有二十多座,每一扇门打开后,都由一人带领着数百名鬼卒。我这才意识到,饿鬼是这一个军营的领头,于是伸手拉住他的衣摆。
饿鬼愣了一下,低头看过来,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人几乎要把手松开。但是我知道,就这么上战场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就顶着压迫抬头回看他。我有些腿软,但把嘴倔强的抿成一条缝,来抵抗他。
“蛮人突袭,唯有一战。”冰原不远处威严的声音响起,身上的压力顿时消失,我将恶鬼的衣角抓的更紧些。我看向声音的来源,撞入眼睛的是一个身穿铠甲号令千军的身影。
我知道,眼前那人就是守护帝国边界近百年的将军——魏黎。
魏黎坐在踏炎马上,他正对着鬼铠营的方向,我有些好奇的看他,这个男人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很多。他本应当有一张英俊的面孔,但左侧的脸却被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遮盖住了,让人难以心生好感。
“全军出击。”魏黎用目光缓慢的环视一周后,视线在我的手上停留片刻,然后调转马头,向冰原的断崖骑去。
这个国家能够千百年不被蛮族入侵,原因有二,其一是在于鬼铠军的骁勇善战,其二便是在地势险要。国家与蛮族交界之处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峡谷连接的桥梁是一块足以容下万人的巨石,只要保证蛮族不从巨石上通过,就可以守住边疆。
我跟着饿鬼前进,却见他在峡谷边缘处停下,“怎么不走呢?”我心里纳闷,四处一看,发现之前在军营里的二十余个领头人,和饿鬼一样在峡谷上依次排开。而身后黑衣士卒,空手上阵,一个接一个从我身侧路过,登上巨石。
地面的震感越来越强,我极力向远望,蛮族,来了。
蛮族的人身材魁梧壮硕,从远处看竟像是失控奔跑的群象。我站在饿鬼身后,看峡谷边上的领头人一个接一个,缓慢地将右手抬起。对面峡谷上地刺突起,如同瞬间生长起的竹笋。我睁大眼睛,被眼前不可思议的景象惊呆,对面落雪的速度,比我所在的一边,要慢两倍不止。
然而蛮族还是碾压过来,他们踩着同伴被钉入地刺的尸首,以此作为地毯前行。因地刺而死去的蛮人躺在地面上,有些承受不住同伴的踩踏,腹腔变得稀烂,于是就有新人倒下。同伴的牺牲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就像是失去理智的野兽。
我从未见过如此场面,腿不可控制的发抖,但我尽力控制自己,不想让饿鬼感到衣角的颤动。
蛮人的速度似乎被强行放慢,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他们的推进,当第一个人的脚踏上巨石时,对于我们而言,真正见血的战役才刚刚打响。我难以想象黑衣士卒是如何赤手与这些庞然大物搏斗,但当我心怀疑问的时候,巨石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黑衣士卒的手中七尺长刀凭空凝结,刀柄刀刃皆是雪白,军阵改变。士卒在长刀出现的一瞬间,身形却变得极致轻盈又极致灵活,以至于墨色衣尾都几乎变成一团雾气。
长刀舞起来生风,足以见得沉重非常,但持刀之人却飘逸,“这就是鬼魂之力吗?”我觉得自己平庸弱小。
就在这时,饿鬼的右手也缓慢抬起,掌心朝向巨石的方向,在他手臂伸平的一瞬间,蛮军的动作突然变得迟钝。
“这是我的能力,饥饿。”饿鬼的声音响起。
我这时候有些许恍惚,蛮人虽被减速削弱,仍然力大无穷,仅凭一拳一脚就地动山摇,但黑衣士卒胜在灵活,一柄刀使得出神入化,足以以一当十。战斗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饿鬼已是站立不稳,但他强撑着。
巨石悬空于峡谷之间,蛮人的尸体一地,血液在冰雪中冒着热气,顺着巨石的边缘流下。黑衣士卒死伤并不太多,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象过一只鬼会怎样消亡,但当蛮人的巨掌撕裂他们时,他们就宛如一片雾的消散。
七尺陌刀坠地,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分散成根根白骨,在战斗的混乱中被踩碎。蛮军撤退,黑衣士卒手中的长刀化作灰白色的粉末,又涌入他们的身体中,在粉末涌入之后,他们有变得有了人类的质感。
“回营。”将军的声音响起,这时候我才发现魏黎根本没有登上巨石,他站在所有人的身后,在最安全的地方。“这个将军未免也当得太容易了些。”我小声嘀咕,说这句话的时候,将军正看向饿鬼的方向。
饿鬼看起来像是耗尽了精神,以至于身体变得有一些散,他接话说“嘿嘿,将军英明神武,只需要观战就好。”我心里不服,想要争辩,却在饿鬼警告的眼神下咽了声。
将军骑着马在后走,我们像是被赶着的猪猡一般回了营地。我看着这将军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又想到他之前冷眼看着那么多士卒死去,心里就有百般不满。
当军营的外门关上之后,饿鬼才卸了力气,瘫坐在床榻上,他说“女娃子,不可以乱说话,将军的能力是探查,你就算是哼那么一声,他也能听个一清二楚。”
“他很厉害吗?也会使那个七尺大刀?”我好奇。
“会啊,只是没人见他上过巨石。”饿鬼想了想又说“嘿嘿,不过他是最强,因为他是将军。”
“最强的就是将军吗?那打过他就能变成将军?”我来了兴趣,又问。
饿鬼听了这问话突然坐直身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嘿嘿一笑,又躺下去“没人挑战过他,将军怎么可以被挑战呢?将军是传承。”然后他摆了摆手,示意这个话题过去。
我并不认同饿鬼的话,哪有人生来就是将军的呢,这个军营应该只认实力才对,可是我现在离实力这个词太远太远。
“求您让我变强吧!”我看着饿鬼,一骨碌从他身边爬起来,然后跪在他面前。饿鬼依然躺着,从眼睛的眯缝里看我,他不说话,我就不说话,只是回以眼神。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模样,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娃,但是我的眼睛里,藏着野心。
“嘿嘿。”饿鬼又开始咧着嘴笑,看他的样子,我知道是允了。
饿鬼告诉我了些没有流传出去的事情,鬼铠军营共二十余座,每一座都有其领头人。成为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项自身独特的能力。
一只鬼的能力取决于他的生前的死因,就如死于饥饿的饿鬼,当能力觉醒之后,可以使走进他区域的蛮军饱受饥饿之苦。但这能力并不是人人都有,大多数没有能力的鬼只能去前线厮杀。
若要去前线,自得有一套趁手的刀具,我之前所见的七尺长刀,不可谓不锋利,斩在蛮军身上,可以看见骨骼平整的切痕。这刀就来自于鬼的骨骼,故又名骨刀。
饿鬼见我不理解,就用手搓了搓肚子,坐起身来,他把手掌向上打开,掌心里就起了一层白雾,仔细看竟是骨粉,白雾旋转凝结,化作一柄短小的匕首。“你的身体就是武器,你学这刀法罢,学的越好,活得越久。”
饿鬼示意我试试,我迟疑的展开手,一丝一缕的白气从我手心升起,我感觉身体轻了些,这种空虚感让我惊慌。饿鬼看着我的神色,我抑制住心里的微妙的恐惧,让骨粉出来的多些,更多些。
慢慢的,一层白雾显现出来,越变越厚重,这时候身体里有声音强烈的警告我住手,停下来,但是我用尽全力去抵抗它,饿鬼脸上出现讶异的神情,我全部注意都放在手心,周围的人变的多起来,他们窃窃私语。
那时候,我年仅十二岁,坐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间,第一次凝结出自己的骨刀。后来饿鬼告诉我,那一次超出了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第一次就抽出自己这么多骨粉,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在第一次就凝结出骨刀。这心劲,即使没有能力,也可谓大才。
当一柄锋利的小刀出现在我掌心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刀沉甸甸的重量,但与此同时,身体轻的就好像要飘起来,这种失去重量的恐惧让我发抖,几乎坚持不了片刻,手中的骨刀就碎裂开来,四散成粉末,涌入我的身体。
它们回到身体之后,那种心脏悬空的不适感终于消失,我几乎瘫倒在地,只能一个劲的喘着粗气。我看到周围人怀着异样的眼神四散,也看到饿鬼脸上的复杂,突然想笑,于是我就笑起来,尽力用一种很少女有很轻松的语气问“我还合格吗?”
“不可估量。”饿鬼抛下这样一句话,转过身去,他似乎陷入了回忆里。
后来的一段时间,蛮人像是被挫伤了锐气,没有再次进攻。我的骨刀从一柄短小的匕首,慢慢变成一把锋利的腰刀。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蛮人的体格在上一次战役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我适应了环境之后,时间就似乎陷入了停滞,冰川和白雪足以概括生活的全部,日复一日的练刀,我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会变得很强,变的不再会惧怕蛮人,可是变到最强以后呢?太遥远了,我想不清楚,但是我想做将军。
我的骨刀最终也不能到达七尺,年幼死去让我的身体停止生长,以至于骨粉也要少些,但我不甘心弱于任何人,我回想饿鬼之前说过的话。
我记得自己死前的样子,风雪寒冷,母亲叹气。也记得知道自己的锁骨被母亲掏出后的感觉,那时候我已经感受不到外界的风雪了,但是心里却在发抖。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寒冷。
这些天,饿鬼一直看我站在冰原上,骨刀发出破风的响声,他给我说天资如此,练到这里已经不易,别把自己逼得太狠。与饿鬼共同生活的时日,他越来越像是一个长辈。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我不相信能力是上天对少数人的馈赠,我不信命,也不信天,只觉得所要就要得到。
我终于可以自如使这一柄长刀,可以在恐惧与力量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一个与往常相似的一天中,刀柄上竟附上了薄薄一层冰花。看到这层冰花的时候,我激动的难以自持,这能力意味着新领头人的诞生,只要给我一段时间。
但后来一段时间,无论我怎样费尽力气,冰花仍只能薄薄覆盖刀刃,如同鸡肋。我未曾告诉饿鬼,只觉得这点冰花像是笑话一般。
很快,我不得不告诉饿鬼,因为与蛮人的第二次战争,打响了。
集合的时候,饿鬼依然走在前列,我已经度过了新人的保护期,需要上阵杀敌。但能力未到先起风,结局只能是折翼。
我此刻身上有无限可能,出什么问题太过可惜,就对饿鬼耳语“饿鬼叔叔,我有了能力,但未能熟练掌握,可否这次不上前线。”
饿鬼一愣,他有些惊讶问“这可不行,缩在后面永远也不能成长,不过你是什么能力?”
“冰霜。”这个词自然在我脑中形成,脱口而出。话音未落,饿鬼就好似浑身一个激灵,他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你说什么?”
我心里惴惴不安,又重复了一遍,饿鬼用一种审视和抉择的表情看了我很久,才开口说“那你这一次还是站在我身后。”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但这和冰霜的能力有必然的联系。
军营门打开的时候,魏黎依然站在不远处,这一次,他视线直对着我,然后又盯着饿鬼,脸上有一种刻意针对的神情。“那个女孩,不能躲在后面。”他的声音让所有鬼铠营的鬼都看向饿鬼的方向,我手足无措。
饿鬼把我往身后藏藏,他声音里带着疲惫和叹气的味道,开口说“魏黎,她不一样...”
“军令如山。”魏黎直接打断了饿鬼的话,他之前看起来极其的不近人情,但说出这句话之后,却愣住,回避了饿鬼的视线。
“嘿嘿,好,好一个军令如山。”饿鬼又开始嘿嘿笑,我听着心里突起莫名的心酸。
我曾经问过饿鬼,为什么越是无聊的地方他越笑。饿鬼那个时候,也是笑着答我的。他说生活已经很艰难,笑起来就能假装让自己觉得好一些。我看着饿鬼的背影,突然觉得有很多东西自己都不知道,包括他和魏黎。
饿鬼不能再护我,意味着这一次我将站在前线。我转身走回黑衣士卒的队列,从他们衣服的缝隙中,狠狠地看那个骑在马上的男人。我心里是燃着火的,即使手上握着冰,如果这几次能撑过去,定要让魏黎跌下将军的位置。
人群无声而秩序的走向前线,我的脚踏在巨石上,向下看是万丈深渊。
蛮人踏上巨石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地面的颤动,即使知道他们被减速,被饥饿所扰,他们的动作仍然每一下都是杀机。我混在人群中,凭借着身材矮小,在士卒的腿边穿梭。
腰刀虽不长但胜在巧,这段时间的训练,凝结腰刀已成为身体的记忆,我变得轻盈,有风穿过我的衣服。此时蛮人距离极近,我面前一士兵举起长刀,但他慢了半拍,于是蛮人双拳生风捶下,若击到他身上,必然骨碎鬼散!
眼前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轰鸣,双手紧握刀柄,拼尽全力挥向蛮人腰侧,刀陷入肉里,鲜血飙起数尺,溅得我满头满脸。骨刀没有受什么阻碍,几乎是一场轻松的分割,反倒是我用力过猛站不住脚,刀尖差分毫就伤到那黑衣男人。
黑衣从蛮人拳下逃过一劫,惊魂未定又躲过我的刀锋,然后用沾血的手拍拍我的头顶,又投入战斗,我看着他提刀的背影,觉得难以形容的帅气。
他这一拍,蛮人的血就把我最后一点干净的头发黏住了,我用手抹了把脸,就着血把眼前的头发朝后一撸,心里的战意就燃起来了,我要战!
这一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快黑的的时候,我隐隐感觉自己的掌控力到了尽头,骨刀发出即将碎裂的哀鸣,每一次挥出都让人胆战心惊。终于,我也同那男人一般,耗尽了力气,蛮人的掌风挥下,我几乎举不起刀。
“这才不是尽头!”我直视着这一掌落下,几乎咬碎牙齿举起刀来,但我的手比他慢太多,就在这时,骨刀发出最后一声悲鸣,化作骨粉。
蛮人的膝盖却突然软下去,我抵制着骨粉涌入身体,用让它们在空中旋转,盘旋成尖锥的形状,“咔拉咔拉”一层寒冰附上,这变成了致命的武器,穿过蛮人的身体,他轰然倒下。
蛮人不知为何撤退,他们突然显得虚弱无力,逃得慢的都永远留在巨石之上。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骨粉涌入身体,我卸了力倒在雪地上。入眼之处尽是一片猩红,很快新的雪落下,就会覆盖住这一切。
我看向饿鬼,突然睁大了眼睛,饿鬼七窍流血,他回望我,然后缓缓倒了下去。
紧接着,我看见魏黎几乎是第一个冲向饿鬼,宛如条件反射。我突然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而我只能躺在地上,被他们排除在外。
这一次战役饿鬼精神力被消耗一空,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当饿鬼被送回军营的时候,魏黎正骑着马站在冰原之上,数不清的鬼卒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而他一动不动的看着远方,看着茫茫的雪,就像是插在冰原上的一柄长刀。
我那个时候还躺在地上,雪漫过我的耳朵,所有鬼卒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起来是多么的不近人情,可是我看他样子,却又像是极其寂寞了。
魏黎注意到我浑身发软,就策马向我的方向走了些,他的影子笼罩住我,我听到他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他说“饿鬼现在的徒弟不过如此,想取代我,不是谁都可以的。”
魏黎的声音里有一种冷嘲热讽,我不明白他为何会对我如此留心,只听见他马蹄子渐远的声音。我在雪地里躺了很久很久,久到所有人都把我遗忘。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是不服,对自己说“他看不起我,但是我会打败他。”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雪在衣服上覆盖了薄薄的一层,我恢复了力气,终于站起来,茫茫雪原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起了饿鬼,风声在耳边呼啸,我冲回营地,看见饿鬼倒在榻上。
“你还好吗?”我不知道如何开口。
饿鬼很疲惫的招手,就像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父亲,招呼女儿去他的身边。饿鬼这一次花费了太多精神力,他需要一个调养的时间。我走过去问“魏黎似乎对您与众不同。”
饿鬼愣了愣,然后闭起眼睛说“他曾是我的徒弟。”饿鬼告诉我,自己曾是上一任将军。
这消息太过不可置信,我从未想过自己身边那个普通的饿鬼曾有这样的地位,于是发问“可是你们现在的关系很僵,不是吗?”
饿鬼继续解释道“将军的位置是传承,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将军的,就像血液总要流动,如果一直由他统领,他早晚有一日会受不住压力而灰飞烟灭,魏黎不懂这个道理。”
饿鬼像是回忆起了过去的好时光,整个面容都柔和了些,他说魏黎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说起自己能力强大,当魏黎师父的那一段时间。大概是受伤而脆弱的缘故,那一晚饿鬼说了很多我曾经不知道的事情。
鬼铠营的将军是会变老的,与人世间不同,只要处在将军的位置,能力就会一天一天减弱,直到消失。所以每一任将军都会在适当的时间退位,重新做回营帐的首领。
魏黎曾经出色优秀,历史中无一人能与他相及,他从未输过。对他而言,从将军的位置上退下,就是服输。他宁愿战死,也永不服输。
一百年中,饿鬼曾一次又一次劝说魏黎退下来,可他哪里听得进去呢?后来,也就不认饿鬼这个师父了。
“你会打败他,但请你让他活着。”饿鬼如此对我说,我看他眼神切切,那是一个师父的眼神,也是一个疲惫的父亲的眼神。我心里一酸,饿鬼从未承认自己是我的师父,对他而言,只有一个徒弟。
“好。”我说,凝结出骨刀向营帐外走去。
又是一段漫长的习武时间,这人间究竟是冷是暖我分不清楚,只知道大雪下个没完。后来又是几次战役,饿鬼精神力不足,但他仍然强撑着上阵,魏黎并没有阻拦。
我心里觉得魏黎相当冷酷,他对饿鬼似乎半点情分也没有,就像是对待一个陌生人。这就是所谓师徒吗?虽然他是将军,我依然看不起他。
当我逐渐适应鬼铠营的生活之后,日子变得好过了很多,长刀上慢慢可以稳定凝结一层冰刃,锋利无比。
一次,饿鬼唤我到身边,他说“你也要有个名字了,叫魏霜如何?”我欣然接受,后来才知道魏姓是每一任将军的姓氏。
魏霜的名字在军营里传开,战争打响的时候,我的位置一次比一次更靠前,我杀更多的敌,冰霜的能力逐渐被展现。后来在鬼铠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很可能成为新一任将军。魏黎没有任何表示,只是风雨欲来。
“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我问饿鬼,这个时候我已经与刚入鬼铠营的自己全然不同了,眼神里尽是杀伐英气。
“再让魏黎最后统领一次鬼铠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饿鬼与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我曾想,自己在他的心中,大概永远比不上魏黎的位置。
得不到感情,那就要得到地位,对我而言,站在前线是冷的,骑在马上也会是冷的,我也许与魏黎是同样的人。
那么怎样避免独行的悲哀呢,也许是足够高傲。
当我终于能自由控制冰霜的时候,蛮军再一次进攻。临行前饿鬼抓住我的胳膊,他说“别忘了你曾答应的话。”我突然想笑,但心里发苦,也许这一战之后,我与饿鬼就不在会以这样的身份对话了。
“我知道。”我看着他,继续说“您从未把我当做徒弟,但我,会记得您的恩情。”说完,便深深鞠躬,向前线去了。
“你与他太像,总看不到人世间的温情。”这是饿鬼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与魏黎对视,似乎是一场交锋。
蛮军踏上巨石,战争如出一辙,血斗之后蛮人退军。就在所有鬼卒准备回营休整之时,一道高高的冰墙筑起,挡在魏黎的前面。所有人停下动作,我感受到饿鬼的视线,但没有向他看去。
我盯着魏黎,每一步踩在雪地上,走得缓慢又坚定,直到走到他面前。
四周雪落簌簌,除我声音之外别无他响,我说“拔刀吧。”
鬼卒四散退去,魏黎低着头看着我,片刻的沉默之后,他下了马。我弓起身子,骨粉从身体盘旋而出,带着森森寒气,在身后凝结出数道冰刃。冰霜的能力之所以强大,在于借助环境的天时地利,武器无处不在,防御滴水不漏。
我第一次看魏黎抽出七尺骨刀,他气势夺人,刀一挥,雪地留下深深的印痕。
魏黎确实统领了边境百年,每一任将军都有天选的才能。饿鬼曾说,魏黎的能力在于侦查,能看百里之外,也能察分毫之间。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仿佛自己一招一式都在他的判断之中,着实可怕。
魏黎能预判我所有的动作,能挡掉处处进攻,又刀刀在我的防守缺漏中。我的冰盾承受冲击,几次之后竟有了要碎裂的趋势,但他丝毫没有卸力。我有些狼狈,从未想到魏黎的骨刀竟如此出神入化,他一直骑在马上,远离前线,以至于我轻视了他本身的实力。
但我不曾畏惧,我这些日子遇强则强,倒未有过败绩。心里不服的念头冒出来,身体轻盈躲闪,我将骨粉一半作刀,握在手中;一半作盾,环绕身侧。就此几个来回,与魏黎不相上下。
“这是要杀我?”当魏黎的刀再一次从我身前挥过时,我后退几步,死死盯住他。
“因为你贪得不该属于你的东西。”魏黎神情孤傲,不可一世。
“所有的东西都是伸手取来的。”我回这一句,不再与他多言。这时候冰原降下大雪,可谓上天的助力,我犹豫许久,心里闪出有一个念头。
我从未让骨粉离开我太远,无论是刀是盾,都是有型的。可是看着飞雪和冰原,我和魏黎都显得极其渺小,突然心中似乎有所顿悟。
我向来将手握得太紧,只看到那些可以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看不到的,虽然无形,但却是存在的,是我太过狭隘了。于是散尽骨粉,融入漫天大雪,空气中尽是杀机。
魏黎能判断我所有动作是不假,但他在将军位置上时日已久,早已不能与往日相比,即使心里清楚,身体是跟不上的。我似乎融入了风里,不杀他,要重伤他,以报魏黎的轻视之仇。
魏黎逐渐应对吃力,胜负已经初定,我伸出右手,风卷着骨粉在我手间一寸寸凝结成刀,我提着刀一步一步走向魏黎,我看他在寒风中如同困兽,一切该结束了。
未曾想自己在最后关头松了警惕,竟给魏黎可乘之机,他猛地回声,眼里满是鱼死网破之势!我大骇,此时已来不及后退,可就在这时他动作却是一滞,我与魏黎同时意识到什么,是饿鬼。
魏黎拼力一搏,却仍慢了半步,我的刀架上他的脖子,犹豫片刻,没有伤他。是饿鬼最后帮忙,我赢的并不光彩。
“你输了,退位吧。”魏黎听我这句话突然笑的怔怔,很久才止住,他看向饿鬼,眼睛比冰还寒。饿鬼只是转过身,消失在鬼卒之中。
“你们如愿以偿了。”
“饿鬼不是我的师父,他只有一个徒弟。”我说完便向鬼铠营走去,魏黎仰面倒在雪地里,安静的就像死去了一样。
去鬼铠营收拾行装的时候,饿鬼并未与我说话,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老人家了,鬼怎么会衰老呢?我想不明白,只觉得他已经疲惫至极。
将军住所与我曾住的地方不远,又感觉千百般远。无论是鬼卒还是将军,一代又一代交替,突然觉得我们都算不上什么了。
提着包裹出来的时候,冰原天地一白,唯我一人独行,觉得十分寂寞。
此后,鬼铠营迎来了一位新的将军。
====================================哈哈哈哈哈我又回来了,神不神奇
微言情(划掉)言个鬼的情
开新坑开新坑嘿嘿嘿嘿
目前所有坑都填完了,可把我牛逼坏了(叉腰) 1/7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