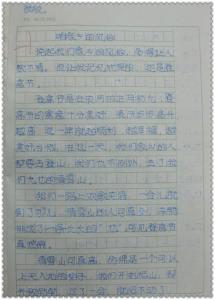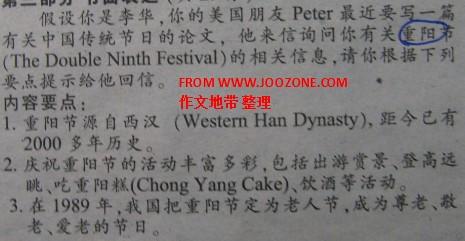重阳节的传说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梁人吴均在他的《续齐谐记》一书里曾有此记载。
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另外,在中原人的传统观念中,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后来重阳节被立为才老人节。

中秋过后又重阳
今天是重阳节,你们打算干什么呢?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对重阳节没什么纪念意义性吧。回答是不是的,重阳节不但是有纪念性也是有意义性的。接下来我就说说重阳节的起源吧:
“中秋过后又重阳”,起源于汉初的重阳节有着悠久的历史。要说重阳节的来历,那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汉初。据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惨害后,宫女贾某也被逐出宫,将这一习俗传入民间的。
古代,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人登高诗很多,大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重阳节还要赏菊饮菊花酒,起源于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士大夫,还多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很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种。清代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
重阳节除了佩带茱萸,也插菊花。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传承至今,重阳节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活动丰富、情趣盎然的佳节,各地人们通过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活动来欢度这个历史悠久的节日。
缺少了我最赞赏的地方,恒景拜师学艺,杀死瘟魔才让九月九登高的风俗传下来。
由重阳想开去
重阳节也称作老人节,理应把为老人祈福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们这里却很少有见到如此的,也许是缘自忌讳。人到暮年,脑子已大不如壮年时灵光,想得最多的就是大限之时。愈想愈怕,于是愈发受不得一点刺激。别说是祝福长寿了,光是翻翻日历都会默然良久。比如我外婆寿已七十有六,眼睛也不大好。我们这一带以九的倍数为人寿的灾祸之年,视为不祥。比如二九十八岁,八九七十二岁等等。时不时就听见外婆叹气,八九七十二,要不要还呐。逢年过节给我们压岁钱时总以“现在不给就来不及了……”开头。我望向夕阳,西沉的日头给眼睛带来一丝刺痛。很多老人就是这样的心态,固执得像一头牛,什么重阳不重阳对他们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渐渐发现,现在的节日更像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忘却古老,忘却过去。在我们一次次用食物和整天的锣鼓喧嚣深化节日这个仪式时,节日真正的精神与内涵却在渐行渐远。若有一日一觉醒来,重阳节凭空消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不知我们是否会感到讶异,寂寞,抑或是漠然。
也许一个节日最好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一个记得这个日子的老人躺在一把摇椅上,目光随着落日下降,渐渐闭上。这就如同一个文明的覆亡。别妄想与天地同寿,那只不过是一个水中的梦。当社会已不再需要,当再也没有更多的理由让它存在时,有一个完满的终点,比它如何开始更为重要。
当然也有可能是由这个节日衍生开去,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含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比之彻底消亡的说法,我也更为认同这种说法,毕竟走极端的只是少数,完全维持中平不被同化的概率几近于零,还是融合来得更为妥当,弱化了具体的概念,而能将精神内核提炼出来。
于是就想到一个关于民族大同的问题。早些时候我对他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后来砖头与我提起,一个民族的走向,无非是两种,即同化他人和被同化。对当今这个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的世界来说,出现统领全局的文化只是迟早的事,当然现如今这个问题便转化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争斗,简言之就是中华文明与欧式文明的一场战争。中华的儒家文化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平正,中庸,凡事不争第一也不落最后,于是团队作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欧式文明更讲究竞争,也催生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这场战争也许会旷日持久,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细节而闪电结束,总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许要靠来自外太空的非自然可抗力了。砖头更倾向于中华大同思想的最终获胜,但究竟以何种方式来结束,就要留给历史来印证了。
一个文明的推演,要依靠一次次的铭记与深化;而希望这一次,不会仅仅流于形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