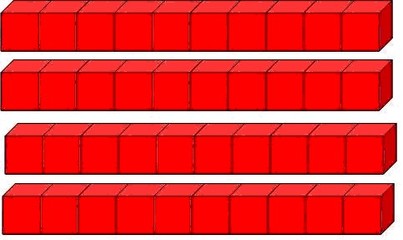曾经,话梅,汽水,山楂片……,都是可以轻易送我们味蕾上天堂的玩艺儿。而如今,舌头像穿上了防弹衣,很难再被什么东西击中。

有个朋友,读高中时,地理老师跟他们描绘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譬如美国,为了说明其富裕程度,他说,美国人把牛肉干当茶余饭后的日常零食,没事就嚼几片。在座的同学,包括我那位朋友,一听之下全暗地涌动着青春期分泌汪盛的口水,心里喟叹,美国人真奢侈,真TM资本主义啊!
因为牛肉干,他记住了这位地理老师的名字。该老师后来考研出国了,他和同学们都猜,老师一准是被“茶余饭后嚼牛肉干”的生活诱惑出去的。
也是这位朋友,他说,小时吃过的冻梨真好吃啊!甜美,爽口,像雪在舌尖上融化。我起初以为冻梨是北方产物,是他某位北方亲戚捎来的,后来弄明白,冻梨其实就是些烂了或将烂的梨,因为便宜,冬天,他母亲从供销社之类的地方买来搁窗台冻着。朋友说起冻梨的沉醉表情足以使人认为那是世上最美味之一!
于是特意从超市买了水晶梨,在冰箱里冻上,某日来请他一块朵颐。他期待地望着梨,我期待地望着他,他咬了口,面无表情,“怎么了?”,“好像……味道和以前不一样”,他不仅没吃出原来那股子“此物只应天上有”的美妙,而且,他的牙和少年时期的牙也大不同了,那时的牙坚实,宽广,任什么内容都能在咀嚼之后转化成愉悦,而现在,他的牙在过多精细食物的簇拥下反而日益脆弱,一只冻梨首先在硬度和凉度上就打败了他,尽管他怀着对过往岁月的依恋与追忆,这只梨还是没能吃完。
他很困惑,是梨不一样了吗,难道是不够烂?还是冰箱怎么也冻不出冬天室外的味道?那时的冬天冷得真刀实枪,能把一只烂梨冻得硬实无比,甘冽无比,在味觉记忆中占据峰值。
还是这位朋友,当他站在城市最大的超市,发现自己成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没什么食品能再撩动他,令他蠢蠢欲动。
难道自己患了“吃冷淡”?他自问,那曾经的生猛胃口怎没了踪影?为这胃口,他曾省下车费在寒风里走了两个多小时去亲戚家,换来一包冬瓜糖;为这胃口,他和哥哥在日头下推了一星期沙换了两笼小包子外加几支冰棍,幸福得快晕厥;为这胃口,他上树捉知了,下河摸螺蛳,吮吸映山红和美人蕉花蕊,为了那一丝珍贵的甜……总之,他为吃做过许多痴情的事。
不止是他。那时,几片五味姜,一小把杨梅,就能领着我们向幸福可劲儿奔跑,而现在——整个超市都攫不动我们寡淡欲望。
当终于有贼心和贼胆时,贼没了!贼没了!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啊!盼了那么久,像穷人家孩子,攒了许久钱,想着要去街角的猪血摊挡恶狠狠地尽次兴,钱总算攒够,然而,摊子没了!不知道何时没的,街角空荡。风凉嗖嗖地刮过,手心里那把硬币忽然没了用处,它们只是一把锡和镍,或铝和铜——就算金子又怎样?总之换不回能让血一下子哗哗流得快起来的东西!
舌尖上的初恋消失了。
那时,我们的味蕾爱得卑微又热烈。普通一点玩艺就可让口腔升腾起焰火。如同初恋,并非那个人有多美好,而是那个时节,我们的心,因为空白如洗,轻易获得了初次而永恒的颤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