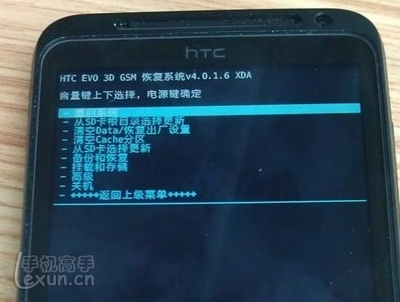幸而昨夜他没去找她,否则必然望见忍冬藤上,每处探出的花蕊都藏着一张扁平的人脸,悄无声息的在哀哭,在求饶......
她依稀记得那个秋天午夜的月色,像一匹闪亮的银锻。

锦绣山苍莽绵延,人迹罕至。有溪名狐尾,溪畔的白果树,怕活了数千年,枯了半边。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那半边枯木上探头看世界,彼时她只是一株忍冬藤。依附着白果树,尽情地吸元纳气,因为一点未泯的灵性而成了精。
忽然有一天她化为人形,落在地面。一袭雪白的纱裹着年轻的身体,乌亮亮的发间插着一支簪,是忍冬的造型,枝生叶,叶缠枝,尾端一串莹然无瑕的花朵。
是那般令人呼吸骤停的美,让山间砍柴的樵夫,望她的刹那,魔怔般追随她那雪白的赤足,来到她栖身的茅草屋……最后,魂魄化作她那支玉簪里细细的一丝花蕊。
这支簪子,是牵连着心与命的宝贝。须得拿这些人的性命,好生供养滋润,这由精到仙的修炼,方算又进了一层。
记忆一旦被翻开,最清晰是那年秋夜。“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那夜她在溪边濯足,轻快地哼吟着这楚辞。是某个痴于求仙问道的书生留给她的竹简上所刻写的句子。那书生的模样,她努力回想,却怎么也看不真切。只记得那书生笑起来傻傻的,单纯的像个孩子,直至断气的一刹那,忽然不似往常遇见的那些豪士勇夫那样死得痛快,只是低低的叹了一句:“世人之险,犹险于此,你千万小心。”
霎时间曾错以为他是真爱过她。后来才知,那或许是一句恶毒的诅咒。
(一)
那天,他憩在狐尾溪畔一块青岩后,许是睡眼惺忪中为她银铃般的山歌所惊醒,唯恐惊破这镜花水月,轻轻收拢露在岩石外的一角粗葛短衫。她捕捉到这细微的声响,诧异回过头来时,就撞见了他的一双眼。干净明澈,仿佛天上寒星,又似一口深井,引得她想要跃身而入。
电光石火的刹那对视,她竟舍不得转开脸。“我认得你,我曾见过你。”她肯定地说。他那样局促又仓皇地退缩着,一
味地晃着手,“你……你如何识得我?”
她伸手去翻看他藏在草丛里的竹篓,都是她识得的草药。原来是个采药少年。忽然她生出奇异念头:倘若舍弃一切,一心一意与这样一个少年度日,那又如何?
她诈称孤女,在山野里长大,未涉足过尘世。他憋一阵终于羞涩地问:“我叫凌霄,你叫什么?”想想又急忙补充一句:“凌霄是一种药藤,性寒味甘,可行血去瘀,凉血祛风。”
她抬眉一笑,“巧是不巧?我的名字唤作忍冬,和你一般,既是藤蔓,又可入药。”他摸着后脑勺憨厚地笑了。
她邀请他:“何不去我家小憩片刻?”他乐呵呵直说不敢不敢,脚却不听使唤,随她迤逦而去。
他七岁没了爹,生计艰难,母亲无奈带他到药铺当学徒。次年母亲也去世了。学徒生涯极辛苦,样样杂活都得做。渐渐熬出头,才跟着师父学了些粗浅的药理。他絮絮地讲他的遭遇,她听得极认真,眼神里是一种温柔的怜爱。
住了三天,他忽然鼓起勇气,“我们成亲好吗?”夜夜她都燃一炉香,只为让他睡得沉实,方能在清寂的夜里悄然蜕化为一株藤,沿着白果老树一路蜿蜒而上,向着风,向着月,把这世间最清明的一股气收入腹中,又吐出积聚丹田的浊气。那枝上细碎的花黄黄白白,在她心无挂碍的修炼时分开得最灿烂。
春天,他花了许多心思,用白果树上的忍冬花藤替她编了一只茶篓。她见了茶篓,脸都白了。他却懵然不知:“是编得太粗糙吗?你不喜欢?”“哦,不。”她强笑着背起茶篓转圈给他看。这枝枝叶叶都是她的血,她的肉,她的灵,但这是他第一次送她礼物,她怎能不受?
那一夜不知怎么熬过来的,她化身为忍冬藤,触摸着无数被折被斫的伤口,有些仍挂着血一般的汁液。若非因为爱,他怎可能伤得到她?隔日他好奇问她:“昨夜你去了哪里?”呵,她元气大伤,那一炉燃香竟没令他昏睡。她眨着眼睛狡笑:“你不记得山中我有许多小兽朋友?好些日子没去看它们了。”她一声笑,自顾自就出了门。
他在溪畔找到她,将她上下端详:“你那支簪子呢?”她随口回答:“想是方才匆忙,落在什么地方了吧。‘’
那连着身家性命的宝贝,因她精血太过耗损,哪里还镇得住数十冤魂,早已还原为一支粗硬藤蔓,拼命地汲取着养分。幸而昨夜他醒了没去找她,否则必能望见白果枝间缠绕的忍冬藤上,每处探出的花蕊都藏着一张扁平的人脸,悄无声息在哀哭,在求饶。
并肩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望着山头的夕阳,忽然他微微一笑,“不知不觉,竟一年了。”
她猜想他是想念俗世生活的。他不快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