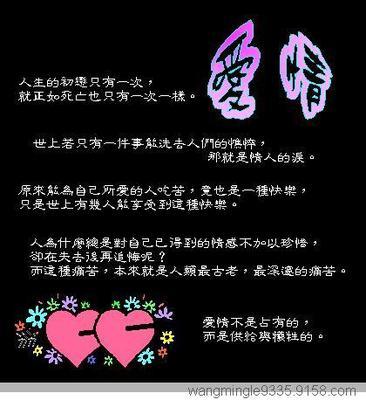我生在美国,我的生活蓝图似乎跟别人不太一样。

画面跳到我5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华盛顿上小学,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了两个星期一年级的课。突然有一天老师没有来,我回头一看,见老师站在不远处跟校长在说话,指着我的方向。他们说完话,老师过来帮我收拾东西,然后带我去了二年级的教室,我从此就念二年级了。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美国教育真有了不起的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这个人就跳级了。什么手续都不用办,连家长都不用通知,就直接把我放到二年级去了。
画面跳到若干年以后。我在11岁的时候回到台湾,我在美国是资优生,从来没拿过B。到了台湾之后,我被剃了个小光头,背个书包,带个便当,天还没亮已经往学校去,天黑了才回家。那一年念完了,老师最后决定让我留级。老天是公平的,我是一边跳级,一边留级。因为我父亲是外交官,父母的想法是,调回台湾3年,我可以好好学中文,等有了中文功底后,我父亲再外派出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可以念哈佛、耶鲁或者其他学校。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父亲在这3年内生病过世了,我的人生蓝图整个发生了变化。我们家变成单亲家庭,政府有所谓的抚恤金,但根本不够吃饭,所以我的命运有了一个大逆转。幸好母亲极为坚强,她非常努力地把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带大,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太管我。
那个时代,父母不可能鼓励你去走文学或者戏剧这方面的路,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那个时代里所有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
镜头再跳,我在台湾念完大学,结婚了,回过来学戏剧。那时候我跟太太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所小公寓里面,那所小公寓非常热闹,经常有朋友来住,地上都躺满了人。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管他叫毛弟,台大毕业后到美国研究所学习。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我记得他当时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后来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他每天跟我们聊天,每天跟我们说人生怎么样不如意。后来找到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也交了女朋友,慢慢地找到了人生方向,生活变得如意了。
同一时间,我在学一些戏剧理论,尤其是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的理论,他一直在讲戏剧形式要有怎么样的翻新,不能有任何的界限,我读不明白。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毛弟出了意外。这个意外说起来荒谬,他被派去一个赛狗场摄影,赛狗场有个电动兔子,电动兔子在栏杆上跑,所有的狗都跟着跑,他为了找最佳的摄影位置,整个人跨在栏杆上拍,后来电动兔子过来,把他撞了。他出事后,好几个朋友开车赶过去送他,车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我们都很沉默。参加完他的告别式,我们同样地开了10个小时的车回来,路上一句话都没讲。
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想到阿尔托说的“什么叫自由”,想到一个电动兔子可以突然冒出来,把人撞死。生命本身的状态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画面再跳,跳向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的画面。那时候我跟太太带着女儿——大女儿才7岁——去了印度北部山上的一个小镇,那个镇非常穷。我太太有一天说她想洗个头,水送来了,她才发现这水是镇上的人翻山走了两个小时才挑过来的。她非常感动,一盆水,不光洗头、洗澡,还洗了衣服。那里的路很糟糕,另外,镇子里一天大概只通电两个小时。
我们走之前问了一下,如果要给那里通水电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其实那里水是有的,只是没有管子通过来。路是可以铺的,电也可以接过来。这些需要几万美元,那个时候这些钱也不算少了。我们就找了10个朋友,凑了这些钱。现在那个地方有水、有电,路也修好了,非常方便,小镇也发展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怎么都想不到,我女儿现在就住在那个镇,因为她嫁到了那里,她的家就在那儿。她不知道这个故事,现在她所住地方的水、电、路等设施,都是我们当年帮忙修建的,这真的很意外。如果当初有人预言说我做这件善事,几十年之后,我的女儿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我一定不会相信,可能反而不会去做了。
这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一点一滴中形成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