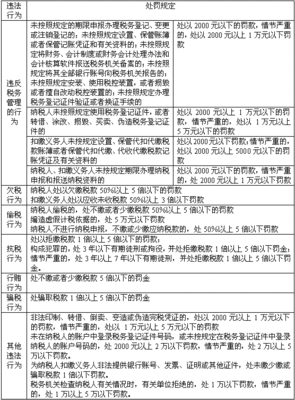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 “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