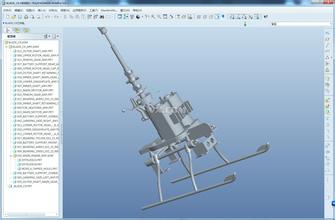海仲上海分会成立6年来,共受理案件200余件,标的金额达14亿元,纠纷类型包括:船舶建造和买卖、船舶碰撞、船舶租赁、货运代理、渔业纠纷等。2009年,海仲上海分会的平均结案期为63天,约四分之一的案件是适用快速审理的简易程序。据蔡鸿达介绍:“海仲审理的普通程序案件,在6个月以内必须要做出裁决;简易程序案件,3个月内便能做出裁决;海事调解案件所需要的时间更少。实际上海仲大部分案子的审理时间都比仲裁规则规定的要短。”

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海仲的仲裁质量也很高。蔡鸿达说:“在全国范围内来讲,上海地区的海事仲裁员相对集中且水平较高,他们熟知航运业务实践,法律修养深厚,办案兢兢业业,这使海仲上海分会出具的裁决书质量无可挑剔。同时海仲内部有严格的仲裁管理和监督制度,设专职秘书处协助仲裁员管理仲裁程序,这既能保证仲裁的快速推进,又能有效杜绝程序上出现纰漏。至今,海仲上海分会没有一件案件被法院撤案或不予执行。” 2008年末金融危机肆虐,航运市场首当其冲。许多大型船舶的建造和买卖合同都受到很大影响,弃船、毁约的情况屡见不鲜。2009年5月14日,山东某海运公司一纸诉状提交海仲上海分会,要求解除其与江苏某船舶公司签订的“苏剑南”、“苏高邮88”、“元顺168”三条船舶的买卖合同,原因只是因为江苏公司未能及时为该三条船舶办理营运证注销手续。而仲裁庭经审理查明,涉案的三条船舶早已移交山东公司,但是由于当时船舶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船价大幅下跌,山东公司眼看自己买来的三条船舶大幅贬值,就寻找了借口以解除合同。最终,仲裁庭作出裁决,裁定山东公司不能解约,但江苏公司也应及时办理营运证注销手续。仲裁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公正、高效处理了这个标的金额上千万元的大案,受到当事人和办案律师的一致好评。 与伦敦仲裁相比,快速高效是中国海事仲裁的一个独特优势,据蔡鸿达介绍,由于英国实行完全自由的临时仲裁制度,仲裁员虽然负责管理仲裁程序,但由于精力有限和仲裁习惯,仲裁员实际上对仲裁的进行缺乏控制,纠纷双方的律师才是仲裁程序的实际推动者,而律师很容易在程序问题上纠结,这会拖延仲裁时间,影响仲裁效率。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每年受理的案件中作出裁决的只有2/5,余下的或是不了了之;一些中方当事人则因忌惮程序拖延和因此产生的律师费用,未战先降,选择私下和解结案。 海事调解 除了海事仲裁,海仲上海分会还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开发多元化的纠纷争议解决机制。分别成立了渔业争议解决中心和海事调解中心。 “中国现在大约有25万条渔船,每年产生大量的渔事纠纷需要解决。到法院打官司耗时费力,渔民更倾向于求助与自己生产经营联系紧密的渔政部门进行行政调解,这增加了渔政部门的工作压力。”蔡鸿达表示,“同样,依据交通部海事局的数据,全国平均每年发生400余起海事事故,仅上海海事局管辖的海域内每年就有100余起。 这些海上事故的特点是:1、发生在主航线上,直接影响海上正常交通安全,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及时清道,紧急抢救、救捞,费用成本大;2、人员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事故善后处理,损失理算,争议解决都十分困难和复杂。长期以来事故调处工作是由海事部门来承担,一线海事部门平时工作任务就已经十分繁重,大量的事故调处工作加重了一线海事调查官的负担;而且,海事事故通常牵涉外轮,外方当事人往往会质疑中国行政调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农业部和交通部海事局都希望我们这个独立的民间机构参与进来,将行政调解转变为民间调解,海仲的海事调解中心和渔业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应运而生。”
海仲海事调解中心和渔业争议解决中心成立至今,先后成功地解决了“豫梅盛3698”轮与韩国籍“Star mariner”轮,“粤顺”轮与“生松1号”轮,韩国籍“Pos Brave”轮与“浙嵊渔0913”轮等几十件海事、渔事船舶碰撞案件。这些成功的案件,在航运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交通部海事局大力支持进一步在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推动这项工作;农业部渔政局今年更是在全国挂牌设立8个渔业争议解决中心办事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渔业仲裁。
发展之困 在《新民周刊》对几位资深海事仲裁员的采访中,他们都表示这一行业需要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沈满堂是中国海运集团法律总顾问,自80年代末从事海事法律工作,2006年正式被聘为海仲仲裁员,4年来已经兼职仲裁了十余件案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位有着20多年海事仲裁和审判经验的专家感叹道:“中国的仲裁员素质很高,可惜整个软环境不够好。西方对我们的恶意宣传,使得很多国外公司误以为中国的仲裁缺乏诚信度,因此我国的海事仲裁等航运服务业总是起不来。” 如今,伦敦每年海事仲裁收入2亿多英镑,在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海仲虽然排名世界第二,但业务规模和影响力显然小得多。按理说,中国已加入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世界上加入《纽约公约》的145个国家是承认中国海仲的裁决的,并可直接申请在这些国家的法院强制执行,但仍出现海仲案件受理量与中国航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软实力”缺失导致的。 蔡鸿达说,时下上海发展海事仲裁的形势非常好,但大多数航运、物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还是没有写上将有关争议交给双方所同意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条文。由于仲裁前提是争议双方当事人签有仲裁协议,否则仲裁机构无法受理。而中国仲裁法对仲裁条款的严格要求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海事仲裁的发展。 海仲的独立身份决定了它不能有政府和行政色彩,否则当事人就难免怀疑海仲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海仲上海分会顾问、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雷海,曾多次在航运专家会议上呼吁:政府部门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海仲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氛围,如推广普及海仲知识、培养海仲人才、在航运界大力推广标准的海事仲裁条款,鼓励航运相关协会为会员提供标准合同,规范争议解决条款。营造环境而不直接干预,在上海海仲事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已受到认可,而上海要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人们同样期待政府作用的发挥。 根据伦敦、纽约等海事仲裁事业发展的经验,海事争议的解决应遵循双方自行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的原则,也就是小审判、大仲裁的做法。法院作为国家提供财政资助的审判机关,理应“不诉不理”,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海事审判只能作为各种尝试失败后的最终选择,不应轻易采纳,法院更不应主动承揽诉讼官司。伦敦法院对海仲的宽松态度,巩固并提升了伦敦海事仲裁的国际中心地位。上海海事仲裁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法院的有效监督与支持,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特定环境下,通过司法和地方立法的方式扩张“上海海事仲裁”的有效性。 海仲上海分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著名海商法专家,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尹东年也指出,“海事仲裁”是几百年来国际上早已形成的习惯称呼,但不知什么原因当下“航运仲裁”充斥着整个上海滩,上海要发展海事仲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还是按国际习惯称之为“海事仲裁”为好。 他还强调,英国伦敦海事仲裁的发达是与其保险公司、保赔协会向当事人竭力推荐伦敦仲裁分不开的。英国众多的保赔协会例如西英船东互保协会、北英船东保赔协会、联合王国保赔协会、联运保赔协会、联合王国抗辩和诉讼协会等,都要求其会员船东签订有关航运合同时订立伦敦仲裁条款或者产生争议后使用伦敦仲裁解决,以有效控制和降低法律风险。保赔协会的这项举措影响非常深远,大量的船东要获得保赔协会的赔偿,就必须依照这些保赔协会的指示进行伦敦仲裁,由此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伦敦仲裁的发展。上海要发展海事仲裁,不容忽视保险公司、保赔协会作为最后埋单者的重大作用,应当鼓励这些公司、协会使用上海的海事仲裁,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