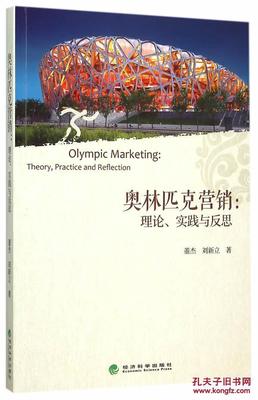陈晓明:林毓生先生对汪晖的批评言论在网上有广泛的流传,我也看到过。开始以为是记者借用林先生的话,以为是林先生被诱导发言。后来才看到编者声称,说是林先生自己看过采访,且订正过采访稿。我稍稍有些不太理解,中国学界的事情,林先生如此关切,如此以紧迫的姿态要求成立委员会来查处等等,一方面为林先生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关切中国学术界发展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窃以为林先生作为老前辈不必以那么紧迫的口吻,那么严厉的期盼(比如使用:“如果不……就要如何……”的句式)来介入这件事。但愿这样的句式是他人的鬼斧神工所为。
说起来,我们在80年代对林先生崇敬有加,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青年学子们是把林先生的著作放在桌上,把他的观点挂在嘴边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汪晖被指责“抄袭”,林先生也加入怒斥之行列。我以为林先生可以看看其他不同意见的文章再提出更加全面的倡议,可能更好些。汪晖当年也是熟读林先生著作的人,对林先生的观点也推崇备至,或许有讨论,有分歧。但林先生的思想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参照,正是这些思想差异,才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代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同阐释。如果没有不同的阐释中国的方法出现,不管是对中国传统还坚对现实的阐释都难有新格局出现,中国学术研究当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王鸿生:林毓生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他关于“反对学术特权”,以及转引自鼐特先生“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的看法,我很认同。强调自律、他律和知识伦理的重要意义,对弊端丛生的大陆学界无疑切中肯綮。林先生快人快语,还看到了学风问题与政治力量影响之间的关系,这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大陆学者感同身受的。只是将此看作“乌托邦革命思潮”的后遗症是否充分或对路,还需要进一步辨析。依我的观察,现在的学界并看不到多少“乌托邦”精神的弥散,而麦金太尔所说的“现代化即功利化”倒是甚嚣尘上。 王斑:林毓生先生也许不认同汪晖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但我觉得,不能因思想倾向的分歧而导致对汪晖十分负面的道德判断。林先生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他最近提出,汪晖的事关涉学术秩序的问题。如果是学术秩序,就可以用学术讨论,学理的分析加以商榷,澄清。也许不能达成共识,但仍然能把分歧摆出来。通过讨论能说明,分歧不光是个人的,可能更是历史的,是思想史政治史的产物。如果执意要通过行政手段把人扳倒,这反而失去良好的、心平气和的学术风格。 《新民周刊》:这次的“汪晖事件”,大众媒体介入很深,网络上也一片混战,这种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媒体怎么做,才能有助于中国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蔡翔: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李陀的看法,大众媒体为什么不能介入学术争论?问题只在于,媒体如何更好地引导这些争论,我想,有两个因素媒体需要注意:一、媒体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这很正常,也很重要,无须大惊小怪,但要有所控制,努力搭建一个公共舆论的平台;二、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体要特别警惕的,可能还不是它的思想倾向,而是积弊已深的“娱乐化”——而在“娱乐化”背后,是所谓的“眼球经济”,是媒体的利润。另外,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以后,遇到类似的“抄袭”指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现在有两种情况:一、向当事人所在大学或其他权威机构举报;二、直接将指控诉诸媒体。我基本倾向第一种情况,因为直接诉诸媒体,不管结果如何(是或不是)都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并会形成混乱。如果不加节制,此风一旦蔓延,会给学界带来很大的危害,如若不信,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媒体应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介入:一,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他权威机构有了明确的定论,媒体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予以讨论,警诫学界;二、举报人久久未获得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他权威机构的有效答复,这时媒体的介入可充分体现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当然,媒体也应做好承担法律责任的准备。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但我感觉这次汪晖的“涉嫌抄袭”之所以如此混乱,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和“程序”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地明确学术举报的应有程序,这样,以后大家就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陈晓明:这次事件,可见媒体能量已经非常强大,也可以说当今人们的生活、人们谈论的话题、认知事物的观点和方法都被媒体支配了。网络上“一片混乱”,也说明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很高,媒体也乐于提供这样的空间。尤其是批判某个知识分子,对某个知识分子表示义愤,这是最能体现正义感,又最安全的方式,这会使人们找到自己高尚、聪慧而又正义的自我感觉。所以,这样的“批判事件”实在是媒体的好素材。
媒体要如何做才能有助于中国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我以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媒体很难对中国思想界负责,只能学界中人自己来负责,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尊重自己。 当然,还是期盼媒体能理解中国学术发展之艰难困苦,80年代才打开国门,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到今天也不过20多年,我们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就是80年代走过来的这代人,这道路并不是身在这样的道路之外的人可以理解的。媒体当然可以严格监督,但媒体最重要的是要有多元兼容并包的胸怀,应该是一个有多种声音并存、多元文化碰撞的空间。
王斑:我觉得大众媒体陷入一种炒作的态势。对汪晖的人格的猜忌,对他的支持者、反对者论战的戏剧性因素很感兴趣,专注于汪晖个人的“沉浮”,加上“倒汪”新一波浪潮,大家陷入一种群体八卦的状态。这并不能促进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真正的百家争鸣应该讨论什么是学术规范,规范的历史沿革,反思中国学术腐败等更大的问题。 《新民周刊》:围绕“汪晖事件”产生了各种意见、说法和现象,相当深刻地折射出大陆学术界思想界的状态,你认为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蔡翔:尽管我认为那些好心人试图把目前的争论还原成纯粹的学术规范之争,收效甚微,但我还是比较认可他们的做法。即使就我个人而言,旁观这次讨论,也是收获颇大。我是近些年才进入大学,在这之前,所谓“学术规范”对我更是陌生,我想,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我指导的学生,以后会在这方面更加严格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我们的学术是一个逐渐规范化的过程,即使今天,也很难说完全规范了——尤其人文领域。我想,在匆忙地给汪晖“定性”之前,应该结合汪晖以及其他有争议的案例,进行广泛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而且应该有法学界的介入,然后形成一个能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具有指导性意义(包括可操作性)的文本,这可能会对以后学术规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更直接的帮助。即使像王彬彬提出的“偷意”、“参见”这些颇有争议的概念,也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不畅快,但我觉得要比匆忙地给汪晖(以及其他有争议的案例)“定性”更有意义。 同时,我也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语言过于欧化,基本上是一种翻译体,这种现象并非汪晖个人所有——事实上,我读过汪晖一些非学术的文章,感觉他的文字流畅老练——我近年的文章也有这种趋向。进入这样的语言写作,我们很容易落入西方学者的思想窠臼,甚至包括他们的用语习惯。但是,我们的理论语言(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学术概念)在哪里呢?有些想法,我们可以通过随笔或其他文体来表达,但是我们毕竟要面对论文写作的挑战,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如柄谷行人所说的“本土性的话语框架”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重要,这里面,有技术的因素,也有非技术的原因。我想,从事学术写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终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自己的学术概念。 陈晓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群落,且也有不同代的学人和媒体知识分子出现,这当然说明当代混杂的思想界状态。我以为此次事件当然把学术规范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步,但同时,对学术规范的批评同样也要负责任,否则,因此形成一支庞大的学术警察队伍——那倒是取得学术成就与名声的捷径,但于中国学术之发展,可能未必真的有建设性。 王鸿生:其实,在学术上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幼稚地起步的,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学人,很不容易地走到现在,并开始在中西古今冲突的背景下寻找自己的“主体性”,是很值得珍视的。但随着影响力的增加,如何进一步建立起内在的反思性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言路、言说方式,对一些学者来讲,却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如,就个体而言,我们都没有对他人的道德审判权,更没有对自己的道德豁免权,这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体认的。如果我们在讲究原则的同时,也懂得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并尊重对手的人格、爱惜对手的才华,不同见解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至于那么水火不容了。 王斑:我觉得“汪晖事件”的炒作和恶化,折射出学术界这样一种心态:学术界就是个名利场。谁拥有什么可申请专利的理论,谁创立的领地神圣不可侵犯;谁走红,声名鹊起;谁被重金聘请为讲座教授;谁的出场费高,谁掌控学术基金,打造、搭建一个个中心、基地、项目;谁拥有什么出版系列,掌控话语权;谁最全球化、国际化,被邀请为欧美学界、世界顶级大学的座上宾;谁开了一个世界级的大会,邀请某某国际名人,有媒体的造势和覆盖;谁的科系在排名上升了,谁跌落了;等等。我觉得还是应该淡漠于势力、权力之争,回到专心学术研究的轨道上,回到培养新一代人文学者和知识公民的路径,不能把学术界、思想界当作名利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