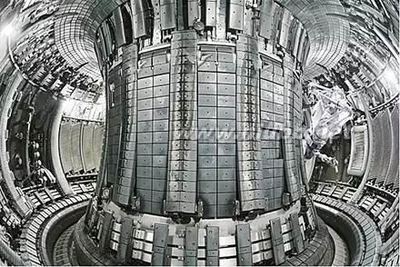记者/邵乐韵 老弄堂里的涂鸦风波 上海华池路211弄,名曰“铁路新村”,其实就是条老旧的棚户弄堂,小摊贩、自行车、晾晒的衣服挤占着本就不宽敞的通道,灰黄矮墙上的裂纹诉说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条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弄堂,最近却格外热闹起来。 5月中旬的一天,弄堂里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在“新村”里华光高级中学内的“上海涂鸦公园”租借了一间工作室。几个老外在墙上喷喷刷刷,没几下功夫就把学校的围墙画得“弹眼落睛”,惹得好多居民都在校门口好奇张望。居民问老外,能不能把弄堂的墙也搞得漂亮些,这些本来就在上海2010世博会参与涂鸦创作的艺术家们爽快答应了:世博会的口号不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很快,鼻子套着橡皮管的大象、有中国特色的龙凤图、抱婴儿的女孩、洗澡盆里的小孩等生动有趣的图画覆盖了原来黯淡的破墙,顿时,老弄堂变得摩登靓丽起来,居民的心情也跟着“牢舒畅”。 住在弄堂口的居民陈济生说,以前也听说过涂鸦艺术,但是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他家里有个17个月大的小毛头,天天拉着大人跌跌冲冲地去“巡”一遍弄堂,看看哪里又多了新的图画。小毛头最喜欢那幅“抱婴儿的女孩”,总是摸摸女孩的裙边,再踮脚摸摸她手里的小婴儿。 可是有一天,小毛头发现,有两幅画不见了,本来涂鸦的地方被抹上了泥浆水。原来老外涂鸦事先没跟当地居委商量,“组织上的人”来清理了,怕老外这么“乱涂乱画”,搞出负面影响。居民们却急了,艺术家免费来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干嘛不让人家画?涂掉太可惜了! 陈济生打电话找电视台来报道,当天晚上,华池路211弄上了新闻,居民们在镜头前强烈呼吁保留涂鸦。这回,没人再来阻拦艺术家创作了,铁路新村也出了名,惹得一批批慕名者挤进弄堂来拍照,其中不乏外国游客。 “昨天就有几个英国人和日本人来照相呢。他们还想到学校里面去拍,现在学校门卫很严,不放外人进校,所以他们只好隔着铁门蹲着拍。”陈济生的妹妹比划着说。 她家门口那幅龙凤图,是德国人在弄堂里画的第二幅涂鸦。她自己还很喜欢弄堂尾那幅洗澡的小孩,画面正好与旁边的水管和水槽相呼应,澡盆上巧妙地连着下水管道,简陋的实物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融合得恰到好处。 40岁的阿基姆·华特(Akim Walta)是弄堂涂鸦创作者之一,他是德国嘻哈基地(Hip Hop Stützpunkt)的成员,也是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城市艺术项目负责人。此次华特召集的团队里除了有德国最顶级的涂鸦艺术家,如路米(Loomit)和肯托(Cantwo),著名麦克莱(Maclaim)涂鸦团体的成员他素(Tasso)和卡西(Case)、擅长专业街舞和文字涂鸦的斯戈蒂(Scotty)等,还有来自韩国、法国、英国等的国际同行。 过去一个月里,华特忙着组织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16个艺术项目,带艺术家们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城市辗转,希望将涂鸦文化和街头艺术呈现给世博会的参观者,同时与中国艺术家开发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就在离开上海参加广州53美术馆开馆仪式之“涂鸦——从德国到中国·广州”活动的前一天,陈家人邀请华特他们到家里吃晚饭,后者则以画册作为回赠。“我们和居民们的关系在短时间里就处得很好了,受到他们的晚饭邀请感到非常荣幸。他们真的很热情,也懂得欣赏我们的艺术。”华特说。 在这个13岁就开始“在几乎所有物体上涂鸦”的德国人看来,涂鸦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架起了沟通桥梁,而且能把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融合到一起,比许多政治家花大价钱搞的项目有效多了。 城市与涂鸦 涂鸦(Graffiti)是指在墙壁上乱涂乱写出来的图像或画作。文字涂鸦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穷街区布朗克斯区(Bronx Zone),当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轻人喜欢在墙面上胡乱涂画各自帮派的符号以占据地盘。 70年代,涂鸦渐渐撇开帮派意识,形成城市涂鸦,除了随意的喷写,墙头和地面还出现了许多精致的图像。到了80年代早期,嘻哈文化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嘻哈文化四大元素(说唱、DJ、涂鸦、街舞)之一,涂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称自己为“写手”而非“画家”,并且给自己取假名或者代号。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柏林墙,不仅记录了一段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历史,也是一段辉煌的涂鸦艺术史。 柏林墙上的涂鸦艺术始于上世纪70年代,20多公里的墙体上有自由与民主、和平与生命等各种题材的画作,其中包括政治意味浓重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民主德国外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兄弟之吻”。涂鸦墙的参与者既有国际涂鸦大师,也有学生和市民,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世界之最。 柏林墙倒塌后,这座最大的涂鸦博物馆也消失了。虽然部分涂鸦得以保留,但近几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德国政府出资300万美元委托艺术家们重现当年涂鸦作品。柏林市长劳斯沃韦赖特说:“涂鸦墙的图像是文献性记录,对以后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图像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柏林涂鸦墙的意义。”

在这次上海2010世博会“柏林周”期间,德国艺术家们就在暂时更名为“柏林广场”的欧洲中心广场上现场表演涂鸦作画,并且配以嘻哈说唱、街舞等表演方式,向游客展示西方街头艺术的魅力。 阿基姆·华特认为,美国主流的嘻哈文化更多偏向商业性质,而德国及其他欧洲城市的嘻哈艺术从一开始便已被认同为“文化”,他所理解的涂鸦是创意产业的重要推动力。“如今许多设计和广告类的创新也融入街头艺术,用于商业目的或进入艺术画廊。我的涂鸦更侧重于表达国际化创新艺术项目的文化内涵。” 对于写手来说,涂鸦与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就在世博德国馆附近,近期捷克共和国展馆内一场名为“大都市”的捷克街头艺术涂鸦展也盛大开幕。 6名捷克艺术家Cryptic257,Masker,Pasta,Point,Skarf和Tron在平均15岁的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涂鸦和街头艺术,混凝土墙、长椅、路灯或地下通道里灰色的墙面对每一个开始的涂鸦作者都是一个挑战。他们长年在布拉格街头游荡,每天都经历着匿名行动而带来的兴奋和冒险体验,经过多年在街上放荡无羁的喷涂,创造了20世纪末的VONTS(指在城市市区冒险画画的一群年轻人)风格,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推进涂鸦的发展,体验着那种不受边界限制的自由感。 这次大都市展上,他们用涂鸦、雕塑、视频等方式创作了一幅未来城市的拼贴画,把玩着梦想与现实。参观者走过砖墙和桥梁会直接进入布拉格地铁站入口大厅,地铁站带有典型大理石墙、布告牌、涂鸦板以及一台特殊的自动贩卖机。有趣的是,里面出售的不是饮料而是喷漆罐和面具。接下来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居民楼群、具有蒂姆·伯顿《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风格的甜品店、以及展现超现实主义客房起居生活的三层塔楼截面模型。 展览将延续到6月20日,这期间,艺术家们还会在馆外一面10米宽的墙上对“生活”进行创作。他们认为,涂鸦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生命力是短暂的,他们都不追求自己作品的不朽。他们自己本身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是活在此时此刻,都迟早会消失在时间隧道中。 阿拉的涂鸦 6名捷克艺术家中,Cryptic的装扮最为惹眼:他戴着一只神秘的黑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厚袜子包在裤腿外面,一副随时准备在街头涂完就跑的感觉。他说,面具体现了涂鸦的“匿名精神”,“人们不认识你的脸,但能认出你的作品,这感觉很棒”。 喷气罐贩卖机正是出于他的创意,这也是请专门公司定做的机器,意在希望让涂鸦爱好者能在街头任意买到各种颜色的涂鸦工具,“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所有写手的梦想,因为在许多城市不允许随意涂鸦。”Cryptic说,涂鸦是他寻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 在布拉格有约100多个街头涂鸦艺术家,但只有5个地方是合法的涂鸦场地,非法涂鸦要遭拘留。当6位捷克艺术家被问到有没有因为涂鸦被抓时,他们幽默回答:“你应该问我们还有谁没被逮到过。”不过早期的叛逆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他们更多参与商业性的项目,不用戴着面罩到处跑了。 尽管嘻哈已经有40年的历史,但对于官方来说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居民能够接受好看的涂鸦,却不能忍受乱七八糟的市容破坏。这也就是街头涂鸦为什么难以定义:到底是美学性产物,还是一种污损和侵犯。1974年,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涂鸦的信仰》一书中,将涂鸦浪漫地解释为社会自由的无秩序显示。而曾经几次因非法涂鸦被拘留的阿基姆·华特更是力挺涂鸦在城市中的正面存在:“城市中充斥着那么多大型广告,你会觉得它们烦人吗?”他得意地说,2006年柏林世界足球锦标赛的赞助商耐克曾邀请他参与国际艺术项目,为5幅巨大的墙壁作画。 “作为嬉哈文化的一部分,涂鸦能帮助年轻人找到积极的人生目标、发挥艺术技能,不仅美化现实生活,还能定义未来的工作。”华特说,许多当年和他一起涂鸦的朋友如今都成了著名的设计家、艺术总监,开发了自己的服装设计等。“没有这种艺术形式,我们今天的世界就会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也会没有工作!” 这两年,华特多次来访中国,每次都看到涂鸦和街头艺术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虽然中国涂鸦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暂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他相信,世博会之后,会出现更为快速的进步。 捷克艺术家Cryptic说,这次来上海,他们一行还专门去了著名的莫干山路涂鸦墙,中国涂鸦者的创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莫干山路是上海街头涂鸦艺术的集中区,而且主要是自发的涂鸦艺术。 负责M50创意园的上海吾灵创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王艺副总经理表示,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涂鸦体现出更加自由、随意、大众的特点。大家普遍认为,在社会认可的地方,用艺术的手法和语言表达的比较正面的“涂鸦”,可以看作是“艺术”而非“乱涂乱画”。 她介绍说,目前在上海,要随性地进行涂鸦创作,没有规定什么审批程序,但也不允许涂鸦。一开始,在莫干山路及周边的涂鸦,也会遭遇官方管理部门的干涉。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以及涂鸦者们所涂的画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官方目前对此基本采取“默认”的态度。 上海的涂鸦者基本上是爱好者居多,有中国人也有老外。他们平时有自己的职业,大多是设计师,业余时间都喜欢聚集到莫干山路来进行创作。有些涂鸦者通过涂鸦而结识,组成专门的涂鸦团队。除了平时自己的本质工作外,会在一起合作参与一些商业性质的涂鸦创作。 上海狂徒涂鸦工作室就是这样一支聚集了国内多名涂鸦精英的新锐团队,成员均为年轻人。团队负责人李振凯说,今年4月,应卢湾区绿化环境管理局的邀请,狂徒在位于卢湾区的汝南街以绿色世博、环境美化生活为主题,精心设计了长达100多米的墙体涂鸦,两边的梧桐树映衬着墙面彩绘,让这条原本不起眼的小街有了别样风情。附近居民纷纷表示应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开展这样的涂鸦活动。 在上海,更多的涂鸦是为了迎合商业需要,比如汶水路沪太路口的那面大型涂鸦墙,是百安居的外墙。今年2月,M50还联盟承办了汶水路动漫街涂鸦墙设计大赛,主要体现宝山区大场镇以动漫及动漫衍生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 通过网络征集设计、专业人士涂鸦绘制,20多天后,一幅近1000平方米的涂鸦墙树立在街头,忧郁的刀刀狗、俏皮的马丁……强烈透视的色块、时下流行的动漫元素,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和外来游客,俨然成了一个新地标。主办方还打算申报“世界最大的单一主题涂鸦墙”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王艺觉得,目前街头艺术在上海的发展与上海的定位仍不匹配——如果上海定位于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繁荣的大都市,那么,目前的街头艺术是相当匮乏的。“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尤其是70后还是非常接纳和欣赏这种随意亲民的艺术,照理说应该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展并生存下去,但是需要合适的物力载体和社会环境。比如说,最好最纯的涂鸦应该是在墙面的涂鸦,但是,大城市里可以涂鸦的墙面越来越少,城管还要出面管一管。从目前来看,即使有一些墙面,大多是一片待开发的工地围墙,临时性的居多。目前,这样的墙面上也有创作,但大多是与世博会有关的儿童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