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一般而言,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人们倾向于反思自我,文化认同的意义也因此而彰显。今日似即类此,国人的往昔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正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钱穆曾提出,世衰则史学盛,因为世道出了问题,前行无路,往往会回头看看过去。中国近代亦一衰世,而史学仅曾有短暂的提升,整体却不能说有多么兴盛。除学术倾向和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变。 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冲击,很多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方向不再是回头看,而是眼光向外,透过东瀛而面向西方。说得宽泛点,就是今日所谓面向世界。这样一种从纵向到横向的眼光转移,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大变,且仍在进行之中。 从辛亥年到己丑年,中国政权在20世纪里转换了三次,类似倾向基本不受影响。中共执政后,1950年代的“一边倒”,1960~1970年代的关注“第三世界”(针对的目标仍是第一和第二世界),依然是眼光向外,只不过聚焦有所转换而已。到“改革开放”之后,眼光向外的倾向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或许因为经济成了中心,“市”道盛行,新的倾向反不像此前一次那么全面,而是回归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一个传统,即试图加入更“阔”的那个“世界”。 简言之,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区别于“古代”的根本性转变,即国家目标的外倾。我曾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来表述这一仍在发展中的趋向。[1]或可以说,这是一个方向似乎明确,目的却未必清晰,越来越体现着当事人的主动,又常常难以人为掌控的发展进程。就像一列有方向而终点站尚属未知的火车,满载无比众多的乘客,正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飞驰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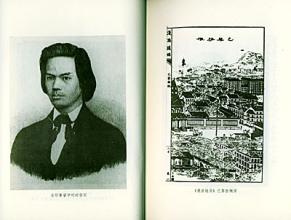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所谓“新中国”,大致即清末民初人爱说的“少年中国”(Young China)。在当年和以后,都被时人和后之研究者用来与所谓“旧中国”(Old China)进行对比。类似的心态持续存在,至少与20世纪相始终。[2]只是不同人心目中的“新”与“旧”,或有不同的指谓。本文所关注的,特指“新中国”那外向的一面,与此前几千年眼光向内的传统迥异。 以前中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古人一方面特别讲究“人我之别”,又总思怀柔“远人”。而中国的“中”和“远人”之“远”,皆以文野为区分(且文野也是可转变的),本不一定是地理的,更多是文化的和心态的。故“远人”几乎就是“他人”的同义词,而“四裔”也往往等同于“四夷”。 不过,古人既有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有“王者不治夷狄”的主张,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怀柔“远人”的方式,主要是“修文德以来之”。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中国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遵行夏礼而沿用夷礼(即坚持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秩序),通常亦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对不那么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随着西力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从自居世界文化中心、视洋人为野而不文“夷狄”,到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在近代中国各种思想遽变中,对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是一个要项。过去许多人爱说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实则更有一个从“天下”到“世界”的进程。“世界”这一词汇在中文里早已存在,很多时候是出自佛教术语的引申,在时人言说中常是世道、社会(或其中之一部分)乃至某一思维境界的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上那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全人类社会。从知识和认知的层面看,今日自然地理意义的“世界”和由人类各族群、各社会、各国家组成的“世界”,对很多晚清中国人而言,是一个过去所知甚少的“新概念”。 这个新的认知既是地理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它逐渐取代了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观念。[3]在此前的认知中,由于万方来朝标志着天命所归,可以印证“中夏”的正当性,“四裔”的存在和向化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若出现四夷不睦的现象,就须自省文德之修为是否有差)。此稍类庄子所谓“非彼无我”,然亦大致到此为止——异己或他人的对照或许有助于认识自我,而自我的存在及其认知,却不一定非要有异己不可。正因此,“四裔”在地图上的反映,有时不过是一个写有国名的方框,最能体现其“存在”的象征性。 所谓“朝贡体系”,曾至少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区域长期运行,为各方所大体接受。其核心观念即夷夏之辨,是这个区域确立国际秩序的主要思想资源。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即在清灭明之后,在日本、朝鲜等地出现了一种试图重新厘清国与国关系的努力,而其重心即在于辨析和重构谁是夷、谁是夏(在大清之内,也曾出现夷夏认同的解构与建构)。不论各方所持观点如何,其所思所言,均不离夷夏之辨的观念。很明显,这既是他们关注的重心,也是当时当地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 不过,“朝贡体系”主要是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性表述,其中多有不为“朝贡”行为所包涵的面相,不必从今日重物质利益的眼光去看。对中国而言,“四裔”在构建“天下”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方面负载了不可或缺的意义,然其存在毕竟更多是象征性的,古人并不特别看重。历代除在战争状态时外,“四裔”很少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心。换言之,这一政治和文化秩序(类似今日所谓国际秩序)虽长期存在,在中国的国家思维(或即朝野以国家为立场的思维)之中,外在因素却仅占有相对次要的地位。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