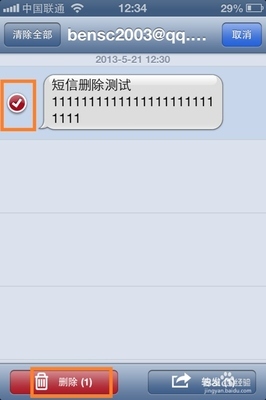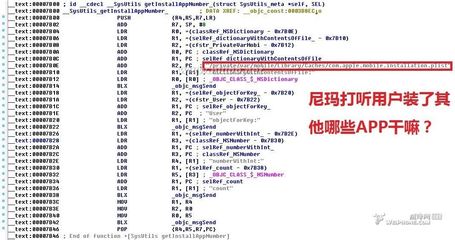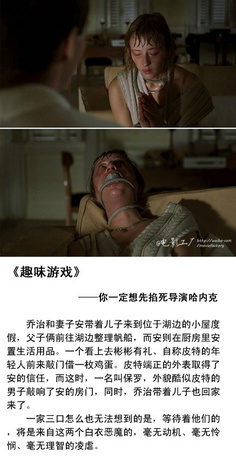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在诉讼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抱着对法律的信仰,权利又如何得以实现呢?

今年5月4日,我收到法律服务工作者肖先生的邮件,内容是关于我和我父亲交通损害赔偿的二审判决书,此时距发生车祸已有1年3个月,接到这份并不令我满意的判决书,个中心酸唯我自知。车祸发生后,肇事方极其不配合,他们仗着有亲戚在当地交警部门任职,先是叫来社会闲散人员破坏现场,后是在医药垫付款上推三阻四,最后甚至就是玩“失踪”。我不想过多在事故责任认定上纠缠,我尊重当地交警部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同等责任,因为,这在当地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但是,肇事方在驾驶前饮过酒,并且是驶入我方正常行驶的左行道,只是当时我与我父亲晕倒,救人要紧,谁也没有想到过取得证据。公安县中医院是全县车祸诊疗的定点单位,我住院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受伤者送过来。隔壁曾经有运用“私力救济”将肇事者铐在床头的情况,以逼迫肇事者拿出医药费。面对肇事方蛮横的态度,沿用肇事方的说法“我们就是要拖”,我们每天都要接到医院的催款单,老家亲戚悲愤不已,几次试图劝说我同意将肇事方“劫持”。我坚信法律必将还父亲和我一个公道,所以坚决抵制非理性的冲动做法。 为了节省医药费,在医院病床躺了77天后,颅骨恢复手术仅一周,父亲就出院了。现在父亲头部的1/3是用一种制造太空飞行器的金属支撑着,而他曾是一座山,在村里担任村长近10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并抚养两个儿子都读到研究生。我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易继明先生得知我遭遇车祸后,率先拿出2000元捐款,全班同学也进行了募捐。父亲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奶奶伤心过度去世。我奔丧回家,面对语词不清、思维混乱的父亲,我强忍心中的悲痛。二审期间,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征询我是否同意调解,被我坚决拒绝。他哪知道,赔偿的意义远非经济层面。可是,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仅为每日15元、护理费的标准仅为每日30元。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判决将我父亲的住院天数认定为误工天数,可按照法律规定,误工时间可以计算到定残日前一天,法院的理由是,出院后,医疗机构并未出具父亲需在家休息的医嘱。一个做了开颅手术的病人回家休息还需要医嘱么?而对我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持为1000元。 肖先生提醒说,更关键的还在后面。保险公司理赔的部分容易执行到位,可是肇事方呢,如果他仍旧不配合,死活说没钱,你也没有一点办法。我不由得想起“私力救济”的隔壁病友,他们把肇事者铐在床头3天后,肇事者家属就乖乖把医药费送来。他们没有讲究法律,更不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可难道公正只能这样获得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