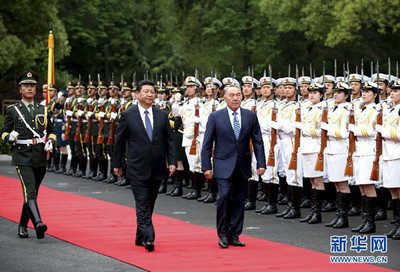文|成庆
柴可夫斯基自称其第六交响乐,即“悲怆”是其交响作品最出色的一首。此话自然不假,但是相比德奥作曲家而言,他尽管大名鼎鼎,但是仍然难逃“地区文化”之命运,就如德沃夏克、斯美塔那之类要与捷克民族文化相联系一样。不过这也难怪,尽管俄国西化较早,但是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文化对垒一直没有消除,这种情况也和中国当年民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论近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拉夫派对农民生活的迷恋,使得俄罗斯文化中有一种强烈返回民间文化的冲动。这种“向下看”的艺术发展路线与欧洲大陆一系的“向上看”的精英文化大有不同,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俄罗斯19 世纪下半叶涌现出来的“强力集团五人组”,和柴可夫斯基一样,都在大量利用民歌旋律与民间传说。当然,整个19世纪末期的白银时代文学与绘画又朝着西化派的方向发展,俄罗斯的近代文化史大致用斯拉夫的“大地情结”与西化派的“未来进步情结”来概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这样的背景下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便让人觉得十分有趣。我曾在波士顿听过列文指挥过“悲怆”,当时就感觉美国人对俄罗斯音乐似乎太过注重旋律的流畅感,而少在节奏以及音色的控制上用力,这或者是因为,美国人与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相差太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或许更易理解俄罗斯的情怀,李德伦的柴六虽未亲听,估摸要比列文出彩。 我手头有数个柴六版本,大致可分为俄罗斯指挥与欧洲指挥两类。俄罗斯的版本中,对我而言,要说最喜欢,可能还要算帕萨耶夫的版本。说起帕萨耶夫,也有一段故事可讲。他的老师是著名音乐家齐尔品(Nikolai Tcherepnin)和指挥大师高克,齐尔品对国人而言比较熟悉。Pashayev26岁以一曲“阿依达”成名,但其影响基本限于俄罗斯国内,虽然也曾在东欧数国作过“社会主义汇报演出”,但是基本也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艺术大师,他也去过伦敦演出,但那时候的西方之旅,基本只能让西方世界窥得一丝风采而已。帕萨耶夫执棒Bolshoi剧院乐团数十年,后却被当时的文化部长Yekaterina Fursteva 突然解职,让年轻的斯维特兰诺夫接替其位。在得知解职的当天夜里,帕萨耶夫心脏病发作,数天后便与世长辞,算是苏联文化体制下的一出不大为人所知的悲剧。 在这个1958年的录音版本里,还收有Alexander Spendiarov与哈恰图良的作品。尽管录音效果并不算太好,但是基本可以领略帕萨耶夫的指挥特质,如果拿他与阿巴多、卡拉扬之类的版本比较,会马上感受到乐句节奏性上的很大不同。以前初听“悲怆”时,常被其旋律误导,最后纳闷,此曲何来“悲怆”之意?后来才发现,许多指挥在对俄罗斯作品的把握上,常对那些动人旋律的处理颇为表面化,而这往往会落入柴可夫斯基美丽的旋律线陷阱之中。后来偶尔听到Litton的版本,才突然对此曲有所感觉。Litton对节奏变换的把握相当出色,因此“悲剧”气氛终于可以呼之欲出,尽管这种“悲剧感”十分“浪漫主义化”,但是至少打破了老柴指挥的一个误解怪圈。 而回到俄罗斯本土指挥,就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柴可夫斯基的把握的确深入肌理。仔细听帕萨耶夫,他对旋律的处理是用急速的节奏变换产生出一种极为强烈的张力感,同时会把旋律的“浮华性”淡化。比如第一乐章中长笛之前的那段旋律,处理地缓慢低诉,沧桑感立现;第二乐章圆舞曲帕萨耶夫也并没有将其演绎地绚丽多彩,而是极其明显的控制速度与节奏,低泣之意,呼之欲出。但是他并没有切割掉旋律之美,这也是帕萨耶夫最让我感觉奇妙的地方。他所具备的那种吟唱气质,有如俄罗斯大提琴诗人Shafran的演奏一般,吟诗需要节奏的变换,但是同时也得浮现诗意,两者兼得,实为难得。 有人或许会说,本土指挥指挥本土作品,自然会占得先机。不过在我看来,要指挥好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或许还需要体验到俄罗斯思想中的那种内在冲突,一方面它有东正教的神秘主义思想背景,一方面它又开始受到西洋近代化的严重冲击,不得不西化以求自新。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如何保存自己的“民族精神”,又保持自己的精神尊严与文化独特性,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国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