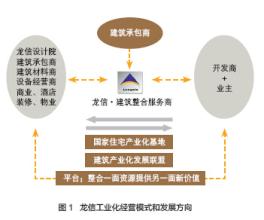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握后工业化时代的许多新特征,着眼于新需求、新供给、新增长、新配置、新思维、新改革,围绕“低碳经济”、“零能源建筑”、“消费主导”,探索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路径。在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路径上,要考虑打通工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装备支持通道,推动资本及部分工业企业向现代服务业领域转移,依托资本与劳动资源的双优势实施资本与劳动力向国外的同步输出
文/文宗瑜 转变经济方式的政策驱动与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提前结束了中国的工业化时代。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割裂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方式及工业比重将发生质的转变。工业化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两头在外而过程在内的中国工业产品制造模式”将被彻底替代。因此,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后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尊重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科学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 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基本 判断 中国30年余年的改革开放,从改革方向及目标看,是着眼于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从改革的实际推进看,更多的精力及着眼点是“补工业化的课”,从而实现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发展及经济运行表现出许多与“补工业化的课”完全不同的新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些影响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后工业化时代特征。 “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已经基本丧失 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低工资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创造了近10年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改革的加速、劳动力工资增长要求的趋强及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弱。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官员、企业家认为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与“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弱化相互叠加的作用。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再恢复到1998年—2008年的增长态势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两头在外而过程在内的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劳动用工的低工资时代宣告结束 “中国工业产品制造”最大优势是劳动用工的低工资与员工的超负荷劳动。无论是国内消费拉动的政策导向,还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与更有尊严的社会发展目标,都要求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必须看到,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在中国目前主要表现为提高员工工资的经济诉求。无论是从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看,还是城市的综合生活成本看,都要求大幅度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应该通过“劳动基准法”、“工资标准条例”的法律出台及实施,强制大幅度提高就业者工资,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产业工人工资增长3—5倍,到2020年基本可以保证一个农民工的初次就业月工资能够达到45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月工资达到6000元人民币左右。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将进入工资增幅较快的阶段,中国的高工资时代已经到来。产业平均利润率时代已经正式开始
在中国GDP已达33.5万亿人民币的条件下,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投资回报率会日渐趋于平均,产业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产业平均利润率作用的充分发挥,资本在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会越来越快,不同产业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支持性越来越大。产业平均利润率规律要求产业之间、同一大产业的各细分子产业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与此相适应,企业之间不再是纯粹的充分竞争关系,更强调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基本可以判断,未来10年,中国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会逐渐缩小,全社会的产业平均投资回报率会略有提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六新” 如果说5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主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种政策导向,那么,现在中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政策要求。这种政策要求,既有碳减排全球共同行动的外部压力,又有自身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的内部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要求中国探索一种与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是需求、供给、增长、配置、思维、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转变。 新需求 在后工业化时代,需求的重要变化就是从物质需求向非物质需求的转变,商品服务的文化要求与精神要求越来越强。从总需求看,非物质的文化需求与精神需求增长越来越快;从个体需求看,客户尤其终端的消费客户要求企业与商家在出售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增加非物质性供给。因此,有竞争力的企业所供给的商品或服务,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要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新供给 在后工业化时代,供给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要求提高文化附加值、精神附加值;二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要求均等化、多元化。第一方面的变化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而推动,第二个方面的变化依赖政府思维与职能的转变。就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而言,其均等化、多元化、不仅可以降低民生成本,而且可以扩大需求,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良性循环。 新配置 在后工业化时代,配置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重要的是资源配置结构的转变。中国30年(1978年—2008年)的改革开放,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资源的积累与聚集,但是,许多社会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或未被开发状态。以官僚资源为例,中国省(部)级以上的离退休官员,70%居住在北京,25%居住在各省会城市,如果制度上鼓励支持一部分离退休的高级官员自愿回其各自的家乡居住,并配套相应的政策措施,不仅可以减少中央政府为离退休高官服务保障的压力,而且可以拉动中小城市尤其乡村的消费,还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的均衡发展。因此,新配置既要强调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统一配置,又要重视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 新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增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向经济增长质量的转变。GDP年增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指标,7%的年增幅,8%的年增幅,9%的年增幅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只能算是一般增长,只有10%以上的年双位数增幅才能满足中国人的高增长欲求。为了追求高增长,实现高增长,不仅要支付巨额的环境资源成本,而且要积累日渐加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工业化时代的经济高增长,既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又进一步放大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而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质量强调经济、环境、自然的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社会、政治的同步前进。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低迷,为经济增长速度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变创造了契机,以此为起端,政策及各种经济手段要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而不是单纯经济增长速度的复苏。只有着眼于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才能把中国经济发展纳入重视经济增长质量的轨道。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新增长,几乎不可能再实现GDP年10%以上增幅,如果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水份,GDP年增幅在5.5%—7.5%之间,仍然可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