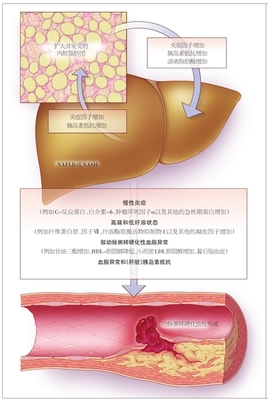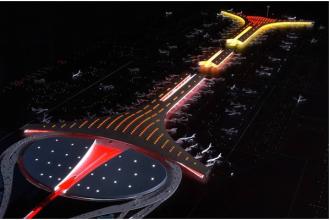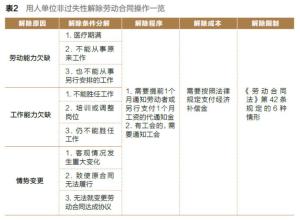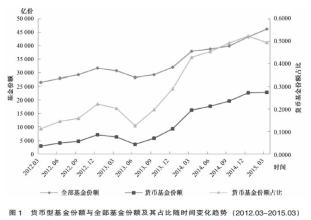“你已经作好准备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进行管理了吗?”詹姆士·赫斯科特(James Heskett),哈佛商学院的管理教授不久前在网络上抛出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赫斯科特说,我们正在被一股行为经济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的洪流所包围。的确如此。传统的基于计量和理性分析的决策科学日益遭受挑战,而金融危机将这样的挑战推至最高潮。风暴中心的格林斯潘也低头承认,“市场朝着自己所未曾预料的方式运转”,那些基于精密模型和周详计算的金融衍生品将世界拖入泥潭。 这股对“理性决策”的反思之势越来越汹涌。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教授在其新书《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中,全面颠覆着芝加哥学派的衣钵。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都认为,市场中人是经济人,有着精密的“理性”,决策也因而是一种严密逻辑推导下的选择。然而泰勒和桑斯坦却把自己称为“行为经济学家”。《商业周刊》以“热度席卷而来”的字眼形容如今风靡日上的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论点:人拥有理性,但并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定义的一样,足以成为精准计算并严格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仪器,而是身陷“有限理性”的泥沼,被非理性的一面耍得团团转的不完美动物。 这股对理性决策“席卷而来”的批判热潮,还包括查尔斯·雅各布斯(Charles Jacobs)的新书《管理新探》(Management Rewired),以及丹·艾瑞里(Dan Ariely)不久前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理性经济学的终结》。前者发现,许多在管理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都与神经系统科学的发现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大多数东西也许都是错的。”而后者认为,管理学中基于员工、顾客或竞争者的非理性行为的理论、策略和行动,要远比对他们“理性”的假设更为可靠。 拷问“决策理性” 传统商学院对决策的训练,总是偏重理性分析。例如,商学院经典课程DMD(数据、模型与决策)中就有一个案例,讲到肯德尔螃蟹和龙虾公司面对一场可能的风暴,而龙虾对保鲜时间的要求很高,这就面临几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的选择。在给出各种可能的情况及其发生的概率后,MBA们需要用绘制决策树的方法,计算出何种解决方式最终产出最大。学生们埋头描来算去,列出各种可能的状态和事件,绘出决策结点、方案枝、状态节点、概率枝,算出各种情况下每只龙虾的利润值,最后得出“最优决策策略”。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计算和训练,就以其中的一个环节来说:所有情况下的概率都是人为设定的,而实际状况中的差之毫厘可能就会使结果谬之千里;况且在现实商业环境中,决策制定及其后的执行过程,更是受到理性之外诸多微妙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对于越南战争的决策,单纯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审视,整个决策过程的周密程度堪称完美,然而事后证明这几乎是一个无比可怕的、失败的决策。 当理性决策的漏洞如此明显,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决策的“冰山”下,那些不为人们所熟知,却又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决策结果的隐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又该如何去把握这些貌似很难捕捉的因素,让决策更加完美? 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性格与情感:隐规则“两翼” 理性之外,人的感知觉、记忆、思维、情感、风险偏好、抱负、群体思维等因素无不影响着决策。想要对此形成较为充分的认识,往往需要了解决策者的决策风格、真实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及其受到的人格心理结构因素、群体情境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影响。 许多研究者已经对这些影响决策的隐性因素进行了探索,比如决策心理学本身就已经是一门不断成熟完善的交叉学科;与理性决策相对应,以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学为基础的行为决策研究也使我们对决策的“隐规则”加深了理解。 在所有这些繁杂的隐规则中,我们认为性格与情感是最为关键的两翼。 一方面,性格既有与生俱来的特性,又带有个人成长历程中的烙印,对于一个既定的决策者来说,在既定的环境下,他的决策会遵照某种既定的方式进行,这就是性格主导的部分。而另一方面,正如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组织文化副总裁王民明所言,影响决策的不仅仅是性格差别,更包括对环境的了解、对个人洞察力以及个人能量状态高低等因素,后者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性格。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为决策者贴上某个性格标签,以此来解释他的决策行为。那么,在不同情境下,在压力大小、能量高低、是否放松等不同状态下,性格之外的“随机因素”又受何支配?我们认为是“情感”。 性格:决策隐规则的“左翼” 透过许多管理者的决策,往往能够窥见他们真正的性格偏好,这是一种本我的流露、来自内心的反应。MBTI、九型人格或PDP人才测评这些工具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通过不同的角度看清楚企业真实运作的主体—人。 同样是国际并购,李东生的一意孤行与柳传志的扎实稳进,分别代表了怎样不同的性格偏好?MBTI工具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性格对决策影响的端倪(见后文《你属于哪个字母?》)。而九型人格则分出九种有规律的心理特征类型,各型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注意力焦点、基本恐惧和主要特征,并探讨它们在决策中的心理过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企业在决策推行的过程中,将传递到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人身上,而关键是如何让大家一起进行有效的决策、达成共识、形成高效的执行力。

如果说智商代表着决策中理性的部分—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对事物本质的洞见—那么,高智商者为何往往仍会作出低水平的决策?因为性格是决策隐规则的“左翼”,它非常关键。本期封面文革对小布什执政期间的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与许多人所诟病的“小布什非常愚蠢”所不同,小布什的智商水准其实非常高,他具有高超的政治能力和智力技能,也就是说,从理性层面看,小布什快速思考并根据复杂信息作出决策的能力是很出众的。然而,小布什的心理特征却成了“阿喀琉斯之踵”。“外向”、“支配”和“大胆无畏”的性格类型,让小布什的决策行为显得粗心大意、肤浅、冲动。伊拉克战争的困境显然就是这种决策风格的典型体现。 情感:决策隐规则的“右翼” 性格是决策者与生俱来并带有成长过程中的烙印,作为决策隐规则的“左翼”,它带有某种“既定”的性质。然而在具体的决策行为中,还有许多“随机”因素产生影响,如前面提到的对当时环境的反应、个人能量状态的高低等。这些发生于决策瞬间的要素会通过影响决策者的情绪、感受、直觉等方式最终影响决策。我们将凡此种种定义为“情感”,它是决策隐规则的“右翼”。 爱荷华赌博任务的实验证明,情感是决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甚至主导了决策(见后文《决策背面:不是理智,而是情感》)。在一个决策过程中,事件的发生会让决策者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情感反应,紧接着就是与情感反应一致的行为变化,然后才开始意识到这些驱使行为变化的情感,亦即直觉。最后的环节,才是理性作出决定。这个实验揭示了决策过程的大脑运转机制:一开始大脑并非有意识地进行判断和推理,而是由潜在的情感和直觉驱动行为变化,直到大脑意识到这种变化并从理智上给予解释,并指导自己下一步的行动。由此,整个决策的隐规则和明规则闭合成一个完整的逻辑。 学者奚恺元等人的研究更是从情感与感受的角度,分析了人们为何总是不能作出让自己最为满意的决策(见后文《“最好”的决策为何那么难》)。规则、非专业的理性主义和媒介最大化,都是避免冲动而产生的自我控制方式。而在决策者在短期幸福和长期幸福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中,对自我控制的运用方式往往令我们或者放纵了短视行为,或者决策保守而错过快乐,所以总难作出让自己最感幸福的决策。而决策时的风险大小、时间紧迫度、目标的远近、现场的情绪等场景因素,统统都会支配决策者的情感,从而影响决策的结果。 ***** 理性、逻辑的分析工具或许可以解释决策冰山上的显性问题。然而冰山底下,与“人”有关的部分也许才是决定性因素。如何找到这些隐规则的钥匙?我们提出了一个较为简明的理解方式—决策隐规则的两翼。“左翼”性格代表着决策者某种与生俱来的、既定的决策路径,而“右翼”情感则代表在特定的决策场景下大脑作出的、临场随机的反应机制。“左翼”与“右翼”,共同构成了决策隐规则的两端,只有理解它们,才能超越肤浅的理性,在决策中游刃有余、妥善应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