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们到底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生产,这个问题看来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行为不仅是满足自身需要,同时也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必需。这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消费,部分就是社会或国家应该为人民偿付的福利。 与福利相对应的概念是税收,前者是出,后者是入。税收的功能内含了公平社会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国家福利有着密切关系,而福利与税收的关系中,一般都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国家福利(也就是政府组织收入为社会提供福利)这个层面上,福利和税收的关系是,低税收一定是低国家福利,而高税收的结果不一定是高福利。 中国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经济加快转轨使原有的福利模式被打破,这给人们带来的不适应是必然的,也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着重布局的。一方面,中国政府的税收以年均20%的速度快速增长,超过经济增速的一倍不止,也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看病贵,住房难,学费高,养老和失业保障太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感受最深的问题。 现实社会中,用于维持社会再生产的这部分福利究竟应该如何分配,如何处理好福利、贫困和资本效率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果。当然,国民自然希望自己的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恐怕就是很多人向往北欧福利模式的原因,而高福利的前提是高税收,中国目前国民收入普遍较低的现实,使这个愿望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而且,在中国国家财政体系尚处于不透明的情况下,“高税收下一定有高福利”这一假设也很难成立。事实上,这不单是中国的“国情”,上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伟大社会”计划,政府幻想为全民提供高福利,结果使美国社会畸变,财政赤字暴涨,不得不回头。 既然国家福利难以指望,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一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办法:低税收高社会福利模式,藏富于社会,还利于民众,少取一些,也就是多予一些。组文中九鼎公共事务所秋风先生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对美国、北欧福利税收模式的分析,或许可以给读者一些新的思考。 以低税收建设高“社会福利”体系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欧洲国民的税负远高于中国,中国人的怨气却远远高于欧洲。这当然与税制不合理、税收与福利的不对称有关,但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 就在政府公布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之际,几位学者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建立北欧那样的福利国家,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大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可以、也应当学习福利国家,为民众提供全面的国家福利保障。另一派学者主张,不应当建立过于臃肿的国家福利体系,因为其效率低下,并可能影响国民的勤奋精神。 其实,中国恐怕既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但这并不是损失。中国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中道”福利模式:政府实行低税收政策,以有限的税款建立、维持一个“薄而全”的国民福利体系;大多数财富留在民间,由社会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一个多元的社会性福利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政策上较为可行,更与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有利于这样的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与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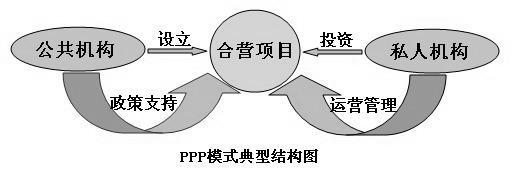
欧洲福利国家的文化基础 北欧及整个欧洲的福利国家,表现为由政府向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种福利制度并不完全是社会富裕的自然产物,而是信念与文化的产物。 这涉及两个方面的信念。国家福利不是免费午餐。而政府自己凭空造不出钱来,高福利必然以国民的高税收来支持。因此,建立高福利制度的前提是:人民是否愿意承受高税收?人民是否信任政府,相信政府把收来的高税收用于国民福利?正好,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人民具有这种信念,而中国人却向来缺乏这两种信念。 梁漱溟曾经用一张图对比中西文化的不同。不论中西,社会的组织都从个人开始,经过家庭,到达团体。这种团体多种多样,可以是宗教、阶级、职业团体,最高层面的团体是国家。三者的位置,在中西大不相同:“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若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 欧洲人好过团体生活,比如,基督教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是典型的组织化宗教。它的教义也具有强烈集体主义倾向,现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仰都与基督教传统有密切联系。这些宗教与世俗信仰体系都要求个人融入团体,共同分享财富、幸福。长期生活在这种信仰传统中,个人对于团体易产生信赖感。因而,现代国家形成于欧洲。 当然,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既然团体对人们的生活十分重要,人们也就设计了各种制度来保证团体——不论是教会还是政府——增进自己的权益,限制其侵害自己权益的权力。有了这种制度保障,国家就成为个体深度投入、融合的共同体。所以,欧洲曾经出现过强烈的民族主义,各种主流意识形态都强调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国民也甘于充当国家的工具。至今欧洲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极其深厚。这一点,深为20世纪初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所羡慕。 随着民主因素强化,这样的政府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个人的保护者,即个人的保姆。国家福利制度的本质就是政府充当个人的保姆,整个国家成为一个集体分享彼此财富的精神与宗教性单位。福利国家绝不是简单的物质问题,而带有强烈情感因素。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教会在人们生活中的全能功能。人们信赖这个保姆,相信它收了钱,会把钱用到自己身上。人们也相信,政府会像忠诚的保姆那样照顾自己,所以,安心地把自己交给政府,生老病死由政府来负责安排。这就是北欧式国家福利制度的信念基础、文化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人们才会把国家福利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才会乐意为高福利支付高税收。 中国缺乏福利国家的文化基础 相反,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和公共性团体生活都是相对匮乏的。比如,儒教被学者归为“分散性宗教”,它缺乏清晰可见的组织化建制。康有为要模仿基督教会建立孔教会,终归不了了之。 对于政府,人们也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中国农民常有“天高皇帝远”的想法,文人也向往着“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所以,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焦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最痛恨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就是人们没有“国家观念”。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人都控诉中国是“一盘散沙”,就是说,人们只知家族、只知乡亲,而不知国家。 直到今天,经历过几十年的强制集体化生活,人们也同样缺乏充分的团体意识、国家意识。人们对政府没有特别的期望,也完全可以没有政府而正常生活。更进一步,人们对政府有那么一点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会诚心诚意地服务国民。过去的“文化热”中经常有学者说,中国人迷信大政府。这是天大的误会,这是把“单位制”时代少数人的想法当成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在中国,人民向来躲着政府,不愿与政府打交道,遇事也不会去求政府。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的税收负担十分敏感。自古以来,社会动乱都是由政府的苛捐杂税引起的。今天,中国民众对于税负的抱怨也十分强烈。这一点让很多学院派税收专家很不理解。欧洲国民的税负远高于中国,中国人的怨气却远远高于欧洲。这当然与税制不合理、税收与福利的不对称有关,但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人们更愿意把钱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愿意交给缺乏足够信赖感的政府。国民普遍地不愿意在国家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体内部分享彼此的财富,人们不习惯如此紧密的团体生活。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