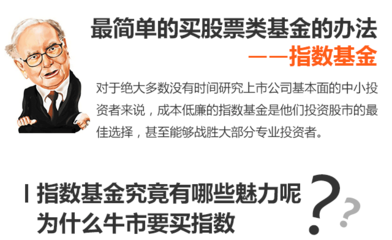亚布力观点:这就发展到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了。不过陈教授,我想沿着你这个路径,把话题引到我们都很熟悉的费孝通先生身上。你知道,他的《江村经济》有着对中国经济社会非常细腻、非常学术化的关注,我在里面读到了先生对中国人的深沉的关切。但是在他的晚年,他似乎再也没有兴趣、没有精力来思考人的命运了。我想说的是,你与他是一样的负笈海外,一样的作品等身,为什么你却把目光锁定在人的发展上?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问,是不是等你老迈之后,你也会放弃这种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呢? 陈志武:我认为我是能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他有权力和地位,德高望重,实际上他是把自己带进了上层权力的体系中,所以到后来,他已经不是一个学者。他要享受所谓权力阶层方方面面的好处,他可能身不由己。这个问题值得关注,不管是谁,只要他稍微不注意的话,权力很容易把一个人给异化了,因为权力的吸引力确实太大了。 事实上我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机会。我有的时候想,如果我愿意这样的声音稍微小一点少一点,我在中国也可以做很多与权力有关的事,给我很多与权力有关的地位。但我的个性在此,加之我身处耶鲁大学,所以,我一般在中国开会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去有部长、有副总理、或者是总理的那种会议,那种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像我们这些人,你到那儿去,不管你说什么,没有人会去关注。你要说得太认真,就是不懂事、不领会这个场合,完全是一个异类,你是跟这个场合完全是不相干的、不协调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明显看到,你的权力越多、越大,大家都会把注意力聚焦在你的身上,前呼后拥,很多人都会这样,绝大多数的人都向往那种境界。这显然是一种权力的境界,而不是学术的境界。 亚布力观点:你这样的选择,是您的个性使然?还是您的另外一些因素决定的? 陈志武:完全是个性,有的东西是天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本能的对权力的反感。 亚布力观点:真的吗?这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般是“学而优则仕”,我们都是这么被教育、被熏陶过来的。 陈志武:所以很多人骂我,很多人说我对国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的不是太多,也许他们说得是对的,因为我受这方面的影响是不多。 我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管我,也顾不过来—— 我有五个兄弟,我父母有六个儿子,没有女儿,家里面的事情太多了,我母亲每天清早天还没有亮,四五点钟就起来下地干活。在我们起床之前,母亲已经在菜园里干活干了好几个小时了;回到家里,看到我们起来,她就开始做饭;做完饭,看着我们吃完了,她又下地干活;中午回到家里面洗衣服、做中午饭。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每年夏天母亲做午饭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她一边做菜一边打瞌睡。然后做完中午饭,她马上再继续洗衣服,把衣服晾干,她没有休息的时间,午饭后又要马上下地干活,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到家里又做晚饭,晚上还要缝衣服。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母亲从小就没有教育我怎么巴结权力。 亚布力观点:我能基本认同你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认知习惯。成长的环境,尤其是小时候的环境,可能决定着我们一生的价值观体系。我想提一下杨小凯,我知道你熟悉他。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就有某种对权力和政治的宏大思考,跟我们这些苦孩子的出身太不一样了。 陈志武:我见过杨小凯,但是没有太亲密的交往。所以我不是太了解他这个人,但是我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惊讶于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竟然那么相似,也惊讶于另外一些领域的完全不同。 亚布力观点:对,他的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在思考国家命运,在晚年才回到个人建设上。而你却在中年开始,就已经把人的命题纳入到你的学术架构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区别? 陈志武:这可能跟一些偶然的因素有关系。在个人因素方面,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85年我在国防科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国防科大的各个系把所有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都叫到操场上,然后让系里的政委、系主任还有其他的领导,从前面到后面,一个个地审查,看看学生有没有奇装异服,看看学生的头发长不长。当时,我们系主任和政委从我身后走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那种审判的眼光来看我,我的血压迅速攀升,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用脚踢他。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侮辱——他们凭什么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我?我有我的人格,我很愤怒。好在我当时年纪尚小,胆量不足,最后一瞬间,我抑制住那种冲动。 亚布力观点:我能理解你当时的愤怒,我们都是这么愤怒过来的。 陈志武:对,我觉得很难忘记。如果当时我真用脚踢的话,那就麻烦了。 亚布力观点:你的人生也许就完全改变了。 陈志武:不过这件事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人要活着?我的尊严来自于哪里? 亚布力观点:事实上当时你已经开始思考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我们再来看看湖南的另一位学者,黄仁宇。他一辈子都在思考国家的命运,无论是大历史观、数目字管理,还是明朝的财政税收,都是国家主义思维,他似乎一辈子也没有思考过个人建设,这是为什么?他也身在美国,事实上他的日常生活可能比你更美国化。 陈志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前几天我在演讲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名记者问我,你鼓励年轻人借贷消费,把未来的钱借用到今天来花,这样会不会让太多的银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加?我回答他说,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像总理一样思考问题。金融借贷,本身是一种博弈。对个人来说,你能够借到钱,你就赢了一半。银行既然愿意把钱借给你,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个人没有必要把整个银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但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大家都不这么思考,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从总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考的错位。 亚布力观点: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杨小凯生病以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陈志武:我也非常认同这句话。多年前胡适之先生早就说过这种观点,他说年轻人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亚布力观点:所以胡适之成为了一代宗师。你看胡适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所思考的问题,胡适早就思考过了,而且都给我们找到答案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话语都是在重复他的思考。 陈志武: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很神奇的人。在中国知识分子里面,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或者重新思考,没有太多的人从英美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换句话说,一直到现在,知识分子没有几个能够像胡适那样,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个人建设找到方法。现在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做专门研究的,尤其是专门研究“五四”前后这些文化和哲学的人,以及做历史研究的人,没有几个领悟到了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尤其没有领悟到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亚布力观点:你这是典型的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在学术上早已是一个学科,是一个范式。你看李约瑟,他是从科技的维度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费正清、费维恺,是从清末的历史,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黄仁宇则是从明朝的财政体制来分析中国问题。美国的汉学家彭慕兰,他是从田野调查的角度,从中国乡村入手,站在一个很具体的小村庄来分析中国问题。我觉得你是延续中国问题的学术史研究,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内,你的路径很醒目,就是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您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吗? 陈志武:有很多道理。但我不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这不是我的立足点,但或许可以说,你的表述接近了我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领域。我更多的还是一个经济学学者、金融学的学者。这个可以说跟中国有关系,也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用这样一个分析范式,来看看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她的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我会拿这个作为我的一个实验室、一个数据和资料的佐证来源的地方。 我这么说,不是自谦。但我承认,我很早就看到,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这些人普遍只对朝代历史、朝代变迁的历史感兴趣。但我更有兴趣的,却是人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开头说的,我现在对市场经济救中国的命题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市场经济救中国人的兴趣。金融让我们得自由,我想这是我未来思考的重中之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