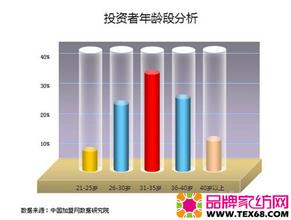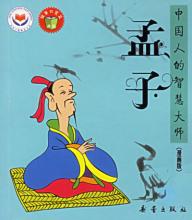她是一个最不像创业者的创业者;她只想找寻“有劲”的生活,却在无意中掉入了商业的河流;她在一次次呛水中学会了游泳,最终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采访 | 《创业家》记者 申音方浩 白明婷 文 | 《创业家》记者 白明婷 编辑 | 方浩 摄影 | 李冰 插画 | 赵贺佳 “咱们今天能不能就到这儿呀!你们从办公室一直问到车上,都快把我问吐了。”坐在我身边的李静终于抗议了。她示意司机把前面的车窗打开一些,透透气。 她看上去要比电视上更为娇小,坐在那辆已显老旧的宝马5系的后排座上,一路上手里不停地把玩着一副大墨镜。我们正在开往位于大兴的一座录影棚,李静要在那里录两档节目,嘉宾分别是于谦和那英,时间会从当天晚上六点直到次日凌晨一点。 作为一位以提问刁钻鬼马著称的著名女主持,一个早就习惯于镜头和闪光灯的时尚达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纯粹商业类媒体的拷问。 从李静的嘴里,你几乎听不到“商业模式”、“现金流”、“企业战略”等这些创业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尽管她的确创造了一家在全中国可能模式最独特的传媒娱乐+电子商务公司。她在东方风行公司内的官方称谓也不是“李总”,而是“静姐”。“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大姐大,戴着墨镜,穿着黑风衣,身后跟着一大帮小弟小妹。”李静对此很有些自得。 “不一样的访问”,就像她在成名节目《超级访问》中喊出的口号一样,李静也是《创业家》杂志迄今为止采访过的一个最不一样的创业者。 跟我们熟悉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创始人(他们基本上是男性)不同,李静从第一天起就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远大的目标,她也没有主动去对标一个现实的可模仿的榜样,她不在乎钱,也对资本没有什么概念,她甚至从一开始就抗拒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 她只是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点出发:为了摆脱现实的无趣,要去做一些真正“好玩”的事情。在不断的尝试和挫折中,这个热爱摇滚的“文艺女青年”慢慢发现,一个原本随性而为的小工作室,完全可以演绎成为一个半径不断向外延展的酷商业。 这难道不是“创业”的真正本质吗?寻找人生的乐趣,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 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犹豫不决的朋友,他们穷尽一生在寻找一个所谓的目标或者理由,无数次地推演得失成败,来说服自己投身到创业的火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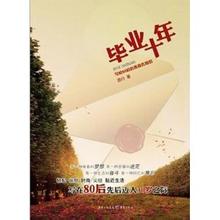
为什么不能像李静这样简单呢?只要“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乔布斯语),任何其他事物就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那时我觉得‘李总’这个词特俗气” 我相信很多的创业家都不是踌躇满志地要去创业,都是被命运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要面对的责任,你的第一反应是逃。但是扭身一看四处都是悬崖,第二再想,那我就硬着头皮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夸大所谓的什么远大抱负。但是有一些特点,他勇敢、无畏,还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我从小就做那些梦,都是我去把别人拯救了。 1999年,已在央视小有名气的李静突然向领导提出了辞职。 “当时在央视很不开心,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种不听话的主儿,对节目总有自己的想法,领导就找我谈话,但我是铁了心要辞职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我创造不出什么来,当时我对工作的取舍原则就是好不好玩,快不快乐,有劲没劲。那时候我觉得特没劲。” 本来李静想像许戈辉、陈鲁豫那样去凤凰卫视的,但由于没什么熟人,也就未能去成。怎么办? 好在还有一批“臭味相投”的老同学,这些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整天谈论的话题是自由、艺术,和这帮“死党”在一起,李静觉得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就跟我的同学聚了一下,我说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咱们拍戏,自己写剧本。然后他们说这里面最有姿色的就是李静,李静你负责去拉钱。我说对,这事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写完以后就去拉钱。根本一分钱也没拉来。不是水平不行,那拨人里面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也有《金粉世家》的美术,但当时还是一帮电影学院的小毛孩。虽然没人理我们,但我们都很狂的,不理他们那套。 但是后来钱还是没拉到,大家都散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总得干点什么呀。 在不痛不痒之中,李静已经由一个央视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北漂”,但她依然花钱如流水,跟哥们在外面吃饭、喝咖啡,基本上是她一个人买单。原因很简单,一是做主持人这几年攒了一些外快,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好,没什么压力。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在最初从央视出来自己做事的那段时间里,之前几乎就没坐过北京公交车的李静,每天出行仍然习惯性地打车,该吃就吃,该消费就消费,有一天突然发现“现金流”马上要枯竭了,就在马路边花2块钱买了张奖券,希望碰碰运气,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李静心想,这样上下班不就可以省下打车钱了吗?于是转天就骑自行车上班,但骑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下来又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美其名曰“休息一下”。 后来我同学就骂我,他说你算过账没有,面的才10块钱,6块钱一根冰糕,还骑得那么累,你还不如打一个面的呢! 所以后来我说我要做公司,我们全家都笑得不行了,我妈说你这个孩子从小就糊涂,从小账就算不清楚,上学时老给家里发电报说:钱已经花完,速寄。所以我说做公司,我妈就觉得很可笑,果然就应验了。现在很多人跟我说,说静姐我想跟你一样,我说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一定会头破血流。 2000年,李静和她的妹妹李媛,还有一个同学,三个人组成了最初的团队,再加上不久后进来的歌手戴军,几个人就这样聚到了一块,第一个节目就是《超级访问》。 但是直到2002年,李静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创业、开公司的概念:“一开始我拒绝,虽然我在做一些公司该做的事。为什么拒绝?因为我觉得一说创业就特别有铜臭味,我特别怕听‘李总’这个词,我觉得那样特俗气。我觉得我还挺文艺青年的。” 更要命的在于,一般节目公司是先有广告队伍,再有发行队伍,最后才有制作团队;而李静的东方风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风行)则是,一上来就是制作队伍,广告和发行队伍根本不存在。 后来给了李静第一笔风险投资的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坦言,最担心的就是这行业的人够聪明,但是有时“不靠谱”,很容易摆不正位置,“该做老板的时候艺人心态”。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当你按套路出牌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而且那个价值是可以被评估的,你做的破例的东西的价值却是永远不可评估的。但前提是你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节目够牛。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立命之本:第一,要做出最牛的节目,就是要有谈判的条件。就像唱片公司,你要有大牌;第二,一定要打破规则,才会让他没办法去衡量你的价值。 对于一直以“文艺青年”自居的李静来说,从2000年到2002年是她为这个身份“买单”的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年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最惨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每天都是最惨,没有最惨。”李静说。 电视节目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拍完20集,就一次性给电视台,如果中间没钱了,也可以选择不拍。但电视节目不一样,它是要和电视台事先签约的,所以电视台不管你赚不赚钱,作为节目制作方,你必须一直录下去。 所以我们永远都在想下周录节目的钱,就可怜到这种地步。当时我们是一帮文艺青年,就觉得《超级访问》是那么好的一个节目,没有因为它不挣钱,这个事就不做了。可是现在想想,如果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看,我们的思维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非常焦虑,最多的时候欠债200多万,而且我当时找的助手都是大学生,都是同学的一些弟子,他们当时就很无助地看着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主持搭档戴军称,当时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 这一点得到了李静母亲的确认。每次回家借钱,李静都会从母亲那里得到爽快的答复,虽然家里不是特别有钱,但绝对百分百支持。“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愿意陪着我玩,我妈说因为怕看到我想不开。她说那时一想到我欠了那么多钱,就很着急,甚至半夜会突然坐起来,但一看我睡得呼呼的,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 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晚装,化了浓妆去应酬。出门前,她会倚在门框上,回头很娇媚地说:兄弟们,等我的好消息啊。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人觉得辛酸。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目,而广告的事却音讯了无。 这种艰辛让李静慢慢地意识到了经营的重要性。当时主流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如光传媒、欢乐传媒等,这些公司与电视台的合作关系都非常简单,就是把节目免费给电视台,然后电视台给你几分钟的贴片广告。如果按照市场价值估算,这几分钟的广告费用一年下来可达上千万,但问题是,电视台不负责给你卖,这是节目制作公司自己的事,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客户资源的李静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 在交了一年多的“学费”之后,李静决定放弃单纯靠贴片广告过日子的生存方式,她想出的办法是卖节目。“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发行总编叫过来,我说我要卖节目,他说不可能,说从来没有卖过节目,中国电视台只有买电视剧,没有买过节目。”李静说,她决定亲自披挂上阵。 我坐着飞机、坐着火车自己出发,去地方电视台,跟人家说我做了个节目。那时大多数地方电视台还很少有外面的节目,人家就说你先回去吧。我说我不走,你们得看,你们看了我再走。人家还挺好的,毕竟原来在央视积累了一些关系,他们带我吃喝玩乐,而我心里根本都没有心思吃喝玩乐。 记得是在湖北,他们带我去汉正街附近吃饭,饭店门口正好那儿有一个拉二胡的,一个瞎子艺人在那儿卖唱。他们还特高兴,让我吃这吃那,然后有一个服务员拿着田鸡就往地上摔,都摔蒙了,然后把田鸡的皮扒下来了,我觉得好残忍。与此同时,瞎子就在那儿拉二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觉得特别像我的心情。我就想我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后来我特别想把它拍到戏里。 最后湖北台领导特好,陪我吃饭。我说你们不要我就不走,后来他们就看,所有人都在审,审完以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说,节目真是个好节目。然后我就特别斗胆地说,如果不好你们就下调,但是前提你们要买我的节目。那时我开始学贼了,因为我不是拉广告的人。 当时李静给他们的方案是,5分钟的贴片广告全给电视台,只把其中30秒作价留给李静。李静跟对方说,这个节目如果收视率第一,你就能卖几分钟广告,而且你一分钱不用投,仅仅需要花费两三千块钱;如果收视率低了,你就把节目停了。电视台同意试一试,每期节目给李静这边2000块钱。这样,在拉不到广告的情况下,李静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卖节目给电视台的人。这一卖,就是50个台,一期节目能卖10万元,而当时一期节目的成本是3万多元。李静开始赚钱了。 成功地卖出了节目后,她没有满足于一期7万块的利润,《超级访问》很快拉到了大红鹰的冠名。 付费买节目的电视台不乐意了,可是此时的李静谈判的时候底气十足:《超级访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江苏台和南京台的人同时跑到北京来找她请客吃饭的时候,她就发现了变化:自己已经开始占据卖方市场的主动。 这些变化和做法慢慢让李静发现不按套路出牌是对的,只要逻辑行得通就该去试试,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行的。 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让我发现原来营销是这样的。我把《超级访问》调到了全新的一个平台上,就像是球星转会一样,一旦成功身价倍增、利益倍增。真正从《超级访问》赚了钱,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我觉得我对这个公司最大的功能,不是管理功能” 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你不是最好,一切都是问题。如果我的节目不够一流,永远都是被别人选择,即便我每天拼命想和别人搞好关系,也搞不好。如果我把节目做成一流,我不用跟任何人搞好关系,这个台不做了,另外的台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所以基本上这八年我只做一件事,这就是我的立命之本。 从2003年开始,李静又推出了《情感方程式》、《美丽俏佳人》等新节目,因为通过《超级访问》她发现,自己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能够比别人快一步,给观众最新鲜的东西。 《情感方程式》的推出也创造了一个第一,就是中国第一档真实还原情感话题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的诞生很有意思。那是2003年的时候,李静去马来西亚出差,无聊的时候她就坐在马路边喝咖啡,看着人来人往,突然觉得换了一个国家之后人与人之间会显得如此陌生。 “什么问题?语言。”李静想。 如果一个家庭之中,两个相爱的人之间语言出了障碍,是不是就会变得很陌生?李静决定要做一个情感节目,回国就和同事们商量。“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看着我说,你有病啊,谁会上电视说自己,家丑不可外扬。” 虽然已经习惯了被泼冷水,但这一次李静还是坚定地要做。从筹备到录制样带,一个月就做成了。李静把她电影学院离了婚的那些同学全都从外地弄来了,先杀熟! 这个节目最早是在深圳台播出的,一炮走红,以至于后来央视做《心理时间》,邀请的专家都是李静挖掘出来的那批。“他们都是我翻各个医院黄页翻出来的。”李静得意地说。 事实上,这个创意与李静的爱好有关。她爱看法国电影,里面全都是讲人性的,而国人对人性的关注又特别少,所以她要让国人敞开心扉地聊人性。“我觉得我的创作激情要大于管理激情,”李静说,“我一直担心做公司会限制我的创造力,把我变成一个特别冷漠无情的商人,我希望保持自己的激情。” 虽然整天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但李静并不觉得自己活得很累。“我生活中的状态与节目中基本是一样的。”李静说。以前有个她很崇拜的台湾女主持,上她的节目,台上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切,然后李静就问这个人的助理,台下她也是这样吗?助理说,不,台下很冷酷的。 多累啊,我可不想成为那种人。为什么我喜欢王朔的东西,他跟别人的交流方式,就是我损你,你也知道我损了你,但是你不会有压力。我批评人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让别人特别压抑,紧张,或者害怕我。 在现实中,她经常像朋友一样叫助理“亲爱的”;但是在拍照时发现衣服没有准备好时,她又会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下属,并得出结论说人只能相信自己。这时她是老板。 2004年之后,李静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成本概念。“之前太自我了,节目没有考虑成本,不管消费者需求,”李静说,“现在不这么做节目了,我先分析市场上需要什么,然后我再去想一个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有可能谁来买单,卖给什么客户,因为我知道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她学会在不同的节目里做出不同的角色调整:比如在《我爱每一天》,她所有的衣物是柔软明亮,淡淡的妆,不戴任何首饰,语调温暖、包容。在《非常静距离》当中是皮衣、中性的,可以互动、可以玩,甚至带一点霸气。在《超级访问》当中,是跟戴军的配合是第一的,自我是第二的。 李静心目中的好产品需要达到双重指标。首先,作为内容提供方要经得住收视率考察,收视率特别残酷,你跟谁认识都没用;第二,生存指标,就是广告。观众高兴了,但要是没有广告还是得关门。这是两个会冲的指标,有时候广告的东西在里面,观众就会换台,那观众换台了广告又不会投,所以一个事情要达到双赢非常难。 在制作公司的这么多年当中,李静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跟广告部打架,可是也不敢真跟他们打。 我尽量站在观众的忍耐程度想。因为我觉得你给观众一个打动他的东西,你再给他加一广告,他觉得我能接受。如果你先给了他一个广告,然后又没给他一个好东西,他说什么玩意儿。事情就是这样,我其实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人。干我们这行的,对我们帮助特别大的是主持。你做事、做人、做节目、做访问就是研究人性,你把人性研究透了,别的就容易了。 “我相信很多创业家都是被命运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 我在整个大学什么都没干,天天就拉琴,我现在用到拉琴了吗?没有。我后来学了那么多东西,编剧、管理、主持、电视,然后学做品牌,是因为我不断地在打破昨天的我,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我觉得好多东西是被选择的,但是后来慢慢变成你拥有的一种能力。明天东方风行在全国开了火锅店我都不吃惊,当然从公司来讲一定有自己的业务主轴,但是从人格特质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有的人只不过没有去试。 2007年的下半年,李静过得很纠结。 当时,东方风行旗下已经有包括《超级访问》、《美丽俏佳人》、《情感方程式》等多档节目,仅靠内容销售和广告,年利润达到近千万。在国内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中,规模和收入仅次于王长田的光线传媒。
 爱华网
爱华网